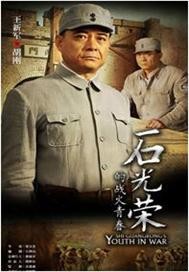白玉楼是京中的老牌酒肆,不但酒美,做的饭菜也是一绝。而且,它拥有两个大隔厅,若有人想要包场,这里是不错的选择。
黄昏时分,一众文人雅士陆续来到,进了张择檩之前订好的雅间“麻姑洞”。
终于,人来的七七八八,才见张择檩坐着他那顶不显眼的小轿,来到白玉楼。
陈秀波已提前到了,但却没有进麻姑洞,而是坐在大厅里。
他一张脸颊好似白玉一般,面容秀雅,黑长的眉毛乌压压延伸向鬓角,一头青丝用玉环束在脑后,袖袍宽广,端坐于喧闹的大堂,一时间,衬得周围的一切都像是他的背景一般。
好一个神仙样的人儿。
见了张择檩进来,陈秀波眉头微挑,露出欣喜之色,张择檩快步到跟前,挽住他手臂,亲热道:“叫陈兄久等了。”
“哪里的话!我愿多等的。”陈秀波一双眼睛波光潋滟的看了看张择檩,开心的说道。
陈秀波身后抱琴的童子早对这一切见怪不怪,跟着张择檩和陈秀波进了麻姑洞。
屋里的各地才子们正在闲话,张择檩迈步进来,所有人都起身对着他行礼,同时也对他亲热的挽着的陈秀波一阵好奇。
陈秀波生的清俊貌美,叫人见之忘俗,又被张择檩这么高看,那些秀才们也忍不住对张择檩生出了好奇心,等着叫张择檩给他们介绍,这位青年才俊到底是哪家的子弟,竟这般温良如玉。
没想到张择檩到了场上,反放开了陈秀波的手,自己上了主位,屋里的好位子早就被占了七七八八,他也不挑,捡了离张择檩较远的一处角落里坐下来,不声不响。
张择檩扫视全场,见不少人都带了伺候的随从,笑道:“今日诗会,我们自得其乐便好,各位带来的家人,且出去歇息一会儿吧。”
既张择檩都发话了,旁人无敢不从,和快屋里就剩下参与诗会的十几人。
诗会立刻开始了,除了神秘的陈秀波以外,旁人很快打成一片,你接我续,只有陈秀波一直三缄其口,只将将眼神锁死在张择檩的身上,偶尔一笑,好似春波轻漾。
诗会越来越热闹,人们慢慢的喝的高了,除了几个酒量不错的还有一丝清明外,很多人已经是迷迷瞪瞪,不知道身在何处了。
张择檩喝得不多,陈秀波也未沾几滴酒液,在东倒西歪的伺麻姑洞中,这两人分外明显。
眼看别人酒力不支,纷纷倒地,陈秀波弯腰从旁边将琴拿起来,放在案上,遥遥对张择檩道:“大人,秀波不才,献上一曲于大人听。”
他不但人生得好,声音也非常悦耳,一开口,好似有羽毛撩拨在人的耳朵里一样,听得人心痒痒的。
张择檩笑着点头。
古琴被放在桌上,陈秀波挥舞十指,测了测琴音,露出洁白的腕子,开始拨弦。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场上的这些才子们,基本都修习过君子六艺,就算是那些没有专注连过琴的,鉴赏的能力还是有的。
只听那琴声泠泠,一会儿如清泉,一会儿如春花,低处缠绵,高处清越,听得人心动神摇。
琴声忽的一转,一个黄莺出谷般的男声唱了起来:“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歌声如梦如幻,听得这些醉汉们不禁的一阵儿神往,恨不得自己也成了襄王,有神女如梦来。
张择檩看向陈秀波的眼神儿,越来越亮,嘴角的笑容,也越发的大起来。
陈秀波的琴艺好极了,不用看手下的琴,就知道该弹哪处,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张择檩,将这首曲子唱了一遍又一遍。
若此时席上有任何一个真正清醒的人,便能看出不对来。可惜,人们都醉得太狠。
终于,陈秀波停了琴声,看向已经快要烧尽的屋内的蜡烛,嗟叹一声:“大人,该回了!”
张择檩才四十多岁,因保养得益,看起来半点不显老,唯有一股成熟男人风流,越过重重东倒西歪的秀才,张择檩上前扶住了陈秀波的手腕:“波弟,你喝醉了!”
“张世叔!”陈秀波轻轻一挣,一根一根掰开张择檩握着自己手腕的五指,回手一扯,把束发的玉环扯了下来,放在张择檩的手心里:“今日不可。我先走了。”
说完后,怀抱古琴,衣袖飘飘,率先离开屋子。
张择檩手心放着那枚冰冷的玉环,好像上面还沾染着他主人冷香一般,露出个温和的笑容。
约莫半个时辰以后,严清歌的手里,读了一封信。
读着信上的内容,严清歌吃惊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她早先叫人去查陈秀波的身份,得到的结果,已经够出人意料了,没想到还有更劲爆的事儿在等着她。
本来她只是查出,陈秀波本是官家子弟,小时候家里落难,年岁不够的他本不用流放,但是人情冷暖,亲戚们不愿收留他,年幼的他为了果腹,进了教坊。
因天生在音律上有才华,现在的陈秀波,其实已经在市井间小有名气了,只不过之前他用的都是自己的花名,叫做玉珏公子。
传闻中,玉珏公子比那些女伶人唱歌弹琴要好听的多,长得也非常美丽,很多富贵人家想要请玉珏公子弹唱,一掷千金也难求。
还传闻,玉珏公子好南风,曾经被一位富商包过一段时日,后来那位富商从京城回了老家,他才又出山了。
但自打半年前,玉珏公子又消失了踪迹,不知道是不是又被谁包了下来。
这种市井间比较出名的伶人妓子,从来都是层出不觉的,各个都红不过五年,所以严清歌竟是根本没有想到,她重生前地位那样高的陈秀波,居然还有这般不堪的过往。
再结合张择檩邀请了陈秀波参加诗会,严清歌的脑门突突的,她可不觉得张择檩会邀请别人包养了的小倌儿,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陈秀波现在就跟着张择檩!
也就会说,张择檩他也好南风。
其实好南风的大臣,在朝廷里也不是没有,只是根本没有一个能够做到张择檩这样的高位上。
而他,现在如此得重新,必然也是因为他还没有暴露。
严清歌的心中兴奋的战栗起来!这是个大好的机会,她一定要把握住。
“去查陈秀波住在哪儿。”严清歌颤抖着嗓子说道:“守好了那里……盯紧了,若是他要买人,找机会安插咱们的人进去。”严清歌吩咐连翘道。
连翘温声称是,倒退着下去了。
时间过得飞快,眨眼就到了七月底。
这中间,严清歌挡退了好几波柔福长公主派来刺探的人。
而且,她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在店铺的周围,有柔福长公主派来监控她的人。
但严清歌今非昔比,身旁伺候的,全被她换成了自己新买来可信的丫鬟、婆子,甚至连之前伺候阿满、炎婉儿的奶娘,都被全换了。
在这儿工作的绣娘亦是从市井里被招收来的,各个手艺都不错,她们的住址、家人严清歌都是知道的,连打带收,这些绣娘们绝对不肯冒着丢了这么高额薪金活计,家人也会受到牵连的可能性,去出卖严清歌的。
仅剩下了三两个炎王府的旧人,都被安排了做无关紧要的事情,连严清歌的屋子都进不了。
这一日早上,严清歌才吃过饭,准备在屋里改一改这几天画的绣图,忽的,外头看门儿的怀菊急匆匆跑进来通报:“炎王妃娘娘来了,已在门口下马车了。”
严清歌一惊,柔福长公主还是信不过她,亲自来突袭查看了么?
幸好,她基本上不出门,但在家也是打扮的齐齐整整的,赶紧站起身,道:“还不快去接娘娘。”
说话间,柔福长公主就已经越过庭院,长驱直入,进了屋子。
她一双凤目有意无意的落在对她行礼的严清歌身上,道:“清歌,快收拾收拾,和我进宫看修羽去。”
之前柔福长公主曾说过,炎修羽在宫里面闹得厉害,想要见家人,太子爷答允下来这个要求,可是她都回来三个月了,就没听柔福长公主提过。
严清歌高兴的好像做梦一样,赶紧叫人服侍着自己穿衣打扮。又想赶时间,又想打扮尽量好看点,恨不得立刻就完完美美的出现在炎修羽面前。
柔福长公主坐在外面喝茶,一双眼睛紧紧的打量着严清歌客厅里的装扮。
只见客厅中收拾的很是素净,虽然空间不大,但因为家具少的缘故,所以看起来并不显得拥挤,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也不见有任何男子留下的痕迹。
空气里燃着淡淡的熏香味儿,以前在严清歌屋里她就闻见过,是严清歌每次吃完饭后才点的,能够祛一下饭菜的余味儿。
桌面上,放了几卷纸筒,柔福长公主伸手拿过来,展开来看,是几幅花样子,便又放下了。
屋里伺候的几个丫鬟静静的看着柔福长公主,知道这位是个厉害的角色,半句话都不敢吭,生怕说错什么,对严清歌不好。
才过了一刻钟,严清歌就从屋里出来了。
她薄施脂粉,容光焕发,眉宇里全是期盼和兴奋,身上是穿花百蝶齐胸襦裙,外罩一件碧绿的长袖纱衣,腰间系着浅蓝腰带,头发挽成坠马髻,插了套宝石步摇,粉面含春,道:“嫂嫂,我们这就走吧。”
倒是干脆利索,不像是心里没有炎修羽的!
柔福长公主道:“好!我们走吧!”说完后,打头离开了绣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