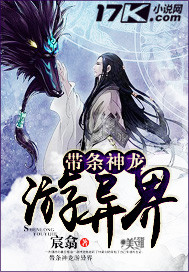“禀将军,冯大夫回来了。”石后平静的声线传进了帐篷里。
以青从沉思中惊醒,高兴地站了起来:“太好了,快请我师傅进来。”
“太好了,”石亨学着以青的话,凉凉的说道:“本将军也有话要告诉她。”
“干嘛?”
话音未落,冯王平便一掀帘子走进来,身后跟着一脸严肃的石后。
冯王平的褐色衣衫已经换成了月白色的袍子,一尘不染,衬得她白白的脸上平淡无奇的五官散发出柔和的光来。
她一边揉着后脖子,一边大步的向石亨和以青走去,一屁股坐在小榻对面的椅子上,眼睛扫过以青的衣服箱子,撇嘴道:“干嘛?要背叛师门?快过来给我揉揉,这该死的莽夫,居然下了死手,不就砸了他几个盘子么……”
以青听冯王平自顾自的嘟嘟囔囔,条件反射的就朝她走去,已伸出去的手却被石亨一把攥住:“冯大夫,青儿以后就不再跟着你了。”
冯王平眉心一跳,坏笑道:“怎么?不跟着我,难道要跟着你了?”
以青连忙摇头想要辩解,就听石亨说道:“正是,大夫果然聪慧过人。”
“想走,总得给个说法吧?当我那儿是菜市场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说法?”石亨笃定地翘起嘴角,扯开得意的弧度,“你的徒弟已经死了,可再怎么跟着你呢?”
死了?
以青反应过来,指着自己的鼻尖说道:“死了是死了,不过是刘阿十死了,对么?”
石亨深深看了她一眼,笑道:“一点就通。”
以青看着冯王平以为她会大吵大闹,谁知道,她却没做什么反应,只是略带惋惜的说道:“死就死吧,人死不能复生。不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么,青儿啊,你节哀吧。”
“大夫,以后你就要改口了。”石亨善意的提醒她说。
“怎么?叫刘十一?”
“不,”石亨刚刚想到了保护以青的办法,郑重将以青介绍给冯王平,“叫石彪,今后就是我的亲兵了。”
石彪?
石亨的义子石彪?
连累他被弹劾的胡作非为的石彪?
居然是我?
怎么可能是我?
以青愣在当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好啊,石彪,我得去悼念一下我可怜的徒儿了,你就留在这里,好好地当石将军的亲兵吧。”
冯王平说的话惊醒了以青,她轻喊道:“不!我不要做石彪,我不要!”
“青儿,其实叫什么有什么要紧?是什么,才最重要。”冯王平以为她不喜欢这个名字,轻拍着以青的肩膀,脸色难得正经了起来,缓缓说道,“而且,月华楼那位已经知道了你的名字了,意味着,你已经不再安全了。得,就这样吧,你们俩慢聊,留步吧。”
冯王平说完,就转头走开了,如来时一样,脚步匆匆。
“冯大夫,留步。麻烦你看看青儿没事儿了吧?这背上可有内伤?还有,最后被我打散的暗器放出的蓝色烟雾可有不妥?”石亨忙叫住正准备离开的冯王平,连声问道。
冯王平并未回头,只是用轻快地声音答道:“放心吧!‘石彪’一时半会儿死不了。走啦!本大夫还饿着呢!”
“姐夫,师傅这样说,我肯定是没有大碍的。 ”
以青奇怪冯王平的反应,这么好说话可不像她的个性。
“虽然是这样,青儿你还是要多休息,来,快坐下。”石亨牵着她的胳膊往小榻上按下去,却看见了榻上灰白的垫子上一抹触目惊心的红色。
血迹?
常年在战场上厮杀的石亨,怎么可能会认错?
“青儿,你流血了?哪里受伤了?”
啊?
以青并未感到身上有疼痛的感觉,抬抬手臂,伸伸胳膊,正纳闷间,忽然感到下腹一股暖流流出。
不会吧?
红霞飞上了以青白嫩的脸庞,好像一个红红的苹果,连小巧精致的耳朵都变成了粉红色,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变声药的后遗症出现了,这月事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偏偏在石亨的眼皮底下来了,尴尬死了。
这要怎么跟他说呢?
石亨见以青涨红了一张脸,不说话,忙握紧她的手臂,紧张道:“到底哪里受伤了?嗯?青儿?”
以青不肯抬头,一下子坐在了那点血迹之上,拨弄着自己的手指,一声不吭。
别问了,这叫自己怎么说呢?
“算了,石后,去请冯大夫。”
石亨想既然以青不肯说,就只能让冯王平来了。
哎呀,自己肯定会被冯王平狠狠地嘲笑的。
拒绝的话刚到嘴边,冯王平就被请了进来,原来她还站在外边,没有离开。
冯王平慢悠悠的踱步到以青面前,伸手按着她的脉搏,片刻后,笑道:“去给她煮一碗姜糖水来。”
“就这样?”石亨追问道,“不用开药么?”
“当然不用,你最好也出去一下,”冯王平也坐在了小榻上,笑道:“等‘石彪’换上干净的衣服,你再进来。”
“石后,去煮水。冯大夫,跟我来。”石亨疑惑的看着奇怪的两人,打算叫了冯王平出去问个究竟。
“她到底哪里受伤了?”
还未等冯王平站稳,石亨的问题就冲出了口中。
“她没受伤。”冯王平平静的说道。
“没受伤怎么会流血?”
“唉,”冯王平叹了口气,缓缓答道:“因为她的葵水来了。”
石亨听后,脸色一僵,难得出现怔忪的眼神,“咳咳……”,他不自在的清了清嗓子,“哦,我去厨房看看,姜糖水怎么还没好。”
微风吹起了冯王平耳边的碎发,她抬头定定的看着石亨远去的背影,脸上的平静裂开了一道缝隙,目光变得凄迷起来,薄薄的唇坚定地抿在一起,求而不得,不如不求。
自己不是早就知道了这个道理么?
这样的身世,还要奢求什么呢?
“冯大夫,你在这里。”
一个熟悉的脸孔映入了眼帘,来人正是驸马府的护军统领,他双手抱拳,躬身道:“大人听说了今天下午的事儿,给您送来一封信。”
冯王平从他的手里接过一个信封,心中冷笑,看也不看的揉成一团,对来人说道:“你转告他,我很好,不劳他操心,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找我,我很忙。”
自己算什么呢?
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罢了。
自己的爹是本朝驸马宋瑛,娶得是成祖皇帝的四女儿,咸宁公主。
咸宁公主为人专横跋扈,狠毒善妒,自己的母亲是父亲年轻时的收房丫头,在咸宁公主嫁过来一个月后就被赶出了驸马府,那时,已经怀有两个月的身孕。
母亲千辛万苦生下了自己后,东躲西藏的过了九年,因为漂泊无依,生活困苦,也渐渐地油尽灯枯了。
母亲临死时,将自己托付给了懦弱无能的父亲,父亲老年得女,虽然高兴,却忌惮着家中悍妻,又因为自己一直是男子打扮,便安排在军营之内,只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石亨一人。
咸宁公主接连害死了几房姬妾后,也得到了上天的惩罚,这一辈子都没有生育,也在九年前病逝了。
可恨的是,她却命令自己那所谓的爹今生不再娶妻,等他百年之后要葬在一处,死而同穴,做生生世世的夫妻。
因为这样,自己也就永远不被承认,永远不能名正言顺的认祖归宗。
认祖归宗?
还不稀罕呢?
自己虽然相貌平平,却也有一身本领,何必要靠别人?
没有他们,自己一样过得很好。
就像,自己从来没觉得一个男人对自己有多么重要,这个男人,就是石亨。
自从来这军营里,谁都知道新来的冯大夫是个脾气古怪的白面书生,不好相与,所以也没有人与自己有来往,这正合了自己的心意,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困苦生活,心中隐隐藏着父亲的不满吧,自己恣意妄为,口无遮拦,在言语伤害别人的时候,也宣泄着这么多年被忽视的痛苦。
石亨是唯一一个知道自己身世的外人,面对自己的古怪脾气,他既无轻视,也无殷勤,只是平等有礼,反而成为了这里唯一让自己觉得轻松自在的人。
何况他又高大俊朗,温文尔雅,可是当自己知道他已有婚约时,就不得不断了曾经一闪而逝的念头。
因为她不想自己再做第二个母亲。
可是,那一年,他回来了,随之而来的除了一个小姑娘,还有他成亲当日新娘横死,并立下永不再娶誓言的传言。
永不再娶?
他与自己那个爹一样都立下了这样的誓言,不过一个是被逼无奈,一个是为什么呢?
情根深种么?
金山大捷,高兴地他不禁喝多了,就是那晚,自己知道了这个誓言背后的故事,原来是因为另一个承诺,因为另一个人,就是他带来的小姑娘朱以青,也知道她的身世和秘密。
也是因为这样,自己才同意收她为徒,并倾囊相授。
以青聪明,悟性也高,有着不属于孩童的豁达和包容,自己也渐渐明白,石亨将尚年幼的她引为知己的原因了。
只是,自己却也陷入了那样曾经不屑一顾的怪圈里。
明明知道不可能,却在跟自己别扭着。
明明知道石亨不可能再娶,却会梦到自己一袭嫁衣。
明明知道石亨看渐渐长大的以青时,眼神像一口深邃的井,却选择无视和嘲笑。
无视那样的昭然若揭。
嘲笑自己的看不透,道不明。
也许,这就是自己的宿命,总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出生,不合时宜的归来,不合时宜的心动。
也许,自己就是这样别扭的个性,知道那个爹咳嗽的旧疾复发,想送药给他,却没拿出手;知道他期盼和自己吃顿饭,却仍旧冷了脸,独自去酒楼用餐;知道以青是个路痴,却故意为难她,让她在街铺林立的路上找自己。
就像,明知道石亨不在乎自己,却对他的漠视感到心痛。
他从不曾正视过自己,自己好像一颗小草,如此渺小,如此卑微。
不是早就知道,自己与他之间就像隔着银河一样,永不相交么?
怎么仍要做出那样的举动?一再地证实自己在他心中的无足轻重?
冯王平轻轻的闭上眼,迎着风,低低唱了起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驸马府来的人还恭敬的站在她身后,听到这样婉转悲伤的调子,不禁奇怪,这冯大夫一向目中无人的,怎么,还会伤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