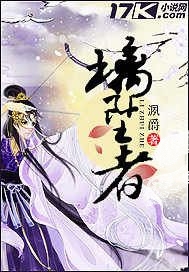慕容予桓的面色和缓了下来,而太后的面色却浮现出一丝忧意。她抬眼看了看石鸿昆,石鸿昆蹙了蹙眉头又去看吴之泰,吴之泰会意又看向令狐齐安,可令狐齐安却也蹙了蹙眉头,一脸茫然之色。
令狐齐安的神色丝毫不落的全都看进倾城的眼中,倾城暗暗一笑,心中更加有了底气,抬首继续道,
“在臣妾和亲之前,臣妾的几位姐妹已被派去伏国和亲,正因臣妾的哥哥已在大周为质十余年,顾念到臣妾的母妃膝下空虚才留下了臣妾。后来哥哥私逃回了施车国,王上为此震怒,为了弥补哥哥的过失,此次和亲周朝便派了臣妾而来。王上虽有心惩治,但毕竟顾及到臣妾在大周的颜面,这才让臣妾以青城姐姐的身份出嫁和亲。”
倾城说到这里,龙安殿上悄无声息,人人都在分析着倾城这话的可信度。石蓉绣转了转眼珠儿,淡淡开口向慕容予桓道,
“皇上,那南宫王子在大周为囚客那么多年,他可有提起过他还有个嫡亲的妹妹吗?臣妾倒没有听说过。”
慕容予桓听石蓉绣一问,也仔细的回想着,然而,他先是皇子后是皇帝,前途一片光明灿烂,哪里有闲工夫去听一个囚客说些什么。别说是嫡亲的妹妹,他现在都回想不出来他是否与南宫忆仁说过话。
齐若月坐在一旁并不说话,只在掐指计算着什么,然后方转首道,
“太后,皇上,臣妾方才算了一下,嫣妃生于施车国文吉十七年,也就是大周宣德二十六年,臣妾记得南宫王子正是宣德二十七年来大周的,也就是说南宫王子离开施车国时,嫣妃还不满周岁,尚在襁褓之中。南宫王子在大周十余年,想来对那个他走时才刚刚出生的妹妹并无多少印象,因此平时不常提起也是有的。”
慕容予桓闻言缓缓点了点头,太后面上的忧色更重,突然开口道,
“令狐齐安,她说的可是真的?南宫王子可曾当真有个嫡亲的妹妹吗?”
“这……”
令狐齐安又是好生为难,不知该怎样作答。倾城见了,紧紧盯着令狐齐安,不慌不忙的道,
“你既是施车国的宫奴,那一定知道王宫中的事,太后问话你据实回答便是了。青城姐姐的母妃尚在人世,本宫的母妃和哥哥也就在施车国中,你说的话是对是错一查便知,谅你也不敢扯谎!”
听了倾城的话,令狐齐安更加慌乱不安,一张脸紧张得苍白起来,他看了看倾城,又看了看吴之泰,最后只得一俯身向着御座上道,
“皇帝陛下,太后娘娘,奴的老国主有许多姬妾,奴并不知道哪个姬妾有几个孩子,也分不清哪位王子或公主的母妃是谁。奴只是一个在子同门外洒扫的下等宫奴,但奴所说公主自尽而亡之事却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奴并不认识她!”
慕容予桓还未说话,和嫔孟惜蕊轻笑了一声,道,
“你既不知王宫中有几位公主,也不知谁是谁的孩子,想必你自也分不清自尽而亡的究竟是哪位公主。你既是个在外庭洒扫的下等宫奴,自然也无福得见公主真容,便是你不认得嫣妃又有什么稀奇!”
孟惜蕊说罢,转向慕容予桓柔声道,
“皇上,依嫔妾之见,这个奴才的话全然不可信!”
“不是的……奴是……奴只是……是……”
令狐齐安还在试图辩解,慕容予桓则若有所思的沉吟不语,倾城见状指着令狐齐安向慕容予桓道,
“皇上,您可否准许臣妾问他几句话?”
慕容予桓略想了想,随即点了点头。
柳丝膝行过来扶住倾城,倾城吃力的撑起酸软麻木的双腿勉强站了起来,她扶着柳丝的手,忍受着双腿久跪后甫一伸展而带来的针扎般的疼痛,行到令狐齐安的面前,淡淡的道,
“你说你是施车国的宫奴,那本宫问你,你是什么时候进入王宫为奴的?”
令狐齐安略思索了一下,回道,
“奴是文吉二十八年入宫为奴的。”
倾城不置可否,又问道,
“那你又是什么时候逃出王宫的呢?”
令狐齐安这一次回答得倒快,道,
“奴是在泰安二年逃出王宫的。”
文吉是南宫仲迟的国号,泰安则是南宫忆英的国号,倾城听了缓缓点了点头,道,
“这么说,你在父王在世之时就进入了王宫,在王宫中也有五年了,就算一直在外庭服役,王宫中的大事倒还是知道的。”
令狐齐安道,
“正是,奴虽不常出入内庭,但国中大事还是有所耳闻的。”
倾城冷笑一声,道,
“是吗?既如此如何连青城姐姐的母妃,父王第十二房的玉王妃早已去世多年的事都不知道呢?”
倾城将“早已去世多年”六个字咬得极重,令狐齐安听了不由得一颤,忙辩解道,
“奴是文吉二十八年入宫为奴的,太早之前的事情自然是不知的。”
倾城听了发出一声清脆脆的笑,随即摇了摇头。柳丝在一旁接口道,
“什么太早之前的事?玉王妃是在青城公主自尽后不久才去世的。青城公主花季折损,玉王妃心痛不已,这才一病不起堪堪谢世。你既在王宫为奴五年却如何不知?方才娘娘说‘青城姐姐的母妃尚在人世’,可你却没有半点疑惑,这便可说明你根本就不是王宫的宫奴,而是假冒的!”
令狐齐安一听,慌忙摆手道,
“不,奴当真是王宫的宫奴,奴是私逃出来的!老国主有那么多姬妾,王宫中又有那么多王亲贵胄,日日有红白之事,奴哪里能记得那么多呢?但公主违抗王命拒不和亲,又因此自尽而亡,这样惊人的大事儿奴却绝不会记错!”
倾城闻言,挑了挑眉毛,道,
“好!既然你一再强调对青城公主自尽之事记得一清二楚,那你就给皇上说说,当时你都听到些什么?”
令狐齐安转首向着慕容予桓道,
“皇帝陛下,奴记得清清楚楚,听说老国主为取得伏国的护持而欲与伏国结亲,便逼令公主和亲,公主不从这才……”
令狐齐安还未说完,倾城已向着慕容予桓跪倒奏道,
“皇上,方才辅政王和吴总领皆提到青城公主死于大周崇庆三年,其实则不然。青城姐姐是死于泰安元年,也就是大周崇庆四年,而下旨令青城姐姐和亲的也并不是臣妾的父王,而是当今的王上!这个令狐齐安对此皆一概不知,因此臣妾怀疑他根本不是王宫的宫奴!”
令狐齐安这一下彻底哑口无言了,吴之泰这时也慌了起来,恼怒的瞪视了令狐齐安一眼,随后又怯怯的看了看石鸿昆。
倾城继续说道,
“皇上,若他当真在王宫中五年,那他很有可能见过臣妾。可方才皇上问他是否认得臣妾,他竟连辨也不辨,只扫了一眼便说不认得,这岂不可疑?再者,若他当真于文吉二十八年便进入王宫,必会被王宫查宗记档,而王宫于泰安二年才开始施行宫刑,他若有查宗记档的话,是绝对不可能逃出王宫的,因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令狐齐安是在泰安二年王宫大批抓捕宫奴时被抓入王宫的,而在受宫刑之前便逃出了王宫,根本没有在王宫服役过!”
令狐齐安脸色更加苍白,张口还要狡辩,倾城回头向他道,
“你说你只是王宫中一个下等宫奴,每日只在子同门外洒扫,那本宫问你,子同门外的丹杏树是春天开花还是秋天开花?你日日在那里洒扫,扫了五年,别告诉本宫你不曾留心!”
令狐齐安苍白着脸,伸手指着倾城,张口结舌的道,
“你,你又要诈我!我自然留心了,丹杏树既不是春天开花也不是秋天开花,而是夏天开花的!这个你诈不了我!”
倾城看着令狐齐安,绽开了一个诡秘的笑。子同门外的甬道,包括那高高的天云台,倾城在施车国王宫做苦役奴时,曾一扫帚一扫帚的细细打扫了一年之久,如何会不知?她看着令狐齐安,一字一句的道,
“不错,你说的很对,丹杏树确实是在夏天开花的,不过,子同门外的甬道上种的并不是丹杏树,而是紫桐树!”
“啊!”
令狐齐安闻言惊呼一声,瘫软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