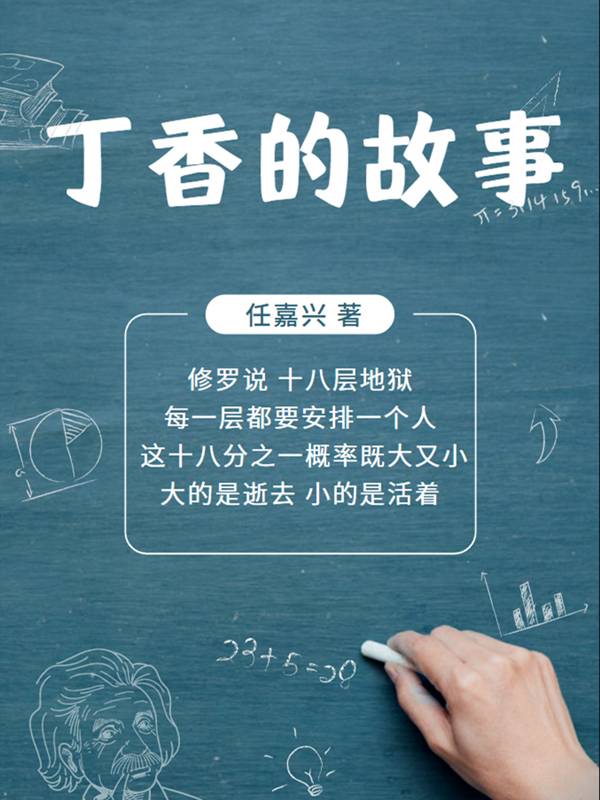“1939年9月20号0时0分,你共我同饮一杯冰茶。因为你,我会记住这杯冰茶,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杯冰茶的朋友。”
“人的一生中会有几多个冰茶朋友?我不知。但是,我知道的是以后的日子,每每见到冰茶时,我一定会想到你,不知当你看到或是尝到冰茶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我啊?”
站在黄昏分别的车站,回忆涌上心头却怎么也找不到要说的话,大抵这便是离别的模样吧。“即使没有你在我身边,我也可以照顾好自己”,明明是想这么若无其事地告诉她,但最后也还是未有说出这样的话语。独自走入车厢中,望向窗外那些匆匆略过的身影,想必他们是正赶着回到等待自己的人身边去的吧。而我此刻则却要在此分别,看见她垂着头的侧脸,眼泪都快要忍不住流下来了,也正是此时我也终于痛切地体会到为什么駅中人的眼中常有不舍。
加注完燃料的火铁拉响汽笛,预示着我即将离开这座城市,虽有不舍也只能是无可奈何了,喷射着火焰的引擎拉动着车轮滚滚向前,望着她渐渐消失的背影淹没于拥挤的人潮中,只留下过于哀伤的残留于我心。列车追赶着快要入海的夕阳很快地便驶离了莱茵兰向安斯克行去。
自改札口走出的时候,这座城市的雨也快要停歇,又一个平凡的夜晚就这么降临了。
独自走在雨后的街道,有关她的思绪再次涌上心头。“我真的好想忘了你,如果不能再见到你的话,那就忘掉心中全部的你。”我是如此地对自己说到。走进路边冷饮店,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望向窗外,只有凄清的街道,昏暗的灯光,以及形单影只的行人。“忘了吧,喝了这杯冰茶就忘掉吧。”言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沉寂有好长一段时日的恩尼格码机发出了响声,在纸上敲出了一行短短的字符,于1939年10月7日晚夜10点40分。
“你有时间吗?可以挂个电话聊聊吗?”
“当然可以,我点会无时间啊。”
尽管那时我正与朋友话聊不久后便要装备中队的新式战机,不过我还是拿起了电话打了过去。
自离开莱茵兰后这是我们的首次联系,但未有一丝的生疏之感,仿佛回到了于莱茵兰假日时的那般熟悉,可以什么都不想,就这么愉悦而放松地聊,自现实走进飘渺。大地已然寂静,连蝉鸣都已消停,电话线的两头却依旧不倦,直到漆黑的夜令我发梦为止。
梦中,依稀还记得在某种场合她将电影票塞与我。接着也不知是怎么地便来到了火车站,就在我还未来得及搞清楚电梯与走道构造时,她转眼间消失了。最可恨的她,也不知用了什么魔法将我引到那巨幅的玻璃前,透过那块玻璃,能十分清楚地看见她,早已排队于札口前的她。
我竟一瞬便瘫坐在地,没了力气,眼泪止不住地流,将紧紧攥于手心那两张快要开场电影票揉捏的破碎。临检前她望向我所处之处,微笑着向我挥了挥手,走进札口,二度消失,在目能所及的地方。似乎一切早有预谋。
刚从梦中醒来,曾做过的梦竟一幕幕在我脑海浮现开来,那是我大抵都已忘却,但现在却又清晰的离奇。仿佛梦是一体的,无数的月台、駅前还有换乘车站又出现在我的记忆中。而随着大脑的逐渐苏醒这种清晰的感觉也愈发模糊,我想若不能及时记下大概又会很快忘却没了踪影。
回放脑海里那些关于梦的模糊记忆里,她又出现在了来来往往的电车与公交上,同我一道。窗外偶尔景色甚好,那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步行街道上,铁质招牌正于风中摇曳,迷雾充盈的沿江路桥连接着绿茵环绕的山间小径。我能肯定这些回忆碎片并非源于某一次,而应是数次梦境慢慢构造起来的。或许梦中我就与她生活于那座城市,也许梦中的我是同她置身另一个世界,那之他我大抵也会梦到此我的生活,也会困扰于刚醒来的时候,亦不知到底这无数奇怪的梦所组成的迷幻记忆源于自己亦或是来自其他。大概这便是我之所以对这梦充满无尽好奇的原因吧。
她究竟是谁?我不知。也不知若她真实存在,她会不会也和我一样经历这些奇幻的梦。
坐在街边咖啡厅,望着窗外阴霾的天搅拌杯中茶咖,心中喃喃自问。
安斯克的天总是这么阴沉沉的,时不时便会落下几颗雨滴,让人本就烦躁的内心因湿漉漉的模样变得更甚,不过好在有她。每每结束一日忙碌返回家中,简单收拾收拾便会坐到桌前,敲响恩尼格码机让字符顺着电讯线路爬上她的收信纸,紧接着便迎来那令人感到惬意的电话聊天,日复一日,终是如此,哪怕翌日一大早就得登上新机进行适航训练,依旧愿同她聊到夜深的静谧,迟迟不肯睡去。
同她话聊时到底是种什么感觉,对我而言是不可名状难以描述的,或许是孤独,或许是因为希望与人分享生活,谈谈人生聊聊理想云云,又或许是因为别的一些连我自己都猜不透的原因。大概人都是如此,希望有人同他分享自己的喜悦,互相倾诉烦恼,希望有人能够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不至于过分孤独地活着。
可是我发觉我错了,在1939年10月21日,我发现她不是她。
那天,在降落一架109G时我失手了,差点害死了同僚,因为真的太困了,连起落架都没放完就重重地摔在了跑道上,高速运转的螺旋桨挣脱了机鼻的束缚径直奔跑道另一侧正等待起飞的190D而去,还好没撞上什么。
瓦洛佳事后抓着我的衣领大骂,可是说实话当时我没什么感觉,因为太困了,只想回去睡觉,当然最后成了,他把我放了回去。
就在我满以为我盼来了难能可贵的睡眠时,她的电话转接了进来。
我用了及其敷衍的语气,尽可能简单的短语,只求能早点放下听筒,然后抱着枕头睡上一觉,可惜我想错了,她开始生气进而暴起,她觉得我满是敷衍,诚然事实确实如此,但我并不想解释什么,那一刻我觉得不被理解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她的语气仿佛在告诉我,我是做错了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我做错了什么,那应该是没有在过去的日子里好好睡觉,毕竟离了她我还能活,离了睡眠,保不齐哪天我就同战争女神坐在一起谈我那段苦短的人生了。
最后她带着愤怒的挂掉了电话,并声称从今以后拒收我的电讯,听她如此一讲,我感觉精神得到了久违的放松,唯一的想法便是不用再与她联系了,真好,至少不再会在驾机时打瞌睡了。
不过不久,她便开始主动发电讯给我,许多封电讯,或是认错,或是道歉。我看都没看就径直扔进了废纸篓,后来干脆拒收了由她发来的电讯。
电讯联系不上了,她又尝试通过其他方式,比如挂电话,但她的行为却令我烦躁到只好同接线员说,不必再接通那个地址打来的电话了,请转告她,我们已经结束了。
夜里,我梦到了她,消失在札口的那个她,她坐在暴风雪肆虐的山上,看着山谷中裹着单衣的地克琴军队艰难地向西溃逃。他们一路上不断有人丢掉燧发枪与弹药,也有人休克倒下,在其身后,维亚济马人的骠骑兵和龙骑兵正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他们并不愿意上前与那些饥寒难耐的步兵交火,就只是紧紧跟着给他们以无声的压迫感,顺带杀死那些掉队的无力反抗者,冰冷地了结一切。我们坐了好一会儿,她站了起来,沉默地拍掉凝于面罩上的冰渣,接着扬起马鞭一路疾驰,很快便没了踪影。
日子一天天过去,恩尼格码不再像前些日子那么频繁响动播报拒收,我猜她应该已经清楚了吧,清楚我们已经完结了。其实在那之后我也在想,为什么最初的愉悦到了最后是以这么不体面的形式草草收场,是因为她与我心中所想的她太过不同吗?可是她仅是个梦中人而已,一个我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过声的幻影而已。又或许是因为最初的夜聊只是一时兴起,一次两次倒也无妨,但当那种违背生理习惯的做法无限被延长,身体终是承受不住的,同样那本就不多的好感也在被迫营业的夜聊中被耗的干净了。
不得不讲,人的感情好容易就过期了,因为不久后我便寻到了新的她,而忘记了她,在1939年的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