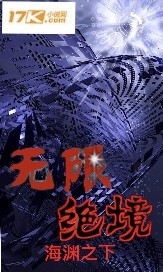一轮夕阳,泛着红晕游走在郭家庄的上空。那点红晕撒在远处的山尖上,托起一片片橙色的雾气;撒在近处的屋顶上,伴着烟筒里的炊烟袅袅升腾;撒在街道上,疏散了喧哗,一切渐渐地、慢慢地寂静了下去。
这个时候,姚訾顺敲开了许家的大门。
“你,你找谁?”冥爷嗞着一口参差不齐的小牙,斜楞着眉眼打开了一条门缝,他的头躲在门缝的里面,他如果再往前挪一点,那条门缝一定夹断他细细的脖子。
姚訾顺抬起眼角温和地笑了笑,然后双手抱拳,“找许老太太!麻烦您给禀报一声……”
冥爷扭着身子,伸出莲花指,把门缝扯宽一点点,他眯着一双小眼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的中年男人,“吆,好大的口气呀,许老太太的名号怎么会是你这号人随便喊的?瞅瞅你这一身破行头,你是货郎?哼,是讨口水喝,还是想找个墙角旮旯坐坐?还是想讨口许家的剩饭吃?”
姚訾顺急忙放下抱拳,他一边扭转身,一边气哼哼地说:“是许老太太请俺来的,您冥爷不让俺进去,也好,耽误了大事,看看您还能不能端得动许家这个饭碗?又能端多久?俺走了!”姚訾顺一撩长袍,一抬腿,迈开大步向前走去。
冥爷一听,身体一哆嗦,他挤挤小眼,姚訾顺嘴里的话不仅带着生铁味,还能直呼他的名号,他有点害怕,他急忙挤出了门缝,“您请留步,留步……俺马上去给您禀报一声。”
这几天因为许婉婷的事儿,许老太太寝食不安,模样削瘦了许多,面色焦黄,更憔悴,走路都抬不起双腿,但,当听冥爷禀报说门口有人找,她一下来了精神,“直管家,快去把来人请进堂房!”她又急忙转身喊赵妈,“赵妈,快,快给俺梳梳头……”
姚訾顺被冥爷带进了许家的堂房。
许老太太在赵妈的搀扶之下挪着小步从穿堂屋迈进了堂房。
她一抬头,眼前的中年男子她不认识,她满脸疑惑,她猜测眼前的陌生人突然到访一定是与婉婷的事儿有关。
“先生,您找谁?”
姚訾顺躬身抱拳施礼,“老太太,您好!”
姚訾顺一边说,一边扭脸看看站在门口边上的冥爷。
许老太太多聪明呀,她抬抬眼角,瞄了一瞄院里,气息低沉:“直管家,劳烦您去大门口盯着点,大少爷他们也快回来了,也许还会有其他人找上门来,无论是谁都让他们进门说话……”
“好的,老太太,俺马上去!”冥爷眯着笑眼退着步迈出了门槛,他一转身换了一副嘴脸,一张恼怒的脸,嗓子眼里气哼哼地絮叨着,“有什么事情还要瞒着俺呢?”
“许老太太!”姚訾顺向前一步,再次躬身施礼。
“您,您坐吧!”许老太太抬起手指指姚訾顺身旁的椅子,一边扭脸看看身旁的赵妈,“赵妈,您先下去!”
“是!”
看着赵妈踮着小脚离开了堂房,许老太太忍不住了,她开门见山,“先生,如果没猜错,您是为我家小女婉婷之事儿来,是吗?”
姚訾顺点点头。
许老太太长吁一口气,她一边走到椅子旁,她准备坐下,她身体踉跄了一下,她急忙抓住扶手,再次转过身看着姚訾顺,放慢语气,“昨儿,舅老爷屋里丫头已经告诉了俺,俺也放心了不少,今儿看到先生您,俺更放心了,您一身正气……”
“许老太太您过讲了,府上小姐不是俺所救,惭愧啊!”
“奥,先生,您说什么?难道您不是为我家小女而来?”瞬间一层乌云笼罩在许老太太脸上。
“不,不是,您不要着急,府上小姐平安无事……”姚訾顺把夏蝉救下许婉婷的事儿告诉了许老太太。最后他又说:“今早上,俺去看过小姐,她很好,只是受到了惊吓,精神状态不佳……”
许老太太全身哆嗦,“她,她没事吧?……”
“她很好!那一些贼人没有伤害她……许老太太,您是希望小姐快点回家吗?”
“先生,您什么意思?您需要多少钱?才……”
姚訾顺连忙摆手,“许老太太,您老误解了俺的意思……今儿,俺长话短说,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俺今儿来许家主要想见见舅老爷,不知可否?”
“见,见舅老爷?找他有什么事儿?”虽然许老太太嘴里这么问,此时她心里已经顾不得舅老爷了,无论来人找舅老爷做什么,她都不会阻止,“赵妈,您带这位先生去见见舅老爷,然后您与我去一趟弯头村。”
看着眼前满脸焦灼的许老太太,姚訾顺急忙安慰,“许老太太,您千万不要着急呀!”
“俺能不着急吗?俺现在、马上就想见到俺的女儿……”许老太太顾不得礼数,她瞬间泪水涟涟。
“您老稍安勿躁,俺已经安排人去保护三小姐,天黑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三小姐平安送回家。”
“真的?太好了!”许老太太一惊、一喜,依然满脸泪,“谢谢先生了!……赵妈,快,快,带这位先生去见舅老爷!”
舅老爷屋里。
海秉云斜着身体躺在床上,他手里举着那杆长烟袋,他大口大口地嘬着,把他瘦瘦的腮帮子都嘬瘪了。满屋里乌烟瘴气。
江德州坐在床边旁的椅子上,他眯着眼睛,似睡非睡。
顾小敏安安静静地站在门口边上,等着两个老人的支使。
少顷,海秉云一边晃着手里的烟杆,他嘴里一边气哼哼地絮叨着过往。江德州嘴里时不时发出“是”“您说得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海秉云磨牙凿齿的声音在烟雾里穿梭,“那个女人嫁给闵家,也不消停,那个闵文章多好的孩子呀,比他爹闵康承强百倍……俺真想一枪崩了她,替许家除了这个祸害!”
听到舅老爷嘴里的话,吓得顾小敏一激灵。她瞪着一双惊慌失措的眼睛一会看看江德州,江老人一脸惊恐;她一会儿看看床上躺着的舅老爷,烟火笼罩在舅老爷的脸上,只看到他一双眼睛里闪着愤怒的光。
她以为只有坊子矿区的张喜蓬和日本人有枪,她万万没想到和她住在一个屋檐下的舅老爷也有枪。舅老爷说他想崩了她,她是谁呀?怎么惹急了舅老爷?
“别,您可千万不能冲动,也别这么做!更不要这么想。”这是江德州说的最长的一句话,这句话带着颤音与惊悚。说这句话时,老人往前挺挺身体,直了直腰,使劲摇摆着一双青筋暴露的大手。
“一品曾说,连成的朋友在这边成立了一支队伍,好啊……听说那个人姓姚,江疯子您认识不?”
顾小敏又一惊。
江德州摇摇头。也不知海秉云看到了没有。
海秉云继续絮絮叨叨,“您不认识?您天天在街口转悠能不认识吗?”
江德州一边把他后背又靠在了椅子上,他一边不紧不慢地说:“不认识!”
这时,前院传来了脚步声。
“丫头呀,去看看前院谁来了?是不是来讨赏的?这一些人与那一些贼人有什么两样吗?眼里只有钱……”
“舅老爷,有位先生找您__”正在这时,赵妈的脚步停在了门口,“舅老爷,是老太太让俺带他来的……”
海秉云一抖身体,他想坐起来,可他只晃了晃膀子又躺下了。
一旁的江德州一边伸伸腿,一边打了一个哈欠,一边从椅子旁站起身来,他嘴里叨咕着:“他来了__”
“谁?你说谁?”海秉云抬起眉梢往门口瞄了一眼,“赵妈,谁呀?让他进来,俺没有体力去迎接他……”
姚訾顺踏进了海秉云的房间。
顾小敏见到姚訾顺又惊又喜,她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姚叔叔!”
海秉云听到了顾小敏嘴里的称呼,他“腾”坐了起来,同时他把手里的长烟袋往桌子上一扔,他向江德州伸出一只骨瘦嶙峋的手,“快,快拉俺起来!”
海秉云慌慌忙忙从床上蹿到了地上,他没来得及穿上鞋子,就那样把两只光脚丫踩在鞋子上,他抬起头,瞪大了一双深陷的眼睛,“您,您就是那个姚先生,是吗?”
姚訾顺急忙上前抱拳行礼,“是,海老爷,您一向可好!”姚訾顺转脸又向江德州深深行礼,“江伯,您也在,您也好!”
“听一品说起过您!快,快请!”海秉云有点激动,声音颤抖。
这是海秉云从没有过的举止与言谈,他对任何人都是冷冰冰的,今儿他有点反常。
江德州向姚訾顺点点头,站在椅子旁不再搭话。
“您二老先坐,快坐,俺小辈今儿仓促来访,是因为这件事有点棘手,俺也不啰嗦啦……”
海秉云一惊,他疑惑地看了一眼江德州,江德州摇摇头。
“海老爷,那个,那个罗一品被蟠龙山土匪掠上了山……”
“一品,一品,您说什么?”海秉云惊愕地瞪大了眼珠子,“扑通”一下,跌坐在了床沿上。
“海老爷,您别着急,俺今儿就是想问问您,以前听罗一品说起,您对蟠龙山的土匪有所了解,是吗?”
海秉云垂下头,哭丧着脸,“了解?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不知真假,可,他们不认识一品呀,这……这……”
一旁的江德州长长吁了口气,“舅老爷,您不要犹豫,这个时候人命关天,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江德州虽然一双大眼藏在皱纹之间,看着沮丧又消极,对海秉云毕恭毕敬,说话装疯卖傻,做事稀里糊涂。可老人深藏不露,他自小习武,又读过几年书,又上过战场,他可以委曲求全,更可以含垢忍辱,但遇事不乱,比海秉云更多了沉稳与智慧。
听了江德州的话,海秉云竟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真是祸不单行……唉!”他一边说着,他一边扶着床沿站起身来,他顾不得穿上鞋子,他光着脚丫,蹉跎着清瘦的背影,他扑到桌子前,他双手使劲拉开了抽屉,他哆里哆嗦地在里面翻找着。
一会儿,他手里抓着一块令牌转过身看着姚訾顺,说:“这是当年罗一品的父亲罗冯轩留下的义和团令牌……听说蟠龙山大当家的赵山楮曾在义和团待过……只是,谁能去一趟蟠龙山呀?”
“我去!”姚訾顺斩钉截铁地回答。
“给,你拿好了它。”
姚訾顺从海秉云手里接过了那块令牌。长方形的令牌是铜制的,金光闪闪,四边镶嵌着黑石,四角缀着蓝色水晶,中间一个“拳”字,这个拳就是当年义和团的名字,义和团又名义和拳。
姚訾顺手里攥着海秉云给他的令牌匆匆离开了许家大院,他踏着月色直奔蟠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