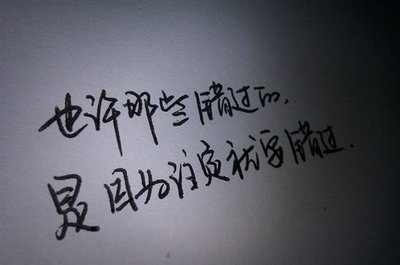邮局的工作说不上难但也不是很轻松,凌妃在物流分拣车间负责核对单号、分发快递。说是车间,但加上快递员一共五个人,除了组长是邮局的正式员工以外,凌妃和其他人都是合同工,与第三方公司签合同,交五险一金,每月到手一千八百元。快递员派送的件数较多时可能会有两千五百元到手,但毕竟县城体量有限,人口也有限,两千五已是最高工资。
当年高考完填报志愿时凌妃的爸爸让她报与邮局相关的专业,当时邮局对相关专业的学生毕业包分配,一毕业就是邮局的正式员工,每个月三四千的工资还离家近。凌妃不屑一顾,暗自觉得自己以后是挣大钱的人那些小钱入不了眼。她并没有听父亲的建议而是学了西班牙语。现在回头想想,或许当时确实是冲动了,那时候真的应该听父亲的话,起码工资可以多一半还是正式员工。
凌妃的家乡叫川平,是西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川平依托煤矿日渐发展壮大,近十年由于煤炭资源的枯竭一直在发展陶瓷业,但毫无起色。最近几年加上人才外流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凌妃从北京回来找工作时一筹莫展,她的家乡并不需要她的专业,还在招人的地方除了广场上的饭店就是房产中介。就连牛肉面店里的收银都必须和老板沾亲带故才有资格面试。
找工作的第一天凌妃就发现手机上找工作的各种App 在川平毫无用处,几乎没有工作会发布在平台上,但是爸爸妈妈很好用。在家里做了一周饭以后,周末的傍晚凌爸爸打完球回来以后给凌妃带回来了邮局的这个工作,凌妈妈则打电话告诉她加油站在招加油工人,一个月也是一千八,没有五险一金。
一股沉重的无力感涌现,曾经身无分文的穿梭在高楼大厦里找工作,在公交车上坐过站往公司狂奔,在地铁上被挤的侧头看别人手机时也未曾出现的无力感席卷而来。到都来,到这个年纪竟然要让父母给自己打听工作。凌妃很羞愧,她无法想象父母在他们朋友圈里的尴尬,也不敢想。可是她毫无办法。
家离邮局很近,步行十分钟就能到。每天早上九点邮车来卸货,下午七点邮车载货而来,中间的时间核对单号然后给快递员派件,再帮着装车。
凌妃很久没有在川平冬天的时候回来,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穿着来时那双带网眼的鞋,刚走到路上就感觉到脚上的凉意,跑回家换上一双雪地靴再冲出来准备扫一辆共享单车去地铁站时才恍惚意识到已经不需要了。以后她中午可以回家吃饭,还可以在家里的床上午休,也不用排队坐地铁等电梯叫外卖了。
车间像是小型仓库,有三条运输带,组长很友善,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介绍了凌妃,之后就各自忙自己的。当天邮车来迟了,九点半的时候才听到动静。凌妃帮着卸了货以后才明白自己买的快递箱子怎么都扭曲的不像样子。
司机站在货车最里面往出扔,同组的杨哥站在车厢卸货停靠的台阶上接应,凌妃站在台阶下负责聚拢丢的太远的小盒子。凌妃不知道这种卸货方式万一把别人买的易碎品和贵重物品摔碎了怎么办,但她看到司机大哥扔之前会大概看一下盒子上有没有醒目标注,杨哥也接的挺好基本没有掉落的快递便没有开口问。
十点的时候已经卸地差不多了,还有几个大件没办法扔,凌妃进到车厢里面挑了个行李箱大的箱子往出搬,为了方便核对把有快递单号的那一面朝上抱在怀里,抱在台阶下弯腰休息的时候就看见周泽深三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