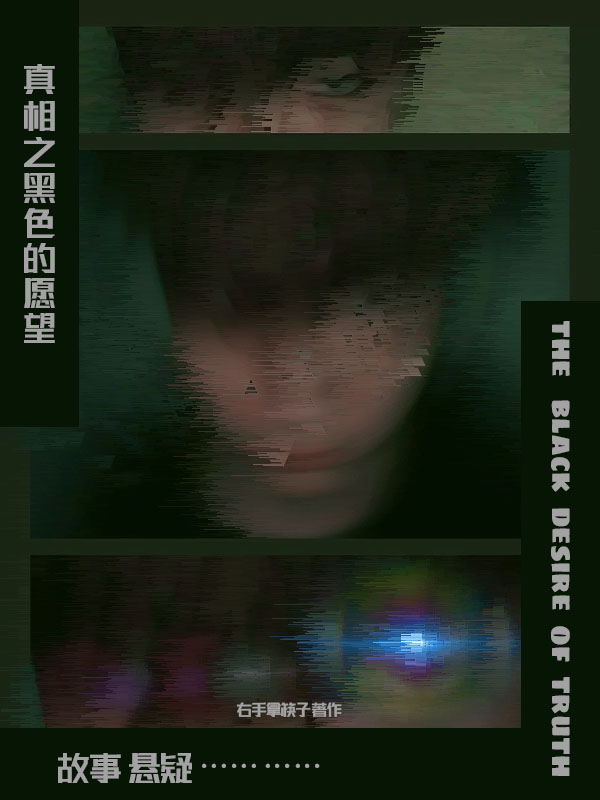雨势渐渐的小了下来,只是依旧不紧不慢的落着。
行歌一个大周天运完,听到雨水从飞檐上坠地的声音轻微了许多,便收了真元睁开眼来。屋内沉压压的歇息着五个人,空气都变得沉滞起来。他小心翼翼的站起身,走过去打开窗户,湿漉漉的风立时灌了进来,带着瀚海后街独有的油腻味。
行歌笑了笑,心想这瀚海城可真够神奇的。前街富丽堂皇只如天上龙庭,后街却破败的像是腐坏了千年的古物,连日瓢泼的大雨都不能淡化这股味道。
“又在听雨?”
行歌回头,余越儿睡得不沉,被这小风一拂便自醒转,正支着头看他。他笑了笑,又转头去看窗外。
“天都亮了,满眼的都是这聒噪的雨点,想听了听不进去了。不过就着小雨看看瀚海城倒是不错,我想我以后能这么看瀚海城的日子只怕是不多。”
“为什么?”
“说不出来,心里沉甸甸的,像压着重物,挪不走拿不掉,只能任它放在那……”
“是什么东西?”
行歌转过身来,坐在余越儿身边,问道:“你算过命么?”
余越儿一愣,随即笑了,点点头:“算过。我记得那老道士谈起我的因缘,说我注定会孤苦的……现在想来,只怕都是假的吧。”
“知道自己命数之后的惶恐……”行歌似乎并未瞧见余越儿两颊上升起的嫣红,自顾自的说道:“我心里的感觉大概就是这种吧。”
“你的命数?你不是说命数不可自推么?再说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道士,已经散去了自己的发髻么?还要学道士算命么?”
“我的命数不是推算出来的,似乎是本来就在那里放着。我一路走来,所到之处所见之人几乎都说着同样的话,他们说,是你啊……我不认识他们,也从未到过那些地方,可心底却像是突地腾起一团火,就将这种无法否认的身份接下来。”
行歌解下身后的长剑放在手边。
“这把剑名字叫做缘尽……苏铁心说它是一把凶残的剑,名字的意思是要斩断天下因缘。其实我心里明白他是对的,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缘尽说他借我杀敌的力量,却要用我一生的欢快和幸福来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相信一把剑,可很多时候,我总觉得真是这样,我走到哪里,哪里便是妖孽横行战乱突起,数不尽的人被杀死……”
余越儿想要说话,被行歌挥手制止。她看着眼前这个似乎永远大笑的男孩,这个永远要将所有人都拢在自己的臂弯里保护的家伙,这个一旦悲伤起来就让人心疼的笨蛋……她突然觉得其实他也不过还是个孩子。
两人不说话,屋里安安静静。
劫生从行歌怀里探出脑袋,蹭的跳上了余越儿的手心。她笑了笑,用手抚摸小貂儿光滑的皮毛。劫生在她掌心里舒服的伸了伸懒腰,又打起瞌睡来。
行歌忍不住也笑了起来,屋里淡淡的愁绪突地一扫而光。
“知道自己的命数又怎样?那老道士说我一生孤苦,或许说对了前半段吧,现在,我身边不是还有你……们么?”
行歌觉得他听到了这个似乎是有意的停顿,这句话像是一点火星落在他的胸膛,无边的幸福突地炸裂开来。那无边无尽的巨大欢喜奔腾起来,像是在心脏里放了一场焰火。他坐在那里手足无措,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坐,不知道两只手该怎么放……
“我也并不是傻子,从来就知道你的心意。这一路上走来,你围着我上下奔波,我也都是知道的……”
余越儿说着将手伸过去,轻轻碰了碰一旁坐立不安的行歌。
桌椅倾倒,屋内乱成一片。原来行歌浑浑噩噩,竟是应手便倒,倒下之时又顺势踢到了桌子。
屋内众人早已醒来,只是都不便出声,各自低着头装睡。此时再也装不得,莫三娘和遥戈的笑声清脆嘹亮,早窜到屋外雨中去了。
余越儿红着脸,低下身去扶行歌。
手还未碰到行歌,却见行歌突地站起身来,脸上凝重的表情带着些惊诧,直勾勾的盯着慧生。余越儿不解,转过头去,见慧生面如痛苦狰狞状,隐隐散发着宝相佛光,正是降妖除魔相。
其余三人被两人庄重的表情吓住,都安静下来,瞧向行歌。
行歌脸上表情变换,终于咬着牙齿说道:“城外军队要攻城了!”
行歌话音刚落,几人便突然闻到浓重的铁腥味。生铁的味道锋利如刀枪,穿透雨幕,直直刺向几人心口。
-
从城墙上往下看去,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如林的枪锋,点点细雨落在钢铁的林子里,如同掉入了黑色的深渊,没有半点声响。黑色盔甲和寒光闪闪的刀枪在城门前的平原上交错闪动,像是一面刀剑做成的大浪缓缓扑来。
城上守军多是城中百姓的子弟,即便不是,也自是南地的乡勇。世道已是安平数百年,这些过惯了太平日子的军士哪里见过这等阵仗,躲在箭垛之后犹自两股战战。
那面汹涌的铁流推至弓箭射程突然静了下来,整整齐齐的停下脚步。守城军士中有胆大的探头去看,见一黑甲将军策马而出。
那将军身着墨色环锁铠,披了一件黑色的大氅,胯下坐骑也是通体乌黑四蹄雪白的踏雪名驹,被身后数万军卒一衬,更显的威风凛凛。
那人走入弓箭射程二十步有余方才扯了扯马缰,立在原地打量城上军士。一人一马面对墙上数不尽的箭簇,竟是不带分毫怯意。
“我知道城中府尹大人早已逃窜,此时管事的是何人?出来说话!”
城上吵吵嚷嚷喊成一片,终于有一人被大家推举出来站出身来。那人生的实诚,大概是在同僚之中人缘最不好的,被推出来首先受死,立在城楼上两腿抖成了筛子。身下有人用手在大腿上拧了一下,那人痛叫了一声,终于张开了嘴。
“来人……可……可是程……程将军?”
城下将军在马上笑了笑,兜动缰绳转了个圈,大喝道:“正是程某。敢问城上将军高姓?!”
那人早吓得腿肚子翻转,抖抖索索半天,答道:“我……我姓朱。”
城下那人又一声大喝,笑道:“好!朱将军,程某前来是想告诉你一声,程某要攻城了,请将军做好准备!”
城上姓朱的中年人终于站立不稳,瘫软在地上。
城下将军大笑三声,掉转马匹,向阵中奔去。那城下大军气势如虹,一起大喊道:“出城受降,一人不杀!”
那一人一马眼见便要奔回阵中,突地城楼上利箭离弦之声响起,一道黑光划开雨幕,直射那将军后背。那将军听到风声,一个闪身已经藏在马肚子底下,堪堪躲过那一箭。
城上城下都喝了一声采,那将军微露得色,一离开弓箭射程便自掉转坐骑,对着墙上众人哈哈大笑。
城上又一声弓弦绷响,将军只听身旁军士低低惊呼,便见一支长箭在眼前越变越粗。黑甲将军心道好箭法,手中马刀暴起,已将长箭斩落在地。正要开口大笑,一只箭从他口中射入,箭簇从颈后探出头来,淌下一串黑血。
“连珠箭!”军中一人惊呼。那将军身形晃了几晃,扑通一声栽下马来。
静了一瞬,城上守军突然发出惊天价喝彩声,以为此时乱军将领一死,便会立时溃不成军,这一场血战便可免了。众人欢呼雀跃,却未曾注意射箭那人却站在城上默默不语,脸色越来越凝重。
莫三娘上前拍了拍那人肩膀,低声问道:“老张,怎么了?”
老张转过脸来,胡乱行了礼,摇了摇头道:“那人不是程郁,只怕只是个普通的兵士。”
“什么?”莫三娘大惊,老张的箭法她是知道的,二百米开外能穿透厚重的淬火钢铠,此时对付对方一个普通兵士竟然需要连射三箭,那眼前敌人的可怕程度只怕已经远远超出她的想象了。
她看着眼前乌压压一片钢铁,心中慢慢的腾起一股无力。她拍了拍老张肩膀,努力笑了笑:“没事!下次射死他便是!”
-
重重刀剑之后,中军大帐内饮酒下棋的程郁听到传令兵送来的消息,哑然笑道:“本来想要夺人气势,没想到竟被人立了个下马威!连珠箭,这后街的老鼠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程将军阵前被射杀,却也并不怕军心动荡,想来是成竹在胸吧。”对面一人在棋埕上落下一子,笑着说道。
程郁笑道:“若是以为我程郁这么随便就会死在阵前,怎么配当我狐将的士兵?”
“有理!”对面那人哈哈大笑,抛下棋子站起身来。“尹天,我看程将军胸怀韬略,是难得的绝世将才,怎么你却说得他一文不值?”
吕尹天听出话语中的怒气,慌忙躬身道:“尊使所言甚是。属下只是担心程将军办事不力……这攻城拔寨自然是程将军厉害,但我们要的人却……”
“蠢材!”那人身穿一件蓝色长袍,衣袖挥动间如带过一片波光。“我们想要的人,此刻便在身前!”
那人转过身来,冲着帐外茫茫的雨水喝道:“小小隐身阵法,也敢拿出来献丑!两位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