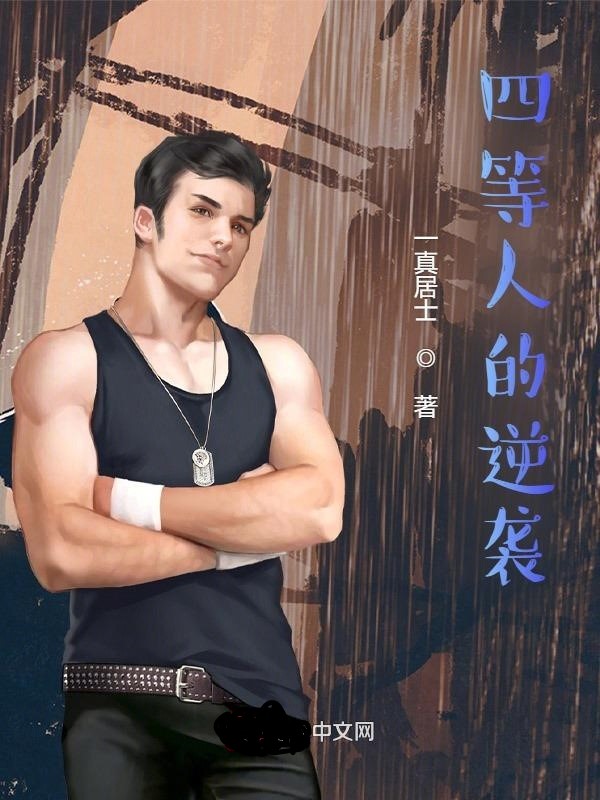淅淅沥沥的雨在入夜时分终于住了,空气中漫透了南国水润的气息。间或有雨滴从屋檐上滑落,在窗外檐下的青石上打出叮当的脆响。乌云还未散尽,天色暗的如同被蒙上幕布。一盏油灯发出虚弱无力的光芒,晃动着将屋内三人颤抖的影子打在墙上。
陈忠从窗外的黑夜中收回目光,看着屋里不言不语的两个少年,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孩子,你们明天还是要出发去往濮阳城?”
行歌的面孔在油灯的照射下显得有些阴郁,他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轻轻抚摸了手中长剑光滑的剑身:“要去!”
老人点了点头,走过用一根纤细的铁棍挑了挑灯芯,快要沉睡的油灯睁开眼睛,变得明亮起来。
“世道正乱,到处都是军队,别人躲还躲不及,你们两个孩子却偏偏还要往上凑……真是造孽……”
行歌从剑身上收回目光,抬头看这苍老懦弱的老人。他不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死多少人,只是不管最后哪一方胜了,天下间会多出无数的陈忠来——他们年老虚弱,孤家寡人,仰仗着养老的儿子被强行带走死在刀剑如林的战场上。
“老人家,你日后怎么过下去?”
陈忠对着油灯,无声的笑了笑:“嗨,我大半截身子都埋进土里了,没几年日子过了……怎么过不都是活么?人老了,也没什么盼头了。”
行歌埋下头去,又去用掌心摩擦手中的剑。屋子里重又变得静悄悄的,只有那盏不甘寂寞的油灯间或爆出一两个灯花。
过了许久,陈忠转过头,脸上爬满了年老的疲惫。
“我的父亲是个读书人,寒窗十载却没有得半点功名,于是意气消沉喜欢喝酒。我年幼的时候喜欢在他喝完酒时拔他杂乱的胡须,每每他被我吵得醒了过来,总是长吁短叹,大都是些壮志未酬的话语,我都不记得了。只有再往后他常说的一句话我听了无数遍,便印在脑子里,这辈子都忘不了了。”
老人顿了一顿,眼睛里挤进无尽的凄凉。
“他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吃人,另一种被人吃。那时候我听了这句话总觉得像是在半夜里听见了打雷声,浑身都惊得颤抖。直到慢慢的日子长了,不断地被那些凶狠的人欺凌了,才懂父亲话中的无奈,心中便也淡了厌了。我这一生可不是便是被人吃食么,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孙子……我眼见着我还有的那些东西都一点一点被啃食干净,到最后剩下我一个人。我常想,如果我不是总是这么懦弱,懂得反抗和争斗,是不是便会不同,是不是就能将那些被啃食的都拿回来。只是总是这么想着却从来也没有去做,等我想做了,我已经老了,老的连这么想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有时候一个人在梦中突然得惊醒,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才觉察到凄凉。人这一辈子,都是这么后悔着挣扎着,然后便要死了。”
他走上前,用大手抚摸两个怔怔听他说话的孩子的脑袋,脸上泛起慈爱的笑容。
“我心里实在不想让你们两个孩子去闯荡,你们那么像我的孙子。可是你们还小,有本事,有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做什么事情便去做,不要回头。人要是连少年的悍勇都没了,那就只剩下后悔了。”
老人说完转过身走进了里屋,行歌看见老人的背影在灯光下虚弱无力。
灯下慧生手中的佛珠发出一声清脆的碰撞,行歌转过脸,看见小和尚埋着头,脸上带着木然的呆滞。
油灯蓬的一声又爆出一个灯花,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
清晨的阳光从热闹的鸟鸣声中射入林间,树下的草叶上泛起流动的光彩。行歌转头看了看身后,老人单薄的身影已经被树木遮挡,看不见了。他用力的攥了攥拳头,使劲的踢断脚下勾绊的一根草。
“慧生,我真想留下来给这老施主当孙子。”
慧生在前面合起双手,声音比往日多了些沉重:“世间疾苦万千。”
行歌追上前去,与慧生并排走在一起:“恩……和尚,我一直在想这场战乱的起因,却怎么想不明白。战争来的太奇怪,就像是突然有人在柴堆里点了一把火,火势就无边的蔓延开来。前些时日听朔州城内的众人说乱军中有妖怪作法,我只当那是胡言乱语——人怎么可能与妖怪为伍?昨天又听见濮阳城中的怪事,这才想通这一场战乱怕是另有隐情,多半便是妖怪挑起的。所以我想,我们一路追上那乱军,除了那军中的妖物,不就能把这场战争了结了么?”
慧生听完沉默了半晌,然后静静的说了声:“诺。”
行歌脸上的笑脸顿时泛了起来,他欣喜的用手搂住慧生的肩膀,欢喜得说,“真是好哥们,以后我们两个就一道修行,待除了妖魔,我陪你去寻你的佛缘。”
慧生轻轻挣脱了行歌的搂抱,垂下眉目又颂了一声“阿弥陀佛”,便自诵经念咒。
行歌心中的石块落地,禁不住心中欢喜,在空旷的林中仰头长啸起来。
前些时日朔州城中他不慎走火入魔被真气灌入脑内,险些丧命,却不想在无意间得了把绝世的宝剑。这叫做缘尽的宝剑一入他的掌心,便有一股浩瀚的真气涌入体内,瞬间将攒动的真气尽皆杀伐的干干净净,最后缓缓回落,像一道山泉顺从的流进他腹中丹田。这一段经历说来简单,其实过程凶险并不下于之前走火入魔。若不是因为他曾在燕山山中得生机之水淬炼,体内经脉比之常人数十倍有余,早就在汹涌的剑气中筋脉尽断而亡。
这一场因祸得福,反使他真气修为更甚之前十倍有余。此刻纵声长啸,只见那声音宽广嘹亮直直冲上云霄,久久凝聚不散,连林间鲜嫩的柳叶也跟着震颤起来。
突听身后的树顶传来一个恼怒的声音:“一大早的谁在那鬼哭狼嚎!扰了小爷好一场春梦!”
两人回头,却见身后那颗参天的大树上青衫晃动,一人撩开了脸前的柳条自怒目而视。
行歌转过脸问慧生:“和尚,你摸摸我的脑袋看我是不是发烧了,我好像看到有个猴子穿衣裳了。”
那人一听更是大怒,扑通一声便从数丈高的树上跳了下来:“小畜生,骂谁猴子呢?”
行歌定睛一看,却是个背负长剑的少年。那少年生了一副发红的面孔,乱糟糟的短发根根冲天而起,一双大眼在酒糟鼻子闪烁着愤怒的光。
“呀,是个人呀,我还当遇见了灵性的猴子在树上做了个窝棚呢。罪过罪过,兄台见谅则个。”行歌弯下腰连连作揖,脸上却带着忍俊不禁的表情。
那少年一张发红的面孔眼见着便要烧起来,他急速的冲过来,一张愤怒的脸几乎紧贴着行歌。奈何这少年却比行歌低了半个头,站在行歌面前与行歌对视却得扬起脑袋,平白得少了半分气势。
“小贼,你认不认得小爷背后的家什?!信不信小爷用它在你身上戳出几个窟窿眼来!”
行歌探头看了看,见那少年背后的剑朴实无华,隐隐的透着凛冽的气息,确是一把好剑。当下咧了咧嘴:“这位小爷,大爷的背上也有一件物事。”说着伸手从背后解下“缘尽”宝剑,后退一步斜眼睨着这少年。
那少年吃了一惊,细细的打量了行歌手中的剑。见那剑平淡无奇,像把普通的青铜剑,于是放下心来,反手也拔出了鞘中长剑。
剑一出鞘,便发出一声高亢的鸣叫,如同龙吟。
行歌笑了笑,用手在剑剑上弹了一弹,道:“倒是一把好剑,却不知道使剑的有几分能耐。”他此时少年心性大起,便想借着这少年之手试试自己从书中新习得的“斩玉剑法”。
那少年脸色一变,手中长剑一震:“钟山门下苏铁心,领教阁下高招。”
行歌摆了个起手式,学着对手的模样:“无名小卒曲行歌!看招!”手下一招“柔肠断水”使出,剑尖摇晃,直奔对方胸口而去。
却见眼前原本站立不动的少年突然消失,待他剑招用老,面前早没了对手身影。他慌忙转身,屁股上早挨了重重一脚,往前一扑趴在地上,脸上蹭了一大块软泥。
“啧啧啧,原来是个软脚虾。”苏铁心一只大脚踩在行歌背上,心中充满疑惑。他分明看得出对手起手式乃是极其高明的剑招,打过来却不知道变通,姿势呆板没有灵性,像一个才学几日剑法的孩童。
他正自思索,却突然觉得脚下像是踩在了一处火山之上,巨大的脉动从行歌的身上传来,身形还未来得及回撤,早被那怪力掀倒在地。
行歌爬起身来,一脸欣喜的看着眼前诧异的苏铁心,顾不得擦掉脸上的泥水,大叫着:“再来再来。”说着又是一招“怒火蚀金”急攻而上。
苏铁心身心一变,又是一脚踢在行歌屁股上。这一次他留了力气,只是在对手的屁股上留下一个脚印。行歌转身再换一招,依旧是被苏铁心踢中屁股。如是再三,行歌新习的十几个剑招使尽,竟是招招落空,屁股上早留下了十数个黑色的脚印。
行歌心中又惊又喜,转身又要攻上,苏铁心急忙一个闪身上前按住了他的手腕:“你不是我的对手,不用再打了吧。”
行歌嘿嘿一笑,上前拉住苏铁心的手:“我打不过你,认输了。我向你赔礼道歉,但你得教我剑法。”
苏铁心昂起头:“你不说我也会教你,你剑法这么臭,被人看见了,丢我们游侠的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