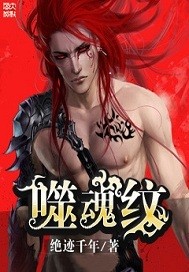几天以后,哲宗下了一圣旨:授徐诚忻为安抚经略使,赐天子剑,替天子巡视江南各路。但具体是去做什么的,并没有言明。
经略使一职只是个临时职务,通常是朝廷派往北方为调整军事布署而设置的。徐诚忻是个武官,给这个职务倒也合理,只是让他巡视江南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只知道他是替圣上南下,又手捧天子剑,掌握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还真让不少人心惊胆战的。
接到圣旨以后,徐诚忻也没急着出发,拜访了几位朝中大臣,虚心听取了一些建议。当然只要是为了去探探他们的口风,看看他们对他的这次出行有什么想法。最后他来到润王府,那位神龙见尾不见首的赵颜总算亲自接待了他。
这位王爷身材伟岸,面如冠玉,五官轮廓分明而详和,颌下三捋美鬓,赵家的子孙果然都生得一付好皮囊。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有板有眼,好象所有时间都控制他手里一般,完全是一付养尊处优的贵族气派。只有那双眼睛深邃幽窈,让人捉摸不透。
润王一开口就说自己只是一位闲赋在家的王爷,而你徐大人身为朝廷命官,又有要务在身,实在不宜来访,免不得相互客气一番。说起此行的目的,徐诚忻只说是为圣上巡视民风,顺道再去看看淮南、江南东路的灾情。
润王点到即止也没有多问,只是说你徐大人年少有为,如今又是圣眷正隆,正是为朝廷建功立业之时。此去江南应万事应以天下百姓为重、洁身自好,努力为圣上分忧才是等等。
徐诚忻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暗暗痛骂:你个老贼,做个天下第一的蛀虫还不知足,还总想着那把龙椅。就算想当皇帝也就算了,还TM的去跟辽人搅在一起,哥最看不惯就是这种吃里扒外的汉奸,早晚做了你。
送走了徐诚忻,赵谏从后堂走出来,皱着眉头问道:“父王,姓徐的怎么会想起来跟您来辞行?上次孩儿欲收他为门人却被断然拒绝,难道现在他又后悔了?”
润王摇了摇头,说:“此人与赵煦向来亲近,现在又成了国舅,他攀上了圣上这层高枝岂会再将我们瞧在眼里?”
“既然如此......”
“如果我猜得没错,他这次来访叫做:画蛇添足,也叫欲盖弥彰。”润王眼中精光一闪,道:“此人留着早晚是个祸害,让你的手下找地方处理了,手脚干净些。”
“这个容易,此人屡次坏我们好事,其实孩儿早就想这样做了。”赵谏又有些不解,问道:“只是父王为何说他是画蛇添足,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
“前些日子赵煦宣为父进宫了......”
“他怎么会想来找父王您呢?”赵谏心中一惊。
“是啊,平白无故的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润王道:“表面上说是与宗亲叙旧,可言谈之中多有警示之意。看来赵煦此人也不笨,已经察觉到什么了。”
“这定是高太后搞的鬼。”赵谏愤愤不平,“当初要不是她将父王硬召于宫中,那陈桥的几万禁军又能奈我何,大事早成了!”
润王也颇为遗憾地说:“本以为外有辽人搅局,内有心腹之人起事......怪只怪自己考虑不周。老太太阴险得很啊,临死之前必对赵煦有所交待。赵煦一亲政就撤换了大批官员,多年的经营损失大半啊,连辽人都不愿再与我们合作了。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求稳,拼死一搏或能险中求胜。”
“如今赵煦已经对我起了戒心,他岂有不知的道理?而且杭州的周通判就是栽在这个徐诚忻的手里,看来此人还是有些能耐的。只是......”他冷笑几声,“毕竟还年轻。他若不来,我还不能肯定,但他却主动来向我告知此行的目的,分明是想稳住我,好让我不对他起戒心。”
赵谏一想果然有理,不由对徐诚忻大为忌惮,忙告辞要去布署暗杀之事。
润王叫住他说:“此人不同于周通判,乃赵煦心腹之人,事发后必会让朝廷大动干戈。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切不可让自己人去办,即便如此也要保证追查不到咱们身上。”
赵谏答应一声急急下去了,润王继续沉思了一会儿,叹道:“可惜了,这样的人才竟不能为我所用,既如此只能将他除去了。”
第二天,处理好一切的“人才”徐诚忻向哲宗辞行,带着刘武和五十多名铁卫营士兵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铁卫营的事晢时交给陈友直等人,一万五千名士兵没用多久便已满员。毕竟铁卫营的地位不同,再加上易州的那一仗,早就让它名声在外了,所以招募起来非常顺利。
军器监在海聋王的主持下也已经正常运转,徐诚忻交待:所有火器加足马力,加紧生产,凭他们现在的这点人手,除去平时训练用度,再真的打起仗来还不知够不够用。
易州的项钟父子那里直接送过去三十万两白银,言明:这是所有的本钱,通关文书到范大人那里讨要,能赚多少看你本事,一年要是赚不到三五百万银子就别来见我了。
事情办完,银子化光,徐诚忻也就安心了,举着钦差大臣有仪仗威风凛凛地开出城门。
才走出没多远,忽从后面追来一骑,马上坐的竟是哲宗的护卫范斫。对于这位“闷葫芦”,徐诚忻还是挺尊重的,做保镖做到这么专业也是不多见的。
“范兄,圣上还有什么话要吩咐我吗?”
“徐大人,圣上只是命我与大人同行,一路听命于大人,以保护周全。”
“这个,我这儿已经有二百名兄弟了,用不着这么小心吧。”
“这是圣上手谕,请大人过目。”
徐诚忻拿来一看,果然如此。看来哲宗还是挺关心自己的,连自己最得力的保镖都舍得让出来,心里多少有些感动。
“既然如此,那就有劳范兄了。”
“皇命所在,大人不必客气。”范斫不苟言笑,说起话来干脆利落。事情既已交待清楚便不再多言,只策马侍于徐诚忻的马车旁,一付“我在工作,别勿打扰”的姿态。
徐诚忻深知他的脾气,倒也不在意,全当他是透明的。当下也不再客气,回到马车里躺下。有这么专业的保镖护驾,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就算蓝月玟的师傅那个老娘们来了,估计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车内早被晚布置得十分周到,厚厚的一层垫子,边上放着书籍、点心之类。虽说走起来摇摇晃晃地有点慢,却非常惬意自在,跟自驾游一般。
绍圣年间,虽说人口有大量增加也不过一亿,但与今天十多亿自是不能比。几天以后,官道之上就行人日见稀少。徐诚忻也不知走到什么位置了,反正有人带路,这第一站便是江南东路的州府所在地--江宁。
走着走着,队伍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到驿站了吗?”徐诚忻探出脑袋问道。
刘武回禀道:“前面有许多路障挡着,队伍过不去,兄弟们正想办法呢。”
徐诚忻跳下马车一看,这地形还真要命。一边是深沟,一边陡坡,路中间长长一段堆着乱七八糟的树杆、巨石。绕是绕不过了,但这些树又粗又重又多,一时半会儿是搬不完的。路上还堵着十多个行人,这些行人也是因为行李太多爬不过去,正头疼呢。
看看天色,估计再过一个多时辰就差不多天黑了,到下一个驿站至少还得走上二个时辰。
“大人,”范斫建议道:“属下觉得应该绕过去。这路障明显是有人故意为之,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总是对我们不利。”
“能绕过去吗?”
刘武答道:“从左边的斜坡上勉强可以过去,不过这马车是过不去了。”
“能过去也不绕,不然人家还以为我们怕了。再说路上还有这么多百姓,我们总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吧。”徐诚忻摸摸下巴,又看了看手下的五十多兄弟,说:“我倒要看看有哪个不开眼的车匪路霸敢对我们不利。”
范斫听了当即不说话了,意见是提过了,听不听是你的事,他这保镖的本份是做得很到位。
“去个些兄弟清除路障,其余人小心警戒,天黑之前必须把道路弄干净。”
一声令下,各自开始忙碌起来。徐诚忻又看了看四周的地形,路的左边是又陡又高的大斜坡,幸好是冬季,草木枯黄倒也躲不了人。右边则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沟崖,跳下去不摔死也得坏几个零件。这种地方确实是谋财害命的好场所,要是在战争期间他还真不敢停下来。
那些百姓见官兵们开始清理道路,顿时安下心来,有勤快的也过来一起帮忙,余下的都聚在一起聊天。
徐诚忻见其中有几个象是行脚商人,便将他们叫过来打听。
“官爷,小人是做药材生意的。这条道每个月至少要跑上二、三趟,从来没听说过有强人出没。今天这种事还是第一次碰到,估摸着是哪家大商号在此采购木材吧。”
“这里常有人来砍树吗?”
“也不常有,毕竟离城里有些远了。也不知是哪家商号干出这等缺德事,幸亏有官爷在,不然......”
他的话还没说完,猛听到斜坡上一声呼啸,紧接着一大帮蒙面汉子手执白晃晃的钢刀冲到路面。当头一个大汉扛着把金背大砍刀,大摇大摆地走到前面叫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牙缝嘣半个不字,定当一刀一个,管砍不管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