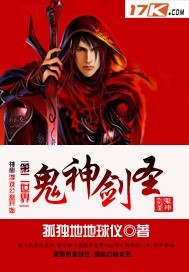烈日高照,狂风喧嚣,古城山坡上一个青年窝在树边阴影下熟睡着。
白色衬衫和西装裤组成了再平凡不过的上班族,白晰的皮肤倒有宅男那股范儿,与他面前那藤蔓覆盖的磐石城墙十分违和。
“丝丝~”随着好似瓦斯泄露的声音,城北亮起一束白光,伴随着沉闷的轰隆声。
那白光很快就消失,随之而来的就是黑洞洞的浓烟、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地震,不过这一灾祸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随着地震熟睡中的青年也被惊醒,揉了揉眼角、打了个豁害,慢悠悠地睁眼看起来惬意不已。
一缕黑烟袭来青年遇臭味难忍就冲下山坡来到正北方的护城河。
撕下衣袖蹲在河边浸湿后蒙住面部,看着河流如此浑浊便顺势看了过去,沿着污迹一直看过去有一件血迹斑斑的粗制白布衫。
他摸了摸眼睛,不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事实。
他瞪大双眼,眼里充满恐惧,青年不想看见的一幕正哀鸿遍野地演绎在他眼前——
数十具冰冷而僵硬的平民尸体漂浮在水面,可谓尸枕狼藉,他们嘴唇已是冬候寒草的沧萎。
他看完后一股来自深处咽喉内如大风若卷似的从喉咙迸发出来,紧接着侧身呕吐起来。
待缓过神来他猛地将湿衣袖丢入水中,神流气鬯地跑进城门一旁,眼神狰狞地望着地上。
回想方才景象令他感到害怕,同时越想又愈发觉得奇怪:那古朴装束以及那发型是什么鬼啊?还有!最关键的是——我怎么在这种鬼地方啊?
他虽然想回去再确认下情况,但那只是“想”,他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场面了,便下意识的畏惧了起来。
他摸着用三氧化二铁上色的城门,感受着时代的沧桑感,“好真实啊。”
城北黑烟徐来,城墙另一侧万籁俱寂。
青年越伫越发焦躁,不时扒耳,不时搔腮,不时锤墙跺脚,脸色焦眉苦涩,眼白上还泛有血红丝,不一会儿便晕摊在地上。
正当青年脸色转好准备起身时,有俩人气势汹汹地朝他走来,那俩人内衬红布衫,外备铁罩甲,手提倭寇铁炮,腰间别着一把腰刀,看起来很是飒爽。
青年看着俩人顿时蒙圈,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
双眼迥然,抬头望着城门又了想什么,随后突然眼睛瞪大,拳砸掌心,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介尼玛不是在拍电视嘛?还尼玛是老子最喜欢的明朝服装。”
士兵听到他说的话便皱起眉头,“此人在说何物?何为喷雷?为何要克死他?”
士兵指枪对着他的手臂示意让他起身,须臾之间上下打量。“倒是和我们颇有一丝同貌,言语实属有些大同。”
青年抬头看了看门匾,又看了看四周,疑惑道:“真是奇怪,啥电视不在北京城而是借用北京城拍摄?”他皱起眉头看向两人,上下大量,“这装备可真够用心,太帅了!”
士兵手提倭枪使尾撑着地,弯身驼背站在护城河交汇处。
两士兵打对眼喃喃细语,眯着眼打量青年,那青年意识事情不对正要转身便被呵住,“说!可是鞑子派来的作细?身着打扮如此怪异,吾等平生素未见过。”
话音未落就将青年双手双脚捆绑于麻绳中,青年可谓是手无缚鸡之力,只好束手让其五花大绑。
“哎哎,不能因为我突然闯入你们的拍摄场地就把我抓起来吧。”青年挣扎无力。
看着士兵那凶恶的眼神,又一霎转脸慈和畏缩道:“大兄弟!别来真的啊,至少绑松啊。”
士兵见他如此啰嗦又从草堆里拔了一捆草芥,塞进青年口中,空气瞬时寂静下来...
士兵拖拽着青年向城中走去,士兵鳞甲片间撞击声清脆,这引得城墙上一些守兵下来探查。
头戴草帽状军帽,顶有血色红樱,蓝色布甲敷着红衣褴褛,陈旧的下裳搭配着起卷卷戎毛的布履,手提一柄长枪,腰中揣着一把三尺(近乎一米)腰刀,守兵的装备和先前的士兵装备可谓是天壤之别。
内城士兵的装备乍一看还挺整齐,再仔细打探时居然发现众兵的装备竟无一处同出。
在他印象中明军的军服是像之前俩士兵那样的艳丽夺目,而不是如此这般朴素褴褛。
那俩士兵可不敢懈怠关卡之事宜,就让俩城兵前去盯卡,走时还不忘身旁的同僚闲聊,“这鞑子力气好生单薄,我那未过门的娘子力气都比他大。”
“确实,不过这细作长得如此清秀,放到咱京城倒像一个白面秀才,居然来干如此晦事。”
青年听到他们的对话使得自己苦笑不得,心想:这剧组演员也太尽职了,连混入的路人都要加戏,勉强配合配合吧,不过…不要真得绑死的啊!倒是把我口里的粗草拿出来啊!哎呀,呲肉了!
从城门走到街上经过府衙到提刑按察使司,街道上近乎隔一甲(十户)就有一尸体躺在地上等待送葬。
许多树林都变成了乱葬岗,左道旁人即恐入。
满街上不像是电视剧里演绎的那样热闹,昔日繁华的商业街陨落变为流氓、饥民、以及不法者的集聚地,除此之外不常的寂静令人感到不适。
他四周打量摄影机的位置,可次次无果,被两人强行控制了,他脸上有些焦虑担忧。
随之走进一个监狱,拉开铁门只见一人正坐长方凳上,正用笔墨书写奏章。
青年全身散发恶臭味、从发际线处流下两支血,按察还未放下笔墨就用袍袖捂起了口鼻,墨汁在须臾之间落在了袖子上,这下大人神情都变了。
刚开门起先的两名士兵把青年扔在一旁,单膝跪在地上作辑,“按察大人,吾等巡司时遇一怪人,此人言语甚怪,但与我们样貌实在相像,吾众深感万分怪异,我粗断是鞑子细作,亦或者是汉奸包衣,您看如何?”
按察使放下笔墨、收拾好书卷,拂了拂袍袖,看着自己被墨沾染一块乌黑的区块,走近青年身边,用嫌弃的眼神儿打量起来。
使官厉声呵道:“解绑,让他说两句话。”按察使一下令,士兵就争先恐后地把绳子解开,他们可不敢懈怠让典狱有一丝不满。
“痛死我了。”被解绑后的青年把口中残留的粗草掏出,吐出血和口水混合物带着拉丝掉落在了地上,傲娇地看向两名士兵,随即站了起来。
士兵看到青年站起来瞳孔缩小,随即用槊尾敲向青年瘦小的膝髌骨。
力大可谓如牦牛,青年受如此疼痛,还未来得及收敛表情就骤然跪下了。
待青年跪下后按察大喝道:“你姓甚名谁,速速报上来,是何许人也。”
“我…我姓朱,名重明,自懂事时从山东临沂随母亲迁往津门。”
还未等按察发话地面又开始剧烈晃动,闸外传来剧烈轰鸣声,士兵和使官猛然蹲在地上,朱重明趁乱撒开腿就跑出了司狱,使官和两名士兵都没反应过来。
来到街上朱重明不敢有一丝懈怠,仓皇而逃,踩到尸体也不敢往地上多看两眼,朝城门方向跑去,他已经意识到这并不是演绎,而是铁铮铮的现实。
他问了很多接踵而过的人今夕是何年?大多数人都把他当为痴汉无视而过,费劲口舌才问到具体的一个时间。
“今年是天启六年,初夏十五,怎么了你,活太累了连日子都不记得了啊?”
天启六年是一六二六年,初夏十五是农历四月十九,也就是...五月三十,没想到还真穿越回明朝了而且还是王朝末期。
城门交接的殡车,送葬人不断,明末大鼠疫始于崇祯六年,也就是一六三三年。
还有六年就要遭受更痛苦的人间地狱,朱重明想想就毛骨悚然,自己也太倒霉了吧!还有,我是咋穿越的才是关键啊!算了算了,既然穿越过来了就好好享受这时代的“风雅”吧。
许多人观望着官府动态,期望能分着一些粮食,多年亦是如此,虽然有些日子能得到赈济粮,换年号时亦尤是,但着不足以支撑生计,人们开始被世态逼用黑暗的谋生手段。
他不明白民众为何不去种地维生;为何不去作佣谋生,这些疑惑只能反映他自身的懵懂无知、不了解这一世态炎凉,这些疑惑也会在未来逐渐变为自身所能获知的真相……
-------------------------------------
城北的黑烟聚成一团在远处的高空上形成“蘑菇云”,空气中弥漫着尸体的恶臭味,开始尖锐爆鸣声变得沉闷,地面开始晃动,足有4分钟之久。
“踢嗒~踢答”,城门口一个骑着俊马的士兵策马进入街道,边喊道:“京城爆炸了,速去救人~京城爆炸了,速去救人。”
城内霎时沸腾起来,门口守卫都纷纷抛下重甲,担上装满沙子的木桶、手握火钩前去城北。
伴着有些不知目的何在的城民,扛起锄犁,甚有拎上片刀前去救火,肩提担子前往北城。
趁着混乱,朱重明见势快步走出城门,走到护城河回首望了望城墙上的那块崭新的石匾,上面刻着三大字——“永定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