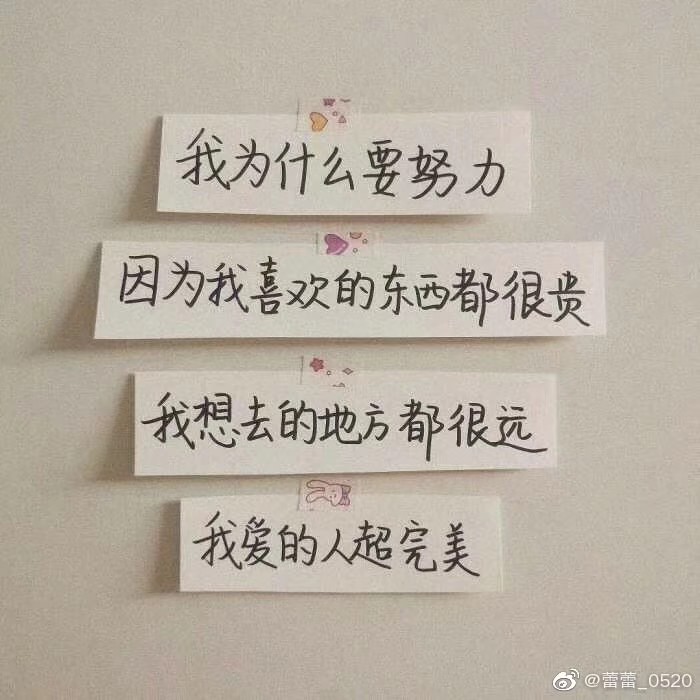小镇上,李继一天天的长大,慕容蔻逐渐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异于常人之处,李继也并未对相依为命的母亲隐瞒,将自己记忆中的另一个世界慢慢告诉了慕容蔻。
出身大家闺秀的慕容蔻最初大感惊异,慢慢的,这份惊异变成了自豪和骄傲,她坚信着爱子绝非凡人,日后必有不平凡的一生。
等到李继十岁时,逃难时带出来的金银细软已经逐渐花光,慕容蔻便靠帮镇民们缝补衣裳勉强度日。
无数个艰难缝洗的夜晚,冰冷刺骨的污水侵蚀了她的冰肌玉肤,一针一线消减了她的绝色容颜......
但她的心是热的,如天下所有慈母一般,看着爱子一天天长大成人,所有的苦楚都不值一提。
而李继,自从可以拿的动“破虏”的那天,便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学武之路。
父亲除了留下一把“破虏”外,还有一付铁臂铜胎的弓箭和一本家传武学秘籍。
他很快发现这个世界之所以可以修习奇妙的武功,根本原因在于这个世界的天地间充斥着一种可以被人的意念感知并利用的气息,李家家传的秘籍中把这种气息称为“元炁”。
即使在这个世界,天地间的这种“元炁”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感知和使用的,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做到,而他便是这些幸运儿其中之一。
李家家传武学分上下两篇,上篇“破阵诀”在他手中,下篇“澄心诀”被祖父带在身边,下落不知。
破阵诀要旨在于调动天地元炁,遍布周身经脉,锤炼出一付铜筋铁骨。
杀破万军,一骑凿阵!
是为破阵诀!
从六岁起,李继便刻苦练习破阵诀心法和秘籍中所载的刀法箭术。
直到他十岁那年......
边陲小镇的居民不多,却是形形色色,有放牧为生的牧民、春种秋收的农民、教书的先生、有钱的乡绅、经商的小贩、沿街讨食的乞丐......
若论最惹不起的,还是镇东开武馆的金鞭刘。
金鞭刘,点苍派外门弟子,在小镇定居二十余年,一把金鞭在这边陲之地也算小有威名。
镇上十个青年中至少有六个人是金鞭刘的徒弟,由于地处边陲,天高皇帝远,金鞭刘俨然是地方一霸。
十岁前,仗着从京城带出来的一些细软,加上母亲慕容蔻精打细算,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母亲也很少出门,并未惹来什么是非。
随着家财逐渐散尽,母亲开始抛头露面,浆洗缝补为生,出现在小镇上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慕容蔻原本就天姿国色,那时虽然年过三十,依然风韵犹存。
金鞭刘开始注意到了这个外来的美妇人,几次调戏无果后,他恼羞成怒,某一日,濛濛细雨中,他带着一群浪荡子闯进了母子居住的宅院。
那一日,凄风苦雨......
当这些恶霸试图将慕容蔻抢回金鞭刘的武馆时,他们丝毫没有注意院中那个目中喷火,长发披肩的孩子。
孩子实在太小,纵然满怀愤怒,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又怎能阻挡他们的兽行。
直到他们看到李继向金鞭刘劈出了一刀。
刀从金鞭刘左颈劈入,右颈离开。
鲜血激飞,雾一般的血珠四溅,在院中开出片片血花。
场中没有人能形容这一刀的速度。
头颅飞起,金鞭刘眼睛仍然圆睁,目中还充满着怀疑和惊恐,他至死都不信这样一个孩子能杀死自己。
血雾迷蒙了恶奴们的双眼,震慑了他们的魂魄。
随着恶奴们如丧家犬般哀嚎着逃出小院,金鞭刘的死讯迅速传遍小镇的每个角落。
杀人后的李继,抱着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呕吐。
两世以来,他第一次杀人......
小镇无法再住下去,李继带着惊魂未定的母亲,匆忙逃入了深山。
从此,母子逐渐在山中定居下来。
可是母亲身体逐渐虚弱,渐渐的开始咳血。
李继明白,这是肺结核,在这个没有抗生素的世界,还是无药可治的绝症。
六年来,李继在山中挖掘各种草药,人参,调养母亲的身体,却收效甚微。
直到昨夜,离别终于到来......
......
泪水早已流干,李继此刻只是麻木着翻动着火上的野兔,回忆着十六年来的点点滴滴。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扬起滚滚尘土,一匹通体纯黑的健马飞奔而来,毛色油光发亮,只有马头上一撮鬃毛白如霜雪,马眸赤红如火,神骏非凡。
马上骑士身材魁伟,满面虬髯,看不出多大年纪,四方的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身穿土黄色缇直具衣,已经微微破烂,看起来与胯下的骏马极不相称。
黑马奔行极快,片刻间已经来到李继的篝火之旁,马上大汉两道冷电似的目光霍地在李继脸上转了转,一提手中缰绳,黑马打个响鼻,鼻孔里喷着白气,停在原地。
大汉跳下马来,冲李继豪迈一笑,说道:“行路之人,腹中饥饿,想用上好的美酒和兄弟换些肉吃,可使得吗?”
李继听到酒字,心中一动。不禁想起上一世,驻防边疆的无数个夜晚,他和战友们痛饮高歌,划拳行令的日子。
那时,酒仿佛就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后来部队开始禁止喝酒,可每到假日,还是会叫上一批战友,先把检讨书写好,再一起喝个酩酊大醉。
这一世,自幼和母亲相依为命,十岁又逃到山里生活,还真没喝过一次酒,也逐渐把酒这种东西渐渐淡忘,此刻听这虬髯大汉提起,心中不禁有些感慨!
李继将烤的肉香四溢的野兔捡出一只,递了过去,淡淡说道:“一只野兔而已,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正好两只,你我一人一只。
大汉也不客气,伸手接过,转身从健马的鞍袋里取出两个革囊,似乎怕李继疑心,将其中一个拔出塞子,喝了一口,然后抛给李继。
“上好的瓮头春,就着这兔肉正好!”
说完也不管李继,坐在火旁,撕着兔肉,大口喝酒。
李继拿着革囊,一股酒香直扑鼻端,他此刻满心悲伤,这酒倒是来的正是时候。他喝了一口,香气轻柔,甘甜柔绵,果然是极好的米酒,比起前世的好酒,除了略淡,其余毫不逊色。
十六年未尝酒味,李继精神一振,不觉仰头又是一大口,脱口而出:
“好酒!”
那大汉见他一口便喝了约莫半袋酒,似乎颇为意外,哈哈一笑:“好酒量!”随后拿起自己的革囊,冲李继遥遥一举,仰头一饮而尽。
李继六年来未见生人,此刻看这大汉生的一脸英雄气概,行事又透着豪迈洒脱,不禁心生好感,也举起革囊,仰头喝干。
大汉看李继喝的爽快,不由眼中放光,站起身来,从鞍袋中又取出七八个酒囊,扔在地上,原本涨的鼓鼓的鞍袋瞬时瘪塌,原来里面装的全是美酒。
大汉指着地上的酒囊笑道:“兄弟酒量似乎不错,咱两个再喝几袋如何?”
李继见这大汉说得真诚,知道对方必是性情中人,淡淡一笑,说道:“可惜我却没有那么多兔肉可换。”
大汉洒然一笑:“若能再饮,但取无妨!”
李继便再不客气,又拿起一个酒囊,大口喝了起来。
大汉也不再多言,自己也开始大口喝酒。
两人各怀心事,互相也不交谈,只是喝酒时举囊示意,不多时,两只野兔便已吃完,七八个革囊中的美酒也全部被喝的涓滴不剩。
望着地上空空的革囊,两人抬头对视一眼,似乎都是余兴未尽......
大汉叹息道: “可惜再没有酒了!”
语气中颇有遗憾之意。
随即脸色一沉,纵身而起,双目凝视李继,缓缓说道:“想不到肃杀组中也不都是无趣的奴才,樊某倒是不曾听说还有你这等人物,如今酒足饭饱,你我酒量虽未分出胜负,便在功夫上见个输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