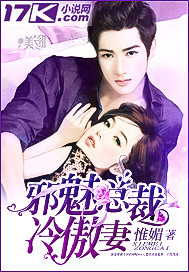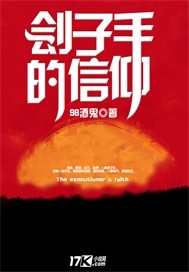“但是还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克洛伊思索了一下,然后问,“你在英国伦敦去世的世间是1920年,为什么到了30年代才再次转世出生在波兰克拉科夫?中间的10年你去了哪儿?”
米塞洛斯看着结冰的湖面,似乎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才用低沉的声音缓缓地说:“那段时间,我也经历了一次轮回,出生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Kharkov)。”
听到“乌克兰”这个地方,克洛伊心中顿时一惊。她仿佛已经猜到了什么,因为那场大灾难是很多东欧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乌克兰,”米塞洛斯缓缓地说,“这个原本被称为‘欧洲粮仓’的国家,在30年代初却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1932年春天,天气本来已经回暖,农民播种后又突然降温,不少农作物都冻死了。而且自从1931年开始,乌克兰就遭遇了大旱,粮食产量骤减。到了1932年夏季又频降大雨,田地里的农作物刚挨过旱灾,又被突如其来的洪灾淹死。大雨过后,农作物又开始生病,麦锈病导致一半以上的小麦减产。不仅如此,幸存的庄稼还要遭受虫害和鼠灾的摧残,粮食的产量缩减了一大半,使得乌克兰人民的口粮空前紧张。而此时,苏联正在推行集体农庄政策,农民必须要将一部分粮食交给集体农庄,再由农庄交给国家。由于当时的苏联领导层推行政策时过于激进,使得很多农民的口粮也被充公。乌克兰人民彻底失去了粮食来源,在集体农庄征收后,一个人平均每月只剩下不到两公斤粮食。大饥.荒很快爆发了,人们被饿得骨瘦如柴,村庄里处处可见饥饿的人步履蹒跚,有的连站都站不起来,趴在地上直到饿死。火车站和各大城镇,乞讨的人群挤满了路面,他们伸着饿得颤抖的双手,向过往路人和火车上的乘客哀求施舍。有时会有人扔一些面包皮给他们,他们却连捡起食物的力气都没有了。火车站旁边和城镇的街道上堆满了饥民的尸体,波尔塔瓦(Poltawa,乌克兰东部城市)的街道一天就堆放了几百具尸体。当地官员下令挖坑专门埋葬饿死的人,然而无论坑挖得多深,总会很快就被填满。为了充饥,人们吃光了一切可惜吃的东西,甚至连死猫死狗的骨头都不肯放过。有的地方人们挖山里的野草吃,不少人因误食毒草中毒而死。很快野草也被吃光了,有些饥民就铤而走险,抢劫国家的粮库。到很多人还没将抢来的食物带回家,就饿死在半路上。活下来的后来大部分被判处死刑枪决。饥饿还带来了很多疾病,在我出生的哈尔科夫,脱水症就非常严重。而在其他地区还流行起了斑疹伤寒,甚至还传到了莫斯科。疾病又使得无数饥民死去,整个乌克兰,死亡成为最不新鲜的词汇。当时的苏联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赈灾措施,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家粮食都不富裕,因而救援也只是杯水车薪。那场持续了两年的大饥.荒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而我也在很小的时候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的家人都饿死街头,幼小的我自知无法逃过悲惨的命运,就在他们枪决抢粮的百姓的时候,默默走上刑场,站在了那些人的身前……”
听到这里,克洛伊早已热泪盈眶。一次次的轮回让眼前这个人饱受苦难,每次转世只在世间停留短短十几年,便很快悲惨死去,进入下一个痛苦轮回。
他们在湖边坐了一会儿,继而起身接着赶路。不知又走了多长时间,辽阔的荒原却似乎总也走不到尽头。
“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天亮了。”克洛伊说,“为什么一点晨光也看不到?”
“这里没有阳光,”米塞洛斯说,“我们已经身在冥界。”
“冥界?”克洛伊不由惊讶,“我们是怎么来的?”
“我可以自由进出冥界,不需要开启大门的钥匙,所以他们费尽心思找了几千年的残片,也就是石碑,其实对我而言毫无意义,我作为冥界之门守护者的身份才是唯一的钥匙,而并非其他所谓的神器。”
“但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对神器的争夺。”克洛伊说。
“就好像我们总说战争是帝王的娱乐,千百年来世界各地的王朝、政权频繁更替,在土地上展开无休止的争夺,就像这场战争,帝王将相牺牲无数生命只为夺取更多领土,到头来只是戕害了无数的黎民!在他们来回争夺、频繁易主的土地上,百姓还是像蚂蚁一样劳作、生存,繁衍生息。战争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就不是王朝政权,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黎民百姓。”
“所以他们对残片的争夺也是毫无意义的,”克洛伊说,“因为掌控冥界之门的钥匙根本就不是某件神器,而是你?”
米塞洛斯点点头,说:“用权力填补欲望的统治者与恶魔无异,有能力而无欲望的,才可谓神明。”
“如果像你所说,那人世间真是恶魔当道,神明无力。”
“时间就是神明,”米塞洛斯说,“时间会在冥冥之中安排好一切。”
“包括我们的命运?”克洛伊问,“这么说我已经死了?”
“对冥界成员而言,死亡只是新的开端。”米塞洛斯说,“走吧,前面就是冥河,过了冥河我们就可以重返阳界。”
冥河的岸边盛开着无边无际的彼岸花,为无尽的黑暗铺上一层绚丽的殷红。米塞洛斯带着克洛伊来到离河岸不远的地方,却并未急于过河。而是看着幽暗的河边,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你看那边,”过了片刻他指着阴暗角落里一块凸起的黑色岩石说,“看到岩石背面的那个人了吗?这是你第一次带着记忆渡过冥河,你应该去见见他。他已经等了你三千年。”
克洛伊惊讶地看着米塞洛斯,问:“他是谁?”
“他叫刚铎,是个古老的狼人。”米塞洛斯说,“三千年前我们还是一个人的时候,他曾是我们最忠实的同伴。但是在那次与冥神的对抗中,他奋不顾身冲向冥神,慷慨赴死,灵魂被送入冥界。而你为了守护冥界之门也牺牲了自己,被冥神打入地狱。他为了保护你走出冥界,甘愿前往地狱默默守护你、伴你同行。你们历经了千难万险,最终穿过冥界之门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身躯为你顶住沉重的巨门,被巨大的石门压得粉身碎骨。他是古老的神,灵魂不会死亡,但会在冥界支离破碎。他用了上千年的时间慢慢修复自己的灵魂,却在恢复完整后仍不愿离开。因为他想再见到你,哪怕只是看一眼。于是他留下来等在冥河岸边,只有你每次在阳界死去、灵魂渡过冥河前去转世的时候,他才能默默地躲在岩石后面看一眼。为了每隔几十年能见你一面,他已经在这里苦苦等待了三千年。”
克洛伊远远地看着岩石背面那个孤独徘徊的身影,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她所能做的,只是迈步过去,慢慢走到那块岩石的旁边。米塞洛斯留在原地看着他们,只见岩石背后的那个人先是迟疑了一下,似乎本能地想要躲避,克洛伊却径直走到岩石背后与他面对面。
他们站在冥河岸边,看着幽暗的河水与嫣红的花海,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说了多长时间,但当卡戎(冥界的渡神,负责将死者的亡魂渡到冥河的另一面)的渡船泊至冥河岸边的时候,那个人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最后看了一眼身边的女子,随即转身踏上渡船。克洛伊目送他离开的时候,米塞洛斯走到河岸站在她的身边。
“执念即地狱。”克洛伊看着渡船上远去的身影,“你不想知道我跟他说了什么吗?”
“你将他带出了地狱,”米塞洛斯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们也该离开了。”
“去哪儿?”克洛伊转过头来看着他问。
他们乘坐一架租来的双翼小飞机,从芬兰的赫尔辛基出发,前往挪威北部的哈默菲斯特(Hammerfest),然后加满油稍作休息,次日继续向海上飞去。
“这些年你一直像个普通人类一样生活吗?”克洛伊问,“难道也荒废了作为守门人的职责?”
“这个世界已经建立了新的秩序,”米塞洛斯说,“人类与世间万物自然会遵守世间生存的法则,不再需要我们过多干预。但我们仍然会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地守护这个世界。我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领地,并集结了和我们一样致力于守护这个世界的无名战士。我们现在就是要去那儿。”
“我有点不太习惯你现在的名字,”过了一会儿克洛伊又问,“你还有其他名字吗?”
“生活在世间的这些年我有过很多名字,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次作为人类降生时,古希腊的国王为我取的名字——撒卡里阿斯。”
“距今已经有三千年了,”克洛伊说,“那时候我还只是个灵魂,没有实体,更没有名字。”
“不,你在更早之前就拥有过名字。我们一起守护冥界之门的时候,你的名字是寒翎柏。”
“那只是一株草的名字!”克洛伊笑着说。
“你在人世间轮回的时候当然也有过很多名字,但我最喜欢的是一百多年前你出生在俄罗斯时用过的那个名字——斯维特兰娜,以后我可以称呼你斯维塔。”
“但我不想直呼你的名字,”克洛伊说,“我愿意称你为父亲,因为你的存在,才有我的出现。早在万年之前,你将自己化为巨石守护冥界之门,我依附在你的身上,守护着你也守护着冥界之门。”
“你都记得?”
“我们守护的地方黑暗而寒冷,只有我身上发出来的一点寒光,没有一丝温暖。”
“但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同样寒冷,而且在北极圈内。”
“冬至刚刚过去没几天,”克洛伊说,“现在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去北极?”
“你不想去看看我们的领地吗?”
“我好像已经有点后悔坐上这飞机了。”克洛伊无奈地笑着说。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说着他打开飞机的舱门,舱外的寒风卷着飞雪顿时扑面而来,吹得克洛伊几乎睁不开眼睛。但她看了一眼飞机下面的景色,目光却再也无法挪开。
视野中是一座被称为白岛的冰封之地,位于斯瓦尔巴群岛东北方向的冰冷海域,整座岛被洁白的冰雪包围,却有着众多类似于城堡的石塔,石塔之上不知什么物体发出像月光一样银白色的光芒,星星点点,映着天空中梦幻般的极光。数不清的塔尖在风雪中巍然耸立,上空有不畏严寒的海鸟展翅自由翱翔。
撒卡里阿斯转过头来看着她,奇异的光芒中他的微笑慈蔼而温和:“我们到了,公主,欢迎来到天使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