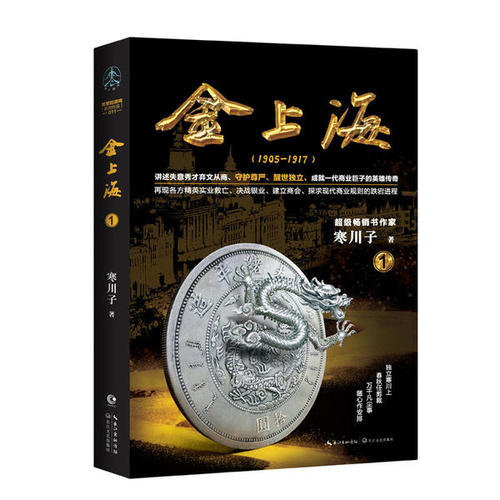光线变暗了,我将目光从信纸上抬起来看了看煤油灯,火苗极其微弱,只剩下豌豆大小。夜已经深了,疲惫突然袭来,我揉揉眼睛,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我很想知道故事的结果,信的主人是不是在那次大火中一同被烧死了?可是转念一想,应该不会,不然是谁写下了这封信,然后将它投进邮筒里的呢?巨大的谜团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很想一口气将所有的文字看完,可是眼皮已经不听使唤了。我将信纸收好了放回信封,将煤油灯熄灭,然后侧身躺在了床上。信中所讲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形成了清晰的画面。我闭上眼睛,回味着那些如梦似幻的尘封往事,一张张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不停地在我眼前闪现。那如烟的往事仿佛遥不可及的回忆,淌过岁月的河流,在我眼前翻涌着波澜。我伴着这些遥远的故事沉沉睡去,希望能够梦回往昔,亲身经历那段尘封已久的燃情岁月……
第二天早上我不出意料地起晚了。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天已大亮,我就知道上班肯定要迟到了。雷蒙德果然对我发了脾气。雷蒙德·多洛辛斯基是我们这儿的头儿,训手下就跟训儿子似的,劈头盖脸一点儿也不留情面,以至于人们都在私下里称呼他“肝火旺先生”。可奇怪的是他关心起手下来也跟关心自己的儿子似的,如果哪个年轻人有什么困难,比如家里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心事影响了工作,他就会把先你叫到办公室呵斥一番,然后叹一口气,继而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开始转变语气跟你推心置腹。
“你是不是在这儿干腻歪了?!”雷蒙德瞪着眼睛大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根本就不懂得时间就是生命!”
他总爱把事情说得很严重,好像我们稍有闪失,世界大战就会再次爆发!
“……如果都像你一样没有时间观念,如果重要的信件不能及时送到人们手里,就有可能会事关生死啊!还好现在仗已经打完了,要是在战争年代,你知道一封家书有多重要吗!”
雷蒙德说的振振有词慷慨激昂,甚至有些夸大其词、没事找事的苛刻嘴脸。奇怪的是,对于他的痛斥我似乎并不讨厌,反倒觉得有些同情他。这个不幸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年人,人生观和世界观肯定跟我们不一样。有人说,战争是帝王的娱乐、战争是死神的盛宴。所有的母亲都憎恨战争。战争来临时,真理是第一个牺牲品。战争使多数人流血,却养肥了少数人。战争也爱吃 精美的食品,他带走好人,留下坏人。就连阿道夫·希特勒都说过——战争只能带来伤害,到头法国仍是法国,德国仍是德国!战争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那种无时无刻的死亡气息。所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阴霾,所听到的所有一切都是恐惧。战争中的人们没有希望,城市没有生命。战争带走了我的父亲母亲,只留下一生都无法抹去的创伤。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雷蒙德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回过神来定睛一看,他正在用一种近似于愤怒的目光盯着我,似乎我是那个伤害了她女儿的负心汉,已经不可原谅。
“听到了,”我点点头回答说,“我以后再也不会迟到。”
他像看仇人似的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摆摆手叫我赶紧去干活儿。
今天的任务依旧不少。似乎是为了惩罚我上班迟到,那一大堆的信件足够我马不停蹄地忙一整天。而且这次又有那个乡下姑娘的信件,去往她家的路上要走过很多崎岖不平的小路,而且很远,所以每次有她的信的时候我总要比平时多跑很多路。可奇怪的是她的信还特别多,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有一封,而且雷打不动,好像她正处在热恋之中,每隔几天都会收到一封恋人给她写的情书。我这么推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每次给他送信的时候,总能看见她焦急地在门外等候,仿佛望眼欲穿。而且每次收到信的时候她总会欣喜若狂,高兴地接过信去然后快速跑回房子里拆看。我不止一次想问她写信的人是谁,她是不是很爱他?可是我没有资格这样问,只是每当为她送来快乐,看着她开心的样子,自己也会感觉到欣慰,所有的辛苦也就值得了。那女孩长得天生丽质,脸庞很清新亮丽,有着一种浑然天成的灵气,尤其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一张灵巧的嘴巴和开朗的性格,总是很容易将活泼与欢笑感染给别人。我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她和伊莎贝拉·安格拉德联系起来,却仿佛总有着天壤之别。伊莎贝拉冰清玉洁,却似乎总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而贝亚特丽斯(这是我在她信封上看到的名字)清新脱俗,单纯中又带着一种冰雪聪明,仿佛迎风而长的石楠花,充满生命的活力。
我无数次地幻想着,如果自己能与这样的一个女孩儿相爱,生命里一定会充满阳光。
可是我知道自己的命没有那么好,我自认天生命贱,经历过战争的摧残、家人的离散,走过岁月的创伤,已经没有能力去爱与被爱了。命运之神已经夺走了我的一切,只剩下孤独。
果然又是疲惫不堪的一天。完成所有送信任务的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了,我在夜色中骑着自行车,在寂静的城市中踽踽独行。无数次我在别人的窗外看到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其乐融融,自己却只能在寒风中眼巴巴地看着。回到出租屋里,点燃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借着暗淡的光芒,我只能在夜里独自咀嚼着这份孤单,并伴着它沉沉睡去。
但今天晚上我不想睡那么早,尽管又累又困,却还有一样东西帮我驱赶瞌睡虫——那只装载着尘封往事的信封。我稍作休息,便急不可待地将它从桌子上拿起来,用手掌轻轻抚摸了一下,就像在抚摸一段珍藏的记忆。然后,我将它打开,取出那叠厚厚的信纸。
它们可以让我不再孤单。
克里斯托弗决定永远离开克拉科夫。那晚,他在大火中窒息昏厥过去,凌晨时分有人发现了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只剩下一口气了。他决定回到格坦斯克,在那里走完自己的一生。他又回到了列车驾驶员的岗位,而且一做就是很多年。直到头发花白,仇恨在他的心里燃烧殆尽,他终于在孤独与悔恨中步入中年。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在了火车上,在那一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行程中,没有喜怒哀乐,没有未来,甚至没有生命。
克里斯托弗有两个搭档,一个副驾驶员,一个年轻的跟班。副驾驶员叫尤利·斯维凯威兹,是个整日忧国忧民的悲观主义者。他说波兰在十八世纪三遭瓜分,十九世纪外族统治,好不容易世界大战结束了,建立了共和国,又要跟俄国争领土。他说波兰就是个竞技场,周围那些豺狼虎豹但凡想要争夺地盘,都要在这块地盘而上打仗厮杀,简直就成了欧洲的公共战场。克里斯托弗对他的那套理论不置可否,只把自己当个倾听者,听他发表一下感慨就只当解闷。罗伯特·马休斯基可就不这么想了,他二十来岁,年轻力壮,自认是个新青年,认为波兰一定会再次崛起,在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重振第一共和国时期的雄风。
这两个人经常会因为思想观念与政治观点的不同展开唇枪舌战,不分场合地进行辩论,各执己见,尽管时常会挣得面红耳赤,但谁都不能说服对方,也永远不会改变对方的想法。
罗伯特·马休斯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胆小怕事。战争对他的影响并不大,他记事的时候大战就已经结束了,因此可以说没怎么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可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所以性格没有那么刚烈,而且有些胆小怕事,嘴皮子上说说还行,真遇到事儿就不行了。而且他还没有主见,从来不敢独自驾驶列车。没有胆识,所以还算是个小孩子。
事情发生的那天他们三个都在列车驾驶室里。
那是1929年10月22日,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下午,他们驾驶着列车从波兹南开往首都华沙。有很多从那个方向来的乘客都来自德国,有些则是荷兰甚至英国,途径波兰前往东欧(主要是俄罗斯)的。当天克里斯托弗坐在驾驶座上,尤利·斯维凯威兹占据着副驾驶座,负责协助他观察数据。罗伯特·马休斯基则坐在他们后面,负责协助他们处理一些杂务。
火车行驶到科宁附近的时候天近黄昏,外面的天色已经逐渐暗淡下来。
旅途劳顿,克里斯托弗和尤利·斯维凯威兹正在谈论世界大战,罗伯特·马休斯基却在谈论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of Austria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南欧洲的统治者。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以他建立奥匈帝国的功绩为世人熟知,1879年他与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结盟,1914年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把奥地利和德国拉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他真正想谈论的是茜茜公主(伊丽莎白·亚美莉·欧根妮,1837年12月25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女公爵与公主,后来成为奥地利皇后兼匈牙利王后),也就是他的妻子。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美丽女性,始终对匈牙利民族持同情心,1867年奥地利-匈牙利折衷方案达成后她与她的丈夫一起在布达佩斯被加冕为匈牙利女王。他说如果波兰一直处于奥匈帝国和德国的统治之下,说不定会比现在发展得更好,或许就不用跟俄国争领土了。
尤利·斯维凯威兹则坚决持反对意见。他说波兰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就算很艰难也绝不能卖国求荣!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列车穿过郊区行驶到了一片杳无人烟的荒原上,周围是一片辽阔的原始森林,在暮色的映衬下显得尤其阴暗荒凉。罗伯特·马休斯基建议打开车灯,克里斯托弗却认为还不到时候,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自然光要比人造光效果更好一些。可就在他信心百倍准备安全、准时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意外却突然降临了。意外发生的时候罗伯特·马休斯基还在喋喋不休,尤利·斯维凯威兹则端着一只杯子悠闲地喝水。
急速行驶的车头突然撞上了什么东西。
或者说,有什么东西猛地一下突然撞在了车头前面。
“砰”地一声,把驾驶室里的三个人都吓了一跳。克里斯托弗一个激灵赶紧刹车,尤利·斯维凯威兹差点儿把水洒在仪表盘上,罗伯特·马休斯基更是险些叫出来,立马睁大眼睛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天色太暗了,他们一时都没看清刚才撞上的到底是什么。
什么也看不到。
前方是一片朦胧的夜色。
三个人惊魂未定地看着前方,罗伯特·马休斯基似乎还声音发颤地问了句:“是人吗?”
他的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更加惊悚的事情就随即发生了。他们上方的车顶突然又是“砰”地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了上面,那感觉就像是一头猎鹰落在了兔子洞顶上。
罗伯特·马休斯基吓得差点儿没从椅子上直接出溜到地板上。几个人本能地一缩脖子,脑子里不由地就浮现出了史前巨兽袭击人类的情景。可是从那之后就再没声音了,好像刚才那一幕只不过是他们三人的集体幻觉。克里斯托弗小心翼翼地继续开车,尤利·斯维凯威兹使唤罗伯特·马休斯基去后面的车厢里看看有无异常,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安抚一下乘客。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小站,克里斯托弗打算在那里停车下去检查一下情况。很少会有列车在那个几近废弃的小站停靠。罗伯特·马休斯基转过身去还没有走出驾驶室,一种奇怪的声音就迫使他们所有人都停下了自己的动作。他们好像听到了秃鹰聚集的声音。一种瘆人的细微刮擦声和令人不安的脚步声从车顶频频传来,整个车头似乎已经被什么不为人知的野兽所包围。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
就在这时,可以斯托夫做出了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动作。他打开了车灯。
车灯亮起的那一瞬间,后面的罗伯特·马休斯基突然发出一声极其惊恐的叫声。
所有人的眼睛顿时都睁大了。克里斯托弗本能地使劲拉下刹车,整列火车带着摩擦出的火花在轨道上向前滑行,车厢里的所有乘客都会大惊失色,说不定还会有人因此受伤……
列车在科沃布热格站停靠的时候,车上的所有乘客几乎都走了出来。这是一个不怎么用的小站,平日很少有列车会在这里停靠,站台小而局促,一整车的乘客都下来显得有些拥挤。
乘务人员挨个询问客人有没有受伤的,人们大都受到了多多少少的惊吓,有的埋怨说东西摔坏了,不过还好没有什么人受伤。有几个人仔细检查了一下列车的各个部位,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天已经全黑了,附近没有旅馆,很多乘客都在埋怨着天气冷。没有办法,只好让乘客们都回到车上,打亮车灯继续前行。有的乘客心有余悸不敢上车,又怕被丢在这里没有着落,就只好妥协。于是没出一个小时,这列满载着不安乘客的火车小心翼翼地继续上路了。两个小时后列车抵达首都华沙,所有乘客都下了车,几乎没有注意到少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引发这次事故的核心。相关工作人员再次对整个列车进行了细心彻底地检查,结果仍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克里斯托弗和其他两个人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对此三缄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