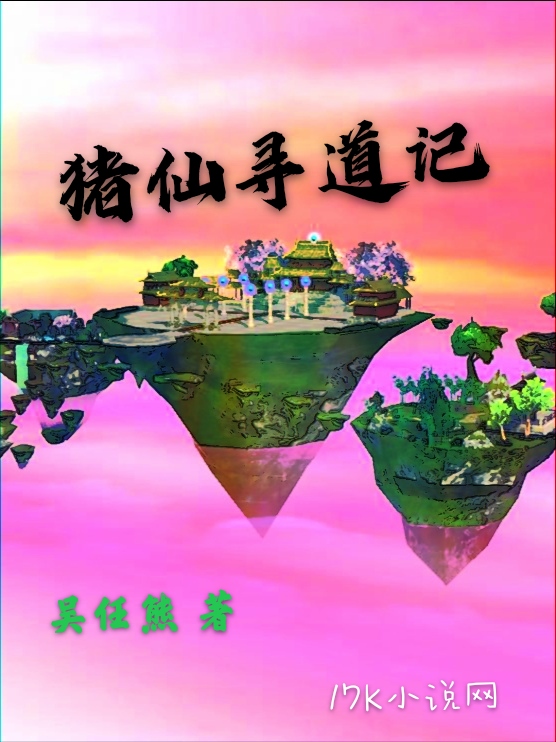是了,即便这世间处处黑暗处处鲜血,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分花拂柳而来,她肩上沾着花香,心灵和面庞一样纯洁清亮。她会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如月牙,而那种种阴暗种种失望,都会在这笑容底下,灰飞烟灭。
有些人心里有光,单纯美好,便成了别人的信仰。
那一瞬止桑猛地睁开眼睛,他觉得之前这一段时间的自暴自弃很是荒唐。因为害怕,因为失望,所以就得过且过了么?武侯问这世界是黑是白,这个问题是错的,任何一件事,都没有绝对的对错,世界,也没有绝对的黑白。
就像明乡,她的笑很暖很暖,她还相信着世界上的温暖美好。止桑勉强从床上站起来,扶着床边的拐杖。他要去武侯的营帐,他要告诉武侯,这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一片黑,可这黑里面,有一道光。而他,可以为保护这唯一的光亮,重新站起来。
如此,止桑被送回了鲁王都。而现在,他站在鲁庄公面前,听庄公面无表情地说:“孤要你杀了武侯。”
若是没了武侯,他能得到什么呢?他能继承博阳侯的爵位,他不用再担心身世被揭穿的那一日,武侯会举起他的长庚刀杀了自己。止桑眼神轻蔑,却是直视了庄公:“做君王的,心真脏啊!”
庄公脸色微变,隐有怒意,止桑笑了笑,又道:“心不脏的人,做不得君王。止桑愿为庄公鹰犬。”
离开石窟仍旧是分了前后,这一回庄公先行离去,过了两刻钟,长公主和止桑一起离开。长公主的步子很乱,显然是心绪不宁,待到了密道的入口处,长公主扶着石壁久久没有按下机关,她忽然回过身,担忧地拉着止桑的手:“桑儿……娘亲想了想,觉得这件事还是不应该交给你做。”
“是么?”止桑推开长公主:“母亲这话若是真心,就该当着庄公的面说。”
长公主:“……”
止桑背过身,在石壁上摸索一阵,触到机关。他看了看犹自出神的长公主:“母亲不必心有愧疚,这件事做成了,于我并不是件坏事。”
御花园,家宴。
王室其实没有正儿八经的家宴。想一想,你在吃饭喝酒的时候,一会儿跳出来一个女子说要来献才献艺,你还能安安心心填饱肚子?庄公的一双妃子正合力奏一曲《春江花朝》,明乡离了座位跑到止桑身边坐下:“哥哥的伤好些了么?”
止桑喝下杯中醇酒,谦谦笑道:“早已无碍。”
“那就好。”明乡从袖中拿出一个五彩的福袋,袋子鼓鼓的,不知装了些什么。她叫止桑:“哥哥。”
“恩?”止桑偏过头,恰好看见明乡月牙般的眼睛。
明乡站起身来,将福袋系在止桑脖子上:“我请师傅给哥哥算了命,他说哥哥此生命途多舛屡遭凶险。所以我为哥哥求了福袋,希望哥哥以后再不要受伤。”
“你傻啊,战场上哪有人能次次全身而退。不过……”止桑抚摸着颈间小小福袋:“得了圣女的祝福,以后上战场,会安心些呢。”
“哥哥是在笑话明乡?别总说明乡是圣女,圣女只是相对谷神而言的。师傅还说我命格不好,此生恐会遇上火难呢。”明乡低头笑:“师傅算命的时候总是一板一眼的,听着很吓人的。”
“明乡信命?”止桑环视在场的数十人,若有所思道:“明乡,事在人为,我们不应当信命。”
这一年偏冷,五月到了,双棠居的石榴却迟迟不肯开花。明乡和止桑一前一后离开鲁王都,那 一树花开殷殷艳艳,却无人细心观赏了。
止桑到达渠水天色昏昏,他去主帐向武侯报告。帐帘被掀开,武侯正坐着看书。止桑行了个军礼:“末将止桑前来报告。”
武侯抬起头来,微微笑着招呼止桑:“你过来。这里有两个字我看不清,你来读一读。”
止桑走过去,接过武侯递来的书,只见书上字迹拥挤,却是很不好辨认:“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
“好了。”武侯叫停止桑:“你说说,这段话,做何解呀。”
“这……”止桑犹豫,这本书他幼时读过,乃是先贤所著《鬼谷子》残篇。但如今这情形,武侯明摆着是有话要说,止桑索性卖个糊涂:“末将不知该如何做解。”
武侯将书翻了一页,自己悠悠念起来:“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
止桑的脸已然变得煞白,武侯素来不作闲事,自然不会莫名其妙挑出这么一段话让他赏读。止桑手动了动,几乎就要去拔腰间佩剑。
武侯却先一步抽出了长庚刀!“长庚刀下魂,皆是英豪。止桑,你也来尝一尝我这长庚刀的滋味!”武侯翻身一侧,从止桑身边越过,止桑连连后退,失声道:“父亲!”
快,太快了,长庚刀步步逼来,自己已是退无可退。止桑被逼到墙角,武侯却丝毫不手软,长庚刀横扫过来,止桑立马俯卧在地打了两个滚儿。武侯凛然道:“你在做什么?还不拔刀!”
“父亲要和止桑拼个你死我活?”止桑问。
武侯却不答,换了步法过来,止桑翻起身拔出佩剑,神色亦是肃穆。武侯笑:“总算舍得了?”
一时间刀光缠着剑光,兵器相互撞击的声音乒乓不绝。忽然间武侯弃了刀法,长庚刀横扫拨开止桑的剑,而后举刀自右上方斜劈下,止桑连忙拿剑去抵,却不想武侯气力惊人,一拨便将自己的剑拨开,剑脱了手,斜飞出去刺进木桩中。
止桑心惊,可手上没了称手的兵器,就好比猛虎没了爪牙。他双眼一闭垂首道:“我输了。”
武侯却并没有杀了他。他把长庚刀收进刀鞘,说道:“到底是年轻,刀剑都拿不稳。如此,我这长庚刀,你一时也配不上。不过你算是个人才,我十五岁的时候还不像你这么争气呢。止桑,平日想事都动动脑子,一时冲动,往往要用一辈子补偿。”
“恩?”止桑惊讶:“父亲的意思,止桑不明白。”
“过去的事情不用再想,你也不必明白。”武侯笑着拍他的肩:“这长庚刀我会传与你,只是好刀是要配英雄的,我等着你长成一个英雄。”
止桑默然,心里五味杂陈,看着意气风发的武侯坐回凳上,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又三月,止桑接到庄公暗桩的指示,要他在一月之内解决了武侯。止桑也基本明白庄公迫切想要夺了武侯姓名的原因。能独断者是为王,庄公因为手无实权,下达命令都嫌底气不足。
而庄公手无实权的根本原因,乃是武侯握紧了鲁国军权。
可止桑做不出选择。他做不出选择,所以只好听天由命。
止桑十五岁的冬天,渠水边上下了大雪。因着这场大雪,军中粮草耗得特别厉害。渠水外千里处有城池名为隼平,算是个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武侯派了五百人前去隼平征收粮草。
一切都很顺利,护粮队很快便收了足量的粮草,只是大雪封路,回程的速度降了不少。而这速度一慢,招来了虎视眈眈的楚军。
听得粮草在半路上被截的消息,止桑心下一沉,放下手上《鬼谷子》,托了头盔赶去大营。大营里诸将都在。武侯头也不抬:“你来了?”
止桑行了个军礼,走到自己平常坐的位置边上坐下,只见桌上摆着一副地图,图上一处地名用红色圈起来正是破葫山谷。武侯摁着地图,道:“楚军这是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止桑,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止桑蹙眉,仔细看着地图,片刻指着破葫山谷道:“不知护粮队情况如何?”
“几无活口。”
“如此,楚军便是知道我军粮草不足的情况了。军心动乱,始于绝粮,这批粮食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夺回来。楚军便是算准了这一点,才会不管不顾的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武侯,末将愿领兵夺回粮草。”止桑请令道。
武侯手中的狼毫笔落在地图上,点出两个小圈儿:“这件事不用你操心。陈生,你领兵五百,再去隼平走一趟。”
“末将领命。”陈生是个粗犷男儿,生得牛高马大,领了军令便出门去。
武侯目送陈生掀帘而去,这才对着诸将细言:“去岁楚军两万人马死在我们手上,按理不可能这么快就向我挑衅。除非他们做了万全之策。我们若去抢夺破葫山谷的粮草,只怕会是有去无回。”
“可隼平的粮草刚被我们征集了,现今又派人去,城中百姓不配合怎么办?”止桑问。
“不配合?”武侯挑眉,笑意冷冷很有些残暴的意思:“那便用不配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