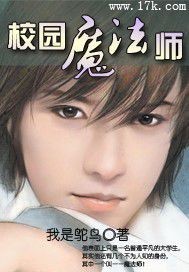止桑平日听的都是壮怀激烈的曲子,对祈谷会上的祝乐向来没有研究。更何况身边站着一个颇讨人嫌的男人,他便更没心思去揣摩这支曲子到底用的是宫商角羽徵中的哪一调。
蹙眉听了半晌,止桑喜庆听出些的意味。那厢明乡水袖微扬,腰肢一转似柳条般柔软,而桓常眼里映着明乡身影,嘴角带了些浅淡笑意。
止桑越发觉得这男人可疑。
待到祈谷会的流程走完,明乡随着一丫头离开。再回到祈谷亭,明乡却是换了一件儿粉嫩衣裳,头发飘散鬓边别一朵小小的粉色绢花。
鲁庄公招呼明乡到身边,笑吟吟对白玉高台下的子民道:“女儿本该十五及笄,而昭和为天定圣女,故而十六方行这及笄之礼。昭和乃是孤王心头爱女,却因圣女身份清修十载。因而孤王许诺,会让她在祈谷会上自觅郎君。众位——”环顾台下一干青年殷切的目光,鲁庄公嘴角一扬:“女儿心思难猜,诸位各展其长吧。”
十里桃林在瞬间热闹起来,明乡身边儿也立马出现了几位打扮英气的女侍卫。原本十里桃林中的青年人便多是冲着明乡而来,鲁庄公话音一落,无数人便高嚷着公主殿下,手里拿着各种奇奇怪怪的物什向着明乡拥去。
止桑抱起剑,眼底一丝轻蔑笑意。鲁庄公被人拥着走到止桑身边,见他神情淡漠,开口问道:“将军以为如何?”
止桑笑:“君上高才。”
这招亲本就是鲁庄公打的幌子。近年来鲁国国势日衰朝中无人,鲁庄公为 将别国的人才吸引过来,便使了这么个计策。明乡素来乖觉,顺顺从从便应了。可如今,止桑环视这混乱人群,不禁又是一笑:这些庸才,巴巴的贴上去,便以为能入了明乡的眼么?
身边飘过一个黑色人影,止桑脸上的笑霎时便凝固了。他目光如炬直落在桓常身上,桓常却一步踏入人群中。
这厮!当真是为了明乡而来。止桑先前的不屑荡然无存,惊慌情绪站了上风,他靠近了庄公一些,压着声音哀求:“君上如何要赌上明乡的一生?又如何……”
庄公却打断他的话:“你知道是为何。止桑,你要明白,你一日担着博阳侯的身份,便一日不能同明乡有牵扯。”
止桑心头一震,眸光暗下去。忽而他卸下身上佩剑奉给庄公:“请君上削去止桑博阳侯的爵位。”
“你手上的军权呢?”庄公眼中精光一闪。
止桑抿唇,一字一字说的艰难:“怀化大将军的身份,臣愿一并拱手相让。”
“很好。”庄公笑得意味深长,拍了拍止桑的肩:“孤王就当听了个笑话,以后万不可在说出这么没脑子的话。不然……你便辜负孤王的期望,也辜负明乡的信任了。”
还是,不会同意的 啊!止桑觉得眼睛有些酸,忙忙低了头。不该妄想的,怎么会奢求庄公的恩赐呢?庄公精打细算许多年,又怎会自己乱了自己的棋局?
清冽婉转的箫音陡然响起,调子是古曲《桃夭》。人群的各种嘈杂声音被箫音盖住,不几时,众人竟然安静了下来。桓常的步子很稳,自带生人勿近的冷冽气质。人群中让出一条道来,桓常一步步走到了明乡身边。
尾调一扬,江诺收回玉箫。明乡拨开身前的姑娘站出来,不着脂粉的脸蛋格外清丽动人。她抬眼看着江诺,目光旋即落在他手中玉箫上。江诺浅浅一笑,冷冽气质转瞬荡然无存,反像个温润如玉的陌上公子。他款步到祈谷亭边,折来一枝桃花。花蕊是勾人的红,红一点点蔓延,一点点变淡,到花瓣边儿上,化作嫩嫩的粉。
而他用这一枝娇艳的桃花作了发簪,绾起明乡蓬蓬如云的乌发:“不是行及笄礼吗?怎的连头发都不绾上?”
明乡害了羞,颊上飞来两抹红云,却又装作镇定的样子,羞涩笑着问:“你刚才吹的曲子是《桃夭》,你为什么要吹桃夭?”
“公主猜我为什么要吹《桃夭》?”桓常捋了捋明乡两鬓微乱的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公主殿下欲宜谁室家?”
清风微动,阳光微动,树间落下片片红霞,桓常手中长萧浮着阳光,碧玉般通透。他将长萧递至明乡面前:“其实我更愿为公主奏一曲《式微》,只怕公主笑我轻薄。”
他说话的声音柔和,好似含了万千情深。明乡的手动了动,颤巍巍举起来,就要去接。
庄公不知何时近了二人的身,他接过长萧打量片刻,迟疑道:“这玉箫可是名叫离凰?”
桓常侧过头,退了半步行礼方才谦恭答道:“正是。”
庄公便不再言语,只催明乡先回山庄去。明乡却正凝神,不知想些什么,竟是许久未挪步。庄公便又招来止桑吩咐:“带公主回行宫。”
一路上明乡都安安静静的,低眉沉思的样子颇为娇羞。她坐在罩着轻纱的轿里,取下头上桃枝,一只手轻轻沿着花枝边缘勾勒它的轮廓,不经意便又是一笑。
止桑骑着马与明乡并行,却是紧皱着眉,什么话也不说。
行宫是一座山庄,明乡有一个单独的院子。止桑与她自幼一起长大,从来也不避讳什么,便跟随着一并入了明乡的院子。明乡并不一味发呆发痴,招呼着一干侍女将采回的桃花捧出来,洗净了作成一坛新酿,埋在屋前的金桂脚下。
她折花酿酒的举止同往年并无甚不同之处,止桑的一颗心却似悬在喉间一般七上八下。他觉得自己心头藏了许多话,那许多话与她有关,而她在他的面前。
数十次欲言又止,他将话改了又改,终于按捺不住开口问:“公主知道那男人话里是什么意思吗?”
明乡抔上 最后的土:“这很重要?”
止桑俊朗的脸上浮出一片怅惘:“他是晋国流亡的公子桓常。明乡,选了这样的人做夫君,你这一世便再难顺遂了。”
“我知道啊。”明乡甜甜的笑:“桓常擅萧,萧崇离凰。他一开始合着我们祭祀的礼乐吹曲时我便猜到他是谁了。”
止桑把明乡从地上牵起来:“你知道他是谁,却还是愿意和他成亲么?”
明乡点点头,却又摇摇头,松开止桑的手:“我不知道。”
“不知道么?公主已然长大了。”止桑轻轻地说。他因背对着太阳,一张脸在阳光里半明半暗,神色也因此显得不可捉摸,只那一双眼睛,幽幽的暗暗的,好似一口深潭。
“止桑,”明乡对着他的眸底一片波光:“或许我会嫁给桓常。”她说这话时极其认真,以致止桑的面容在瞬间失了血色:“我觉得桓常吹的箫音,清冽且婉转,如三月清风,六月谷雨。”
自行宫回鲁王宫时,庄公带上了桓常。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公布于世的消息里头,说昭和公主在十里桃林里头选中的夫君,是沉日大陆上鼎鼎有名的文人江诺——桓常被逐出晋国之后,一直化名江诺在七国辗转。
庄公把桓常安排在明乡的双棠居住下,如此,即便庄公那里没有发下任何讯息,宫中却无人不知这黑衣公子便是昭和公主的未婚夫婿。
止桑在博阳侯府里住着,心思却总是安定不下来。人在心有记挂的时候总是忐忑不安的,止桑纵是少年英才,却躲不过这常规。他是承了父亲爵位的博阳侯,是正三品的怀化大将军,是和硕长公主的儿子,是明乡的堂兄。
他觉得自己有些煎熬,为这身份也为这放不下的情丝。
他在夏初进了宫。这天天气很好,前一日刚落了雨,空气清新草木葱茏。他刚走到宫门前,却见得一匹骏马从开启的城门里冲出来。马上黑衣男子牵着缰绳将女子环在怀里,转眼便化作飞沙一粒,独剩止桑愣愣站在宫门处。
“侯爷请。”守门卫兵见他恍惚,又急着关上城门,出声提醒道。
他眸光一转,浓黑睫毛遮住眼底流光:“罢了。”叹息的同时有泪水和着落下。
罢了,都罢了。既是没办法放下这身份,自该断了对你的念想。止桑从卫兵手里收回博阳侯令,令牌上雕有一只孔雀,那是博阳侯府的图腾。
止桑在王都过得甚是不快活,且这不快活他还不能挂在脸上。一来二去,整个人瘦削下来,倒像个羸弱文人。他每日最怕的便是上朝,因着上朝入了宫门,他便按捺不住去双棠居见见明乡的心思。一颗心孤零零躺在胸腔里,除了他自己外再无人知这颗心的冷热。
五月,楚国以练兵之名陈兵渠水,止桑辞去禁军都统之职,自请镇守边关。他十岁便在战场历练,十五岁已提了长枪上战场。止桑是以骁勇善战闻名的少年将军,他不怕战争不怕流血,他只怕左胸那颗没了寄托的心。
鲁庄公允了。
下了朝,止桑向庄公请了道口谕,去双棠居向明乡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