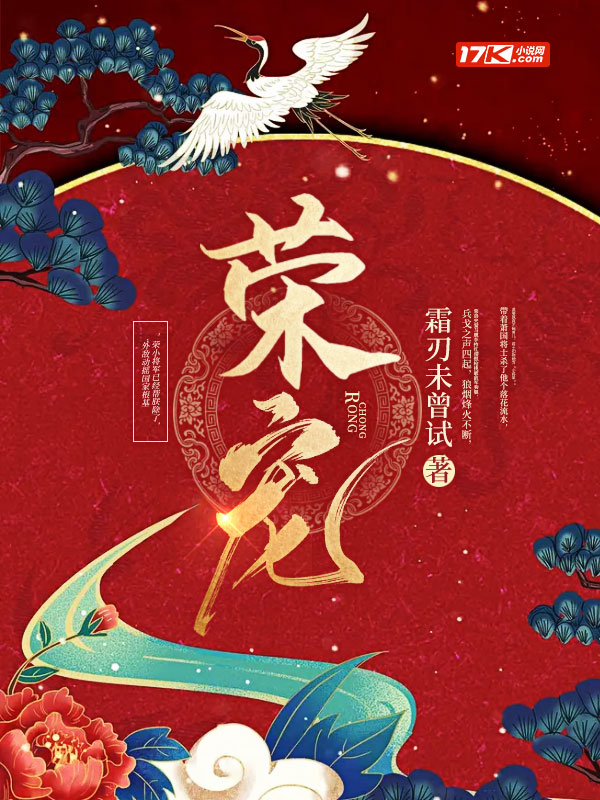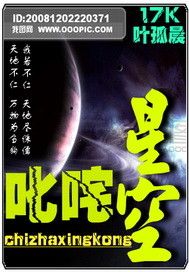事实证明每个人年少时都会遇上那么些个狐朋狗友,楼谷于我便是如此。大概是我给他的印象很是温良,一次与他在幽冥司吃酒时,他拽了我到三生石边拜了把子。
楼谷一贯爱热闹,多次带我避开孟泽四方玩乐,末了,还总不忘告诉那些同行的人我姓甚名谁。当时我尚未获得封诰,仙界没有几个人知道未央宫的主人是长安,但是人人都知道孟泽座下唯一的徒儿叫做长安。
而孟泽的性子一向冷清,素日里忙来忙去也就忙着六界里哪里哪里天塌了地陷了出现妖魔了要派什么什么人去处理。许许多多的小仙儿平日里想要见着孟泽一面也属难得,更遑论摊上什么交情。
可是我不一样,我素日里除了钻研那些个幻术再没有别的事情做。此番我被楼谷拉着在六界乱跑,竟让许许多多的大小神仙乐开了花,以至于我二人走到哪儿哪儿便有一大堆神仙堵着。
从前我想事情不深,自以为是自己人品爆好,现在想想,实在是因为别人想要巴结孟泽而没有门路,所以才在我身上花起了心思。
那时候楼谷正年少热血,时不时会出些诸如拔了青丘狐狸毛偷了东海龙子鳞的事情。而每当那些个受害者哭着闹着拖了自己的父母兄弟过来,楼谷总是很机智的躲在我身后。
不看僧面看佛面,没有人愿意找孟泽的麻烦。
只是好景不长,楼谷五百岁时被他老子丢到了西天极乐地学习禅法,临走前眼泪汪汪地跑上九重天与我作别,还说是等到他学成归来,一定会重新找我吃酒。
我当时也只是笑笑,答了一个“好”字。全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荒羽岛上与世隔绝地住上九千年。
楼谷碰了碰我的酒盏:“在想什么这么出神?”
我强忍住笑,老实答道:“想起了你以前做的那些傻事儿。”
楼谷站起身,将我拉起:“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脸上的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不会,也是来捉我会九重天的吧。”
他笑了笑,望着店里的其他人,学着我先前的口吻:“你声音这么大,就不怕吓着旁人么?”
我并不答话,只静静看着他。良久,无奈地笑了笑:“算了,你应该不会拦着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楼谷带我去了北泽极冰之地。北泽的天地皆是白茫茫一片,狂风夹杂着大雪,一年四季落个不停。
这地方环境恶劣,极少有生命能够长久生存。不过这里生长着一种名唤忆尘的奇特花朵,仙帝特特锁了几只皮糙肉厚的穷奇在这雪原里守护忆尘花。
忆尘的作用是什么来着?忆往生想前尘?
然而楼谷带我来这里,绕过了那只穷奇。换句话说,他带我来这里,并非是为了看那朵忆尘花。
我一边控着周身内力以保证自己不被这风雪冻伤,一边亦步亦趋地跟在楼谷身后。北泽莽莽雪原,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模样,且大风大雪铺天盖地来势汹汹,若非一般的神仙妖魔,根本使不出腾云驾雾的仙术来。
介于我方向感向来差得可以,一路上我都紧紧拽着楼谷的衣袖。
楼谷轻车熟路的走在我前面,像是对这地方熟悉非常。我哆嗦着开口:“你以前常来北泽么?”
他思索了片刻:“一年会来一次,算频繁么?”
我坚定不移的点了点头,又想起他走在我前面,看不见我点的这个头,于是答道:“我以前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你自己对比着看。”见他没有回应,我又问道:“你怎么会常常来这么个破地方?”
他那被狂风吹起的三千墨发在风中张扬,有雪花落在发间,却又迅速的消失不见。他声音冷冷,已不是我熟悉的模样:“再走走吧!再走一会儿你就知道答案了。”
走着走着风渐渐小了起来,雪花也是疏疏落落的,不成规模。楼谷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说:“到了。”
我看着面前的雪原,除却风雪小些之外同先前经过的地方相比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于是我静静站在一旁,等待着他下一步的动作。
“你不像从前那么莽撞了,姐姐。”楼谷微笑,忽地张开了双手,从怀里拿出了个墨色的圆环往空中抛开。他的动作奇快,以至于我没能看清楚那圆环有什么奇特之处。
圆环越变越大,升到大约三丈高的空中,忽然急急下落砸在雪原上,并自顾自的转起圈儿来。待到圆环停止转动,被它圈起的地方忽然下陷,现出一道冰雪堆砌的阶梯来。
“跟我下来。”楼谷叮嘱道。
我紧了紧衣衫,快步跟在他身后。
下去之前我以为这里会是一座地宫,但下去之后仅有一丈开来的活动范围使得我生生断了这个念头。楼谷停在面前的冰墙边上,右手握着已经变回手镯大小的圆环从左往右轻轻扫了过去。冰墙在刹那间变得透明,显出明亮的光线来。
而我借着这光亮,看到了两个人——两个安睡的人。
冰墙之中并列躺着一男一女。女子发丝银白满脸皱纹,即便是闭紧了双眼也没有遮掩住她面上的一份不安。而男子一袭黑色深衣,三千墨发散开,与那女子的白发纠缠,俊美无俦的脸上挂着清浅笑意。
我看向楼谷,他仿佛是在笑:“姐姐,我早该带你来拜见父君和母亲。”
“母亲……”我愣了愣:“阿谷,你的母亲……是凡人?”
他点了点头:“是啊,我的母亲是个凡人,父君终其一生也没能让仙界接纳她。若不是幽冥司司主代代血脉相连,而父君是独子,指不定仙帝会拿出什么法子来惩治他。”
我转头看向厚厚冰层中安睡的两人:“既然如此……”
“父君对母亲用情至深。母亲去后,他将母亲葬在北泽雪原,为的便是在这个地方,尸身千年万年不腐不烂。”他忽地笑了:“母亲只生下了我这么一个儿子,幽冥司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孩。那时候吵着闹着要认你做姐姐,实在是因为我闲得发慌。”
“阿谷……”我叫他的名字:“我一直都是你的姐姐呀。”
他微笑着点头,坐在地上:“是啊!我一直都把你当姐姐。可是我从西天极乐地学成归来之后,父君不见了,你也不见了。那时我才六百岁,还不算成年,却要担起幽冥司这么大一个担子。姐姐,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心里头一时慌乱无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楼谷。记忆里他一直是骄蛮的小公子,任性,贪玩,偶尔胡搅蛮缠,可是从来不会这样安静地诘问。声音卡在喉咙里,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楼谷却在这个时候笑了一笑,换了轻松的语气:“算了。你的那些事情别人不知道,我却清楚得很。荒羽岛四季如春,可是姐姐,你一定不会过得很开心吧?”
我在他身边坐下,叹了一口气,慢慢伸手拉住他的手:“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不过我的肩那么高,可是现在我们坐在一处,我却只有你的肩那么高。”
“姐姐又要避开这个话题了么?”楼谷侧过脸看我:“当年我与你结拜是知会了父君的,幽冥司名册上也添了你的名字。姐姐,在父君面前,你也不愿意说出心里话吗?”
“阿谷!”我狠言道:“你今日将我找来,究竟所谓何事?!”
楼谷见了我的恼怒模样,嘴角笑意越发深了些:“姐姐从前,是倾慕过孟泽神君的吧?”
墨色圆环被他拿在手中反复摩挲,摩挲的同时还时不时敲敲冰面:“姐姐不要不承认,流破山上的两百年加上玉华殿的三百年,你若没有对孟泽起其他的心思,打死我也不信。”
我默然不语,听着楼谷在我耳边絮絮叨叨:“最开始我拖着你四处玩乐惹祸的时候,你总是胆怯说不敢,是担心孟泽会责怪吧?后来你总是由着我将你带往各处,并且做出的事情比我还要张扬,是因为你发现孟泽总是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你收拾烂摊子吧?你这样在意他,以至于要用顽劣的作为来引起他的关注,不是倾慕是什么?”
“够了!”我打断楼谷的话:“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话?拜把子的兄弟?幽冥司司主?还是仙界说客?!”
我解下腰间挂着的司命雕像,温润白玉线条柔和。我摊开手心,将司命雕像放在楼谷面前:“你不用去揣度过去的我是什么样子了。因为现在住在我心里的人,是送我这个司命雕像的男子。”
楼谷怔怔看着我,良久,别过眼去。墨色圆环被他放在地上的凹陷处,整个冰面发出耀眼光芒来。待光芒散尽,脚底的冰面也变得透明。
透明的冰面之下,躺了一名身着嫁衣的女子。那女子样貌清秀,纤长睫毛即便隔着厚厚冰层仍旧清晰可见。只是嫁衣上面有好几处破损,破损处有血污将嫁衣的颜色染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