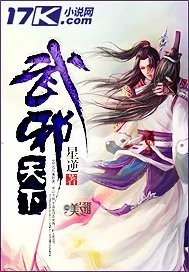此乃多事之秋,先帝驾崩,太子年少无能,沉迷黄老之学,大权旁落,奸人当道。朝廷党派争斗不休,藩王割据混战,最后淮南王从中杀出一条血路,登.基称帝,年号永熙。
秋风萧瑟,西北的刀子正割着囚犯的皮肉,菜市口的血迹犹存。许多未站在淮南王一方的官吏,或多或少有些担忧,有的已经闭门不出,写好遗书,备好财产,等着来人提着自己的脖子复命,只求保住家人性命。
所幸礼部并未牵扯太多朝廷争斗,其中的邓英邓郎中也是个兢兢业业恪守本分的五品小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家中妻女暂未收到牵连。
至少现在邓家的人是这样想的。
今日十五,本是圆月团圆之际,却是乌云密布,无一点星子,家人分散,秋蝉恹恹无声。
一青衣女子软软地倚靠在窗前,两眼微红,目光迷离,双颊白皙,无一点血色。她似望向石子小路延伸的远方。邓絮的父亲邓郎中留在礼部策划新帝祭祖的事宜,母亲留在外祖母的姐姐长安公主的府邸。邓絮只能与沾衣相伴。
沾衣就在她的身侧,站得端庄笔直,双目如黑珍珠般发亮,颇有些英气。
今上的长子,当初的淮南王世子。当初与邓絮有缘,曾温柔以待,却坦言自己是断袖。或许是报应,他已经死在了平乱的马上,尸骨埋在土里也有一月有余,怕早已经被土虫啃烂了。
可惜邓絮今日才从当今皇后信里知道此事,一时间竟忍不住为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痛哭流涕。
再过半年,到了来年玉絮纷飞之时,她就是个双十的老姑娘了。
邓絮收回目光,撑住椅子起身,拿起茶盏旁墨迹斑斑的信件,端详了片刻。表情是千变万化,最后都化为喟然一叹。她提腕将信纸置于烛火之上,火舌慢慢吞尽纸张,飘落下几缕灰色尘埃。
的确是对不起她。邓絮这样想。可是和死人计较又有什么用呢?
沾衣总会看透邓絮的心思,劝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既然拒绝了小姐,那便是天涯陌路人,况且还有沾衣在侧,小姐不会孤单。”
邓絮掩唇一笑,柳眉微蹙,“你不同我,你师傅营子里面,喜欢你的比比皆是,只要你愿意,我做你的妹妹,送你出嫁又如何?”
沾衣面色凝重地摆头,“小姐明白,何必打趣我。那些个连我都打不过,怎的叫我看得上?”
“是啊,”邓絮苦笑,转头望向窗外的小道,“可我爹娘就我一个女儿,我总要给二老送上一个孙儿吧。”
断子绝孙,老无所依,不能儿孙满堂,承欢膝下,于邓絮父母而言,的确是悲哀。况且邓絮只是一介女流,有德有才又有何处可以施展?如何为家人博取半分颜面,如何供养病弱的母亲和自己?
可邓絮自幼有些高傲气,看不上普通凡民,看不上叫她续弦的老头子,更看不上要纳她为妾的风流子弟。
若是……邓絮摇了摇头,世上哪有什么若是。
一阵风吹动烛火,烛火疯狂地摇曳起来,邓絮的脸也忽明忽暗。沾衣起步欲关上窗子。脚步声,木头嘎吱的声音异常响亮。
邓絮再看向静静燃烧的烛火,思索片刻后,微微摇了摇头,“其实我更担心爹的处境,当今陛下性格古怪,稍微有疑点的,都要丢半条命。唉!娘亲不得不东奔西走四处求人。说来我也不是个好女儿,连亲生母亲的身世也不明白。”
“夫人只是想瞒着小姐。”
“是啊,我当初就不该问的。”邓絮道,“祖母早逝,祖父懈怠,母亲本就不喜他们,嫁给父亲的那一刻就不是什么县主了,如今又要捡起来这层身份,拜访皇室宗族子弟。”
邓絮叹了口气,脱下外衫挂在床栏上,朝沾衣道,“你今夜陪着我别走了,一个人怪冷的。”
说完,邓絮自个儿踢掉了鞋子,爬到了床榻里面,钻入棉被,背着光躺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