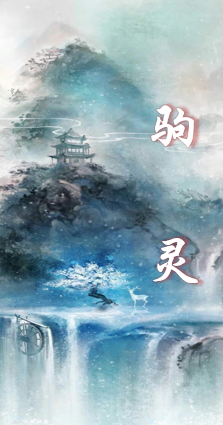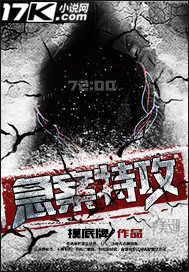奴隶,这个词对于贾仁义来讲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甚至可以说,相较这些已经禁止贩奴数百年的胜国人,他才是最了解奴隶的那个。
和奴隶朝夕相处的日子太久,让他都有点忘了,奴隶好像不只是商品。
听了李二狗要求的知府也不由得沉默了片刻,然后才挥手示意捕头带队去将奴隶们请回来。
轻拍惊堂木宣布休堂,知府却没直接回转到堂后去休息,而是从桌案后走出来,下了高台,站到衙门口。
门外的百姓不知知府是何意,但都自觉地向后退让开。
衙役们很快站到百姓前围成人墙,将知府和大家隔开保护。
耳中听着百姓们的夸奖,知府一言不发,怔怔地看完了一切,向前鞠了一躬,不做任何解释。
起身走回桌案后,这个修为超群又尚处中年的官,脚步略显蹒跚。
人人都在看着知府莫名其妙的举动,却不明白他意欲何为,唯有陪伴他多年的老师爷隐约能猜到些什么,为其添上些茶水后就留他自己独自悲春伤秋。
为官近五十载,自二十出头高中进士名满旧都后就被下放到边疆的小城做了个芝麻官。
九品官一做就是三十年。
有人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他倒是不穷,少年得意,青年失意。
本以为莫欺青年穷之后是莫欺壮年穷,无数次努力试图获得晋升无果,已经认命的他又因为当年无意中得罪的世家被对手击败而获得启用,只能苦笑世事无常。
三十年扎根小城里,实打实为百姓们做的实事儿变成了政绩和官名。
与百姓情似鱼水,就是他远近闻名的官名。
芝麻开花节节高,苦尽甘来之后官儿升得也比烟花还快。
连李铁柱这从农家汉摇身变为国主的人都听过他的大名,上位铲除了害群之马后就把他从邻府提拔了过来。
转眼间第二个三十年过半,他成了旧都这一国京师的知府,四品大员,却在刚刚才发现自己一直以为保持得很好的官名好像早就变了味。
和自己国家的百姓都产生了距离,不把敌国的奴隶当人看待似乎也不是很奇怪。
知府不走,大堂里的众人也只能沉默地等待,心里催促捕头赶紧归来。
好在是罗捕头亲自出马,苦练多年的轻功着实不俗,全力施为下仅花了半个时辰就提了人回来。
骨瘦如柴的奴隶女子其实对于罗捕头而言没比拎根水火棍费力,但尊重使得他选择背着对方返回衙门。
牛兰珊见到女子露出很惊讶的样子,不停做些小动作想跟李二狗说些什么,还是李二狗见她这幅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认识这名女奴隶的样子轻踢了她一脚才没暴露更多。
面带畏惧的女子一见到贾仁义等人就哆嗦得不成人样,话都说不利索,赖在罗捕头背上不愿下来,恨不得变成他背后的纹身一般。
没法子,知府让衙役去堂后把他的屏风搬来,将贾仁义等人隔在一角才算完。
“这女子,今日将你请来是想问些昨晚发生的事情。按理来说你昨晚应该目击了一场搏斗,具体情况如何你能否跟大家娓娓道来?”
在心中立志要做出改变的知府放低姿态,用尽量温和的语气和表情对奴隶女子问询,但对方一开口还是让他微微上扬的嘴角忍不住抽搐。
没办法,女子带有口音的黑国官话为大家生动形象地解释了什么叫对牛弹琴,驴唇不对马嘴了属于是。
刚有起色的大堂内气氛又降至冰点,好在博学多才的御使大夫及时挺身而出,充当翻译一角才解了尴尬。
恰好没看到这种无谓的担心没出现,女子经过商人平日的训练已经有变得对他人的要求言听计从的趋势,弄明白问题后就滔滔不觉地描述了昨晚的状况。
语言不通成了美妙的巧合,她根本不知道李二狗和商人们说过的话是什么意思。
只说她见到自己所在车厢的门被贾仁义打开后,拖出了被矮胖商人刚放进去不久的口袋,与里面钻出的人对峙一会紧接着就动了手。
因为她下午曾经逃脱又被捉回去的原因,她正巧位于车厢的最外侧,将全程看得一清二楚,描述起来也详实生动,再通过御史大夫这文化人的二道加工,听起来比评书过瘾。
意犹未尽的知府依据李二狗的第一口供设计了几个问题,其中几问的题干不乏故意错误地提供信息,但最后都被女子正确回答并纠正,强有力地证明了其与李二狗证词的可靠性。
心满意足地让衙役将女子领去找自己夫人代为临时照看,知府看着撤去屏风后面色惨白的贾仁义发出几声桀桀怪笑。
懒得再委婉一下,知府直接问道:
“认罪吗?”
大家都是聪明人,贾仁义知道在会审的三司代表面前不会让他认下之前未曾提及的罪名,为求体面索性落落大方地认了。
对方认罪是胜利的初步保障,知府让衙役将昨晚收缴的兵器呈到堂上,确认道:
“你们人数占优,兵器占优,甚至还持有军械,围攻一名你们只知道是丑段甲等实力的人,故意伤人是事实,说是故意杀人未遂也成立。”
“据证人描述李二狗制服你后第一时间停了手,结合宋仁骰的证词他并非自愿前往客栈后院主动滋事,对我判定他为正当防卫你没疑问吧?”
被拿捏了死穴的贾仁义不再挣扎,虽然明白了前面大张旗鼓给宋仁骰定罪的目的,但是实在是已经没了翻盘的条件,连拖李二狗下水也成了奢望,只好有气无力地点头同意。
“好!那本官宣判……”
正要宣布定罪的知府忽然被李二狗打断,暗自惊讶他竟然还有后手,没多说什么,示意他开口说出要求。
后手有时是埋伏许久的伏笔,但有时也只是神来一手。
李二狗要求不多,开口道:
“我请求知府大人传胜必钱庄管事。”
没能理解是何用意的知府没盲目应下,追问这位管事在此案中充当什么角色。
“我在胜必钱庄为我的脸办有保险,每年需要交纳整整三百两白银。具体保额为……”
转身对着贾仁义邪魅一笑,他轻声说出了那个数字:
“白银一百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