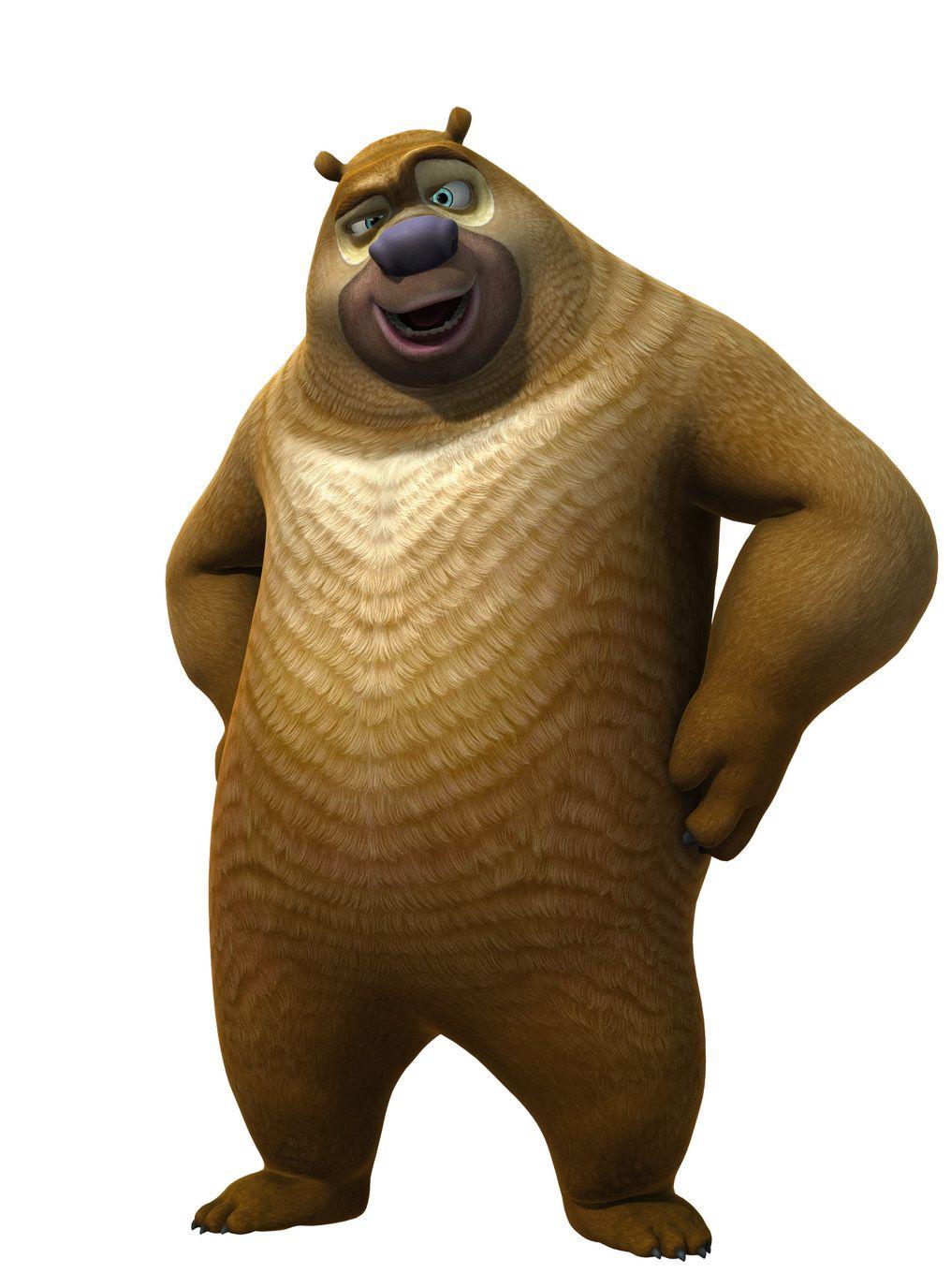就算为了对得起如李皇子一样的人们做出的无私奉献,自己也要在追求公平的公正这条路上走下去。
信手抄起师爷做的笔录,捕头大致扫了一眼就盖上了自己的私戳,确认绑架案暂时告一段落。
继续在上面做文章已经毫无意义,在后面的斗殴案上划分清楚罪责才能击溃这个有牺牲觉悟的利益团体。
套路性地轻咳一声作为开场,重振旗鼓的捕头开口道:
“现在开始采集有关斗殴案的笔录。你们双方谁先动的手?事情经过又是怎么样的?”
已经获得捕头感情倾斜又是独自一人作为一方的李二狗自然又成了先攻,先声夺人道:
“你们收缴的在场兵器里压根就没我自己的家伙,人数上也不占优,谈判崩了就遇上对方想杀人灭口了呗。”
轻咦了一声,捕头让后面收拢了证物的捕快把凶器都呈到栏杆前,指着其中的木鞘黑刃短刀问道:
“我们进到后院的时候你是手持这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吧?这不是你的兵器?”
凡是参加过今早堂审的人都觉得这短刀眼熟,因为风格上和付贵那把完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是刀身换成了黑色的乌钢,更坚韧也更危险些。
极简风格某种意义上倒也是独门特色,这样一把个性鲜明的武器实在很难让贾仁义启齿说这是李二狗提前准备的同款。
或者说,他直到发现李二狗有寅段实力之前都不明白为何对方敢于孤身赤手空拳地单刀赴宴。
见到贾仁义光棍地承认这是他被夺的短刀,李二狗也承情地老老实实按照事实简单复述了动手的经过。
没升上卯段前,修炼者间的搏斗其实和常人打架区别确实不大。
没有那么多刀光剑影,遵从人类作为高级动物的本能而使出的一招一式全部都基于致对方于死地这个简单目标,描述起来格外干巴巴。
如果不是当初隔着老远都清晰可闻的惨叫和眼下仍旧显得触命惊心的几个伤口,李二狗描述里的战斗经过似乎还不如衙门里养的那几只猫儿打架来得精彩。
已经多次和李二狗唱对角戏的贾仁义开始习惯了对方这种平铺直叙式的先手。
用事实说话,这招就像象棋里的拱卒,让他每次想找出漏洞来反打都有狗拿刺猬的棘手感。
硬要说,可能唯有李二狗因为是先手而无法说得过于详细算是个破绽,给了他在留白处肆意涂改的机会。
看到捕头的示意,想好切入点的贾仁义说道:
“我夜间闲来无事清点货物的时候无意间在车厢看见了之前没见过的麻袋,将里面的李大皇子解救出来,还没等我问清状况,反倒是他倒打一耙,质问我为什么将他掳过来。”
心里明镜似的知道捕头和师爷根本不顶啥用,真正能拍板的唯有今日见过的那位知府,他连白天那种造作的表演也无,保持话语里丰富的情感已是最后的诚意,接着说道:
“我哪知道我是被自己人的邀功给陷害了?这话就说不清了。我是姿态做尽,甚至主动提出哪怕跪地磕头也要让他平安地回家,可不敢拦着这位寅段高手的路啊!”
“谁知,人家根本不领情,就吃定大户了,非要我拿个赔偿的章程出来。不怕各位笑话,我这商人老话讲是上九流里的臭老九,要别的不怕,就怕要我钱袋里的命根子。”
说个不停的贾仁义语气起承转合间变幻不定,对比之前李二狗的版本称得上一声引人入胜了,但面上略显僵硬的表情在灯光下又显得怪异诡谲。
负责记录的师爷很想将此刻贾仁义的脸一并临摹下来,明日呈堂给知府的时候也好叫老爷知道这话到底有几分可信。
转念一想,又回忆起知府今日最后怒摔惊堂木的表现,显然也是清楚贾仁义是怎么样一个人物,放下了无意义的担忧。
正说到谁先动手这关键的贾仁义感情又踏上了新台阶,激昂地说道:
“李大皇子见我不识抬举,索性打算仗着自己有道理直接到我这来强取豪夺。我又不知他真真地占着理,哪里肯答应,但技不如人,还是被他掏了怀。”
一指地上的短刀,贾仁义最后补充道:
“我怀里只揣了这把防身的短刀,被他掏个正着。眼瞧着他夺了刀,我还哪里敢大意?赶忙召集人手保护自己,结果似乎让他以为我是要群起而攻,抢先对我动了手。”
故作无辜地摊摊手,贾仁义很明显意思是懒得再重复一边具体的战斗经过,引得捕头和师爷都难以抑制地露出不悦的表情。
可惜,二人的不满不能在笔录上展露丝毫,因为带有非案件当事人主观情绪的话一旦出现就算是污染了可谓最为珍贵的第一次口供。
在这个证据难以保留的现状下,第一次口供笔录通常是一切判断的根源。
就算后续改口,新提出的观点如果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撑,官府也往往更倾向于依赖理论上更接近案发时间也即记忆更清晰时做的第一次口供记录。
这份证据一旦因为被污染而作废,逆转生死当真就易如反掌了。
实在是历史上少有的几次被三省发回重审的案子里,被翻案的大半都是最后落在证据被污染导致的证据链断裂或证据缺失。
强忍着恶心,捕头拿起记录细细检查过,确信师爷没有马失前蹄,在末尾压上自己的私戳,又请师爷盖过,最后让犯人们各自画押。
李二狗恶趣味地直接从脸上的伤口抹了一把,疼的呲牙咧嘴的同时留下了一个略显怪异的小号指纹。
相较周围割破拇指留下的大号指纹,显得鹤立鸡群,格格不入。
师爷用早就备好的纸袋和火烛蜡封好笔录,急匆匆地走了,忙着再另备一份卷宗明早给知府提前批阅。
早已待不住的捕头也想走,却被李二狗拦了一下,被提了个小小的请求:换牢房。
其实他不说,一会也免不了将所有人隔离关押,因为要避免串供出现。
哪怕已经出现了。
沉默式串供使得即使是会记录下牢房犯人关押期间所有话语的旧都府衙也束手无策,或许互相不能照面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地面上的牢房怎么数都是不够用的,捕头哪怕是将商人们分别塞入其他案件犯人的牢房让二人同挤一间,还是有五六人要去地牢里对付一晚。
为了图个清静,李二狗又一次挺身而出,主动申请自己去地牢占个单间。
理所当然,得到的答复是捕头对他头脑是否被哨棒敲坏的检查和翻着白眼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