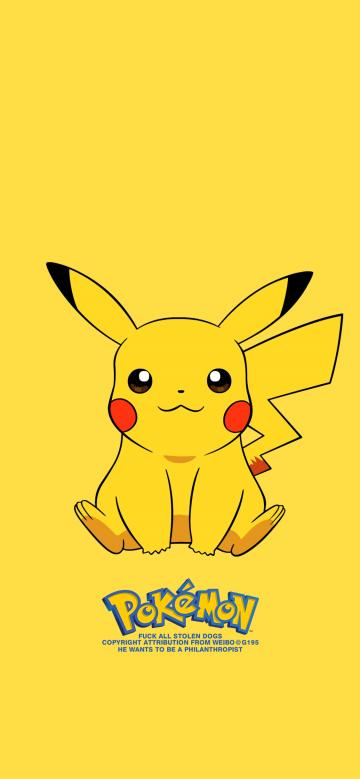俄日敦达来晓过了吃萝卜不能一个人吃的理儿,拿联络员来捆绑巴雅尔。
巴雅尔脑瓜子里钻进了一窝土蜂,嘴里出了声:“再好的轮胎,干不过尖尖的石块。”
隔了一夜土蜂全飞走了,他琢磨起了牧民合作社这事来了。
念头起来了,现实摆在眼前,有几个牧户想入合作社,中间隔着阿来夫和岱钦。
把中间的网围栏拆掉,牧场连成一片,恢复到以前嘎查集体放牧的那样,扩大了草场范围,大牲畜能到处溜达,减轻了对牧场的践踏损害。
轮流打草,牛羊有了四季牧场,草场能得到休养,把一块一块的碎片草场整合起来,以草场和牲畜入股,打草接羔剪羊毛的人手多,统一雇佣羊倌,省钱省人,多余的人手到矿山油田煤矿干零星活,多挣些钱贴补家用。
更重要的是打防疫针、剪羊毛、配种、接羔子、打草,到最后卖到冷库一条链下来,量大好讨价,到手的钱还快。
查娜的眼光随着他说话的声调上下跳动着,脸上的肉块让上下翻动的眼球拉的一会笑,一会嘟嘟嘴。
她想要是入了合作社,接羔和剪羊毛需要的人手多,一家出一个人就够了,自己就不用去了,去食堂还能挣一份钱。
自从牧场分到户以后,接羔不是两个人能忙过来的活,要找人手帮忙,人家也要接羔啊。
打草更不用说了,都集中到那几天,更是找不到闲下的人手来。
人手多了好搭配,接春羔早冬羔和冬羔,人手更充裕了。
让人受累的是给羊打针防疫的事了,羊痘、胸膜肺炎、口蹄疫、破伤风疫苗啥的都要打,累得腰抬不起来。
一个省钱的事,不用红砖和水泥砌个大坑了,给羊“洗药澡”了。
五六家买一个打药的泵子,用红砖垒两个圆形的圈,人站在内圈的出口处,用水龙带的喷头给羊一个一个的洗药澡。
羊从大圈和小圈间的通道出去,一个也不会落下……
巴雅尔和冷库的关系好,冷冻白条羔子。
阿来夫醒了一半酒反悔了。
查娜骂着:“生孩子痛,下辈子都当男人啊。男人和男人贴在一起生不了孩子,找谁放羊去呀,他有那么那坏吗?反过来你能做到他那样?”
“好事,他不会拉外人入伙的。”
“烫了舌头就不吃饭了,胸叉肉没少吃一口,血肠也进了肚子里。啥时能改掉心服嘴不服的怪毛病,这是你一辈子的病。” 查娜埋怨着说。
第二天日头爬上山包有半个套马杆长,岱钦在阿来夫的门外喊话了。
“昨晚你说啥啦,DNA的钱给够数了?”
岱钦一直惦念着那2万的DNA钱,要上来有跑腿钱。
孟和前两天买了羔子,兜里有钱了。
阿来夫推开门:“没啥,就是合作社的事。”
岱钦说:“他也找过我了,说过一大堆的好处。”
阿来夫回过头来说了一堆不入社的理由。
查娜把阿来夫凉到了岱钦眼前。
“惯坏了的臭脾气,不知说啥好了。不值钱的泪再多又不能当盐吃当水喝,哪件事能捋直啊?”
阿来夫把头发在眉毛上面捻成一缕,和牛的尿线一样, 硬是顶着嘴说:“他就是个糖姜,外甜内辣。他能瞅准啥啊,入合作社的事,他闹不成。”
在岱钦面前,查娜没给阿来夫留一点脸面。“你是头顶上敲铜盆子,越敲越响,给自己大胆啊,咋说他闹不成?”
岱钦接着俄日和木的电话出了门。
俄日和木算着自己的帐,对清点数量的人,塞几条烟就完事了,用不着藏着掖着的。草场租金没少交一分,能多一头就多一头,租期到了走人。
这块牧场隔断了西边三户牧民,对入合作社拆除中间的网围栏阻碍很大。
巴雅尔找俄日和木也没有办利索。
俄日和木说:“我撤走,那几家包我一年的租金。”
岱钦瞪大了眼瞅着他:“瞎球闹……羔子卖钱了,让谁包呀?”
俄日和木硬是不卖他的帐,拿驼腿堵他的马腿。
巴雅尔喊来岱钦、俄日和木和那三家牧户一起喝闲酒,说到了自己认识一个有钱的朋友要来牧区整合旅游项目,就是北边砂石路不远处的“圣泉”。
每年的“那达慕”有好多人过来用矿泉水瓶子装水回家,说是喝水能治好胃病。
夏天来旅游的人,也闹着去装水,有人挂在网上,说是能治脚气和睡眠。
“圣泉”的一边,插了一个牌子:欢迎热爱草原的朋友来牧区旅游,请您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牧草,不要随手乱扔垃圾和杂物。请您放慢一下脚步,耽误几分钟看一下下面的文字,会对您草原之行有很大帮助的。再次欢迎您来美丽的牧场观光旅游。
您随手扔的各类垃圾,在牧场完全降解时间表,多可怕啊。
棉质手绢2—5个月。
牛皮纸袋3.5—4.5个月。
玻璃瓶4000年。
铁罐10年。
塑料袋100—200年。
塑料打火机100年。
烟头1—5年。
尼龙织物 30—40年。
易拉罐80—100年。
橘子皮2年。
羊毛织物 1—5年。
车票3—4个月。
俄日和木觉得巴雅尔说得不假,要是“圣泉”旅游项目整大了,也在牧场里闹个“度假村”。
他在那七八个井口转悠了一天,游客说的格外神奇。
每个井口用木板封着口,深一点井口上有木栏杆围着。
井口间隔不到6米,水的味道却不一样。大一点的那个井让那个人说活了,水井里一直冒着气泡,游客把头探进井口大声吼着,气泡冒的格外多,引来了好多人瞅着井口。
说这口井的水能治拉肚子和胃病,往南的那几口井能治疗皮肤病、眼病、口眼歪斜,最后面的两口小井里的泉水不能喝,西面的那口井专门用来洗头的,治疗脱发和睡眠不正常的,北面是洗脚的,治疗脚气很管用的。
俄日和木把群羊交给了两条大黄狗,套马杆倚在那个牌子上,混进游客的群里听那个牧民说了大半个上午。
往西瞅了一眼,离大一点的那口井近一点的敖包南面坐了五六个人,把膝盖以下的部分用灰白色的稀泥包裹着。
一个岁数大一点外地口音的女人,一边抹着稀泥一边说,来这里有三年了,风湿痛好多了,这灰白色的泥巴治疗皮肤病比药膏还管用。
照着那个牧民说的次序,俄日和木挨着取水试了7天,没觉得有啥效果。
吃了沙葱包子和韭菜花酱,胃烧得厉害。
提了两大塑料壶水洗头,头发一点没少掉。
游客信那牧民口里的话,一传十十传百来喝水抹泥巴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琢磨来琢磨去的,巴雅尔蛮够意思的,让俄日和木把羊群挪到他牧场里去,那里的草比这里好多了,不愁贴不上膘的。
俄日和木打心眼里偷着笑,这事要是挪到自己身上,心没有他这么大。
巴雅尔一手压在头顶上,一只手顶在腰带上,指着酒杯:“血压到了110--175了,不能闹了,倒下可坏大事了。”
俄日和木擎着酒杯,激将着说:“你不接这杯,我咋给岱钦满上啊。我这人最大的坏处是好事忘不了,坏事记得更清。黑白能分清的,我再敬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杯。”
岱钦瞅着巴雅尔闹的差不多了,把俄日和木和自己的杯子全灌满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走一个。”
放下杯子心里的气还没顺出来,租了我的草场,赚了钱不说一句暖心的话,我倒成了做坏事的人,灌死你。
瞅着像狗一样趴在桌上的俄日和木,他又哨起了巴雅尔:“拿血压高说啥事啊,那是你家的祖传,高压闹到200怕啥,顶得头皮发涨是你摊上了好事,趴着的这人,忘不了你的。”
俄日和木顺利和巴雅尔更换了牧场。
巴雅尔把挨着矿山油田和煤矿的草场全弄到了手里握着,办牧民合作社是早晚的事了,心里的底气更大了。
……
岱钦帮阿来夫追回了孟和欠的2万多块钱,去老丈人家祝寿,头一嘴就告诉了舅子媳妇。
阿来夫姐姐脸上挂着那层冰,让笑挤得噼里啪啦掉到了地上。
伊日毕斯喜欢吃奶皮子,瞅着锅里的奶茶翻着水花,喊着儿子:“多放些奶皮子和炒米,还有肉干。”
又瞅着伊日毕斯说:“嫁出去的回娘家是客人。你血肠灌的不赖,瞅一眼你哥,磨磨唧唧的还没杀利索呐。”
岱钦和孟和是同父异母的连桥。
阿来夫的姐姐瞅着伊日毕斯:“不是一个包袱里出来的,远了一步。你也操了不少心啊,钱,总算拿回来了。”
阿来夫去孟和家拿钱,碰上了巴雅尔,三个人一起闹多的。钱没到手一分,赚了一肚子酒回来。
夜里落下了一场雪,牧场上白晃晃的一片,小动物下了平日人们难以察觉到的痕迹。
大黄狗的叫声,打破了草原寂静的夜空。
岱钦把袍子披在身上,看见不远处马上驮着一个人,歪斜着坐在马背上。
他喊着:“这不是阿来夫嘛,好赖上了马,要不会冻死的。”
边骂边从马背上把乱醉如泥的阿来夫背进包里,死沉死沉的,浑身没有了支撑。
查娜接过了伊日毕斯送到手里的2万多块钱,顺手塞给了她2000元的跑腿费。
阿来夫硬着脸说:“那天闹多了,忘了桌子底下的那包钱,喝酒前孟和就塞给我的。”
隔一天,巴雅尔过来争功了。
查娜打量着他:“没把钱塞我手里,凭啥拿跑腿费啊。只进不出,啥时能倒过来。”
巴雅尔和走黑夜路自己哼唱着给自己壮胆:“我跟孟和磨了老半天,才吐口给钱的,闹多了没让阿来夫拿,丢了可咋办啊。一个说给了钱,一个说没拿到钱,我夹在中间算啥呀。我没捡到钱,掏腰包给垫上?我可是动了嘴跑了腿的。”
阿来夫捏着鼻子:“没入合作社,就赖磨钱了。到了那天,能把我大羯子当苏白的价卖了,不入了。”
巴雅尔把帽檐向右边一拽,露出了圆圆的小尖眼睛。我按着你的手不让你拿钱走,一捆醉烂草,那一把“毛爷爷”能捏回几个,回家。
他闭着眼像画圈一样比划着阿来夫的草场,孤单单的甩出去碍不了合作社的事。
眼睛瞪得大大的,甩出和马镫一样硬的话:“你自己提出来也好,没打算拉你进来,冷库放不下那些‘白条’啊。”
小孩在别人手里长得快,这事摊在查娜头上,一天比十天还长。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硬是不见巴雅尔的影子。
阿来夫坐在炉子边上,捏着一大块粪砖。
查娜说:“掰开,炉口放不下啊。等等等,啥时是个头啊,半个月过去了。有尿,把他拽回来呀。”
阿来夫出门了,瞅了几眼商店的方向又回屋里了。
人和羊不一样,羊爱扎堆,人总爱和身边混熟了的人吵架说狠话,碰到不熟悉人,说心里话。
巴雅尔和水一样,能把脏衣服洗干净,也能把干净的衣服染脏。
他是小孩拉屎头硬,一个月过后憋不住气,一天一天的数着手指头,他找到阿来和岱钦夫去毕利格饭店又喝上了。
他越是这样说,阿来夫心里越是放不下,孬事盼着走掉,好事怕贴不上,拾杯前一遍一遍的告诉自己,喝三两杯就走人,怕闹多了把持不住说漏了嘴。
巴雅尔早摸透了他的习惯了,在前面领着路,喝一口说一句,几杯下去阿来夫交底说了大实话。
他到外屋把喝闲酒的工区长喊了过来,他们几个是阿来夫要好的赌友。
见到他们几个,阿来夫眼球暗淡了几秒后发了绿光,拉直了脖子嚷嚷着,碰着杯吼着歌,彻底“断片”了,说了些啥打死也想不起来了。
岱钦说了假话,说是矿山几个要好的把阿来夫灌多了。
查娜歪着头盯着他:“兜里没钱了,那几个赌鬼不会白白和他在一块喝酒的。你的网围栏啥时拆掉?入了合作社,一块打草,一块打防疫针。”
岱钦挠着头瞟了一眼小虎牙,舌头顶着牙齿滋滋的响,漫不经心地说:“网围栏过几天撤,巴雅尔找人过来帮忙。”
他这几句话,是巴雅尔用200块钱让他说的。
他有意扎查娜的心:“听说你不入社了,亏大了。网围栏撤掉了能卖钱,接羔打防疫针和打草配种之类的事,省下好多钱。”
出的话是一块通红的粪砖,烧得她心肝熟透了一半,却硬着牙齿,不把事放在心上:“拆掉了中间网围栏是一片大草场,耙子混群下的羔子,咋DNA辨别啊?”
岱钦听这话有了活口,费几下嘴皮子又能赚回200块,又说,“女人脸皮薄,抹不开脸面,回头我找巴雅尔说两句,咋说也是同父异母啊,人不亲血亲。”
查娜想到给羊上保险让人骗了钱的事,担心羔子杀成了“白条”堆在冷库里拿不回钱来……觉得巴雅尔靠不住,保险的事是他扯上阿来夫的。
又改口说:“我才不稀罕他的那个合作社,是好事,他不会拉那么多人进去。和上保险的秃头李经理没啥两样,揣着钱跑人了,现在没见个影子。”
她只是随口说了一嘴,岱钦眼睛里飘过一丝忧愁,却宽着她的心:“牧场摆在这里,他又搬不走。真到了那一天,重新把铁丝网拉起来就是了。你是烫破了嘴,不敢吃把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