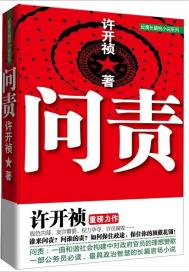嘎查长接着满都拉的电话,嘴里答应了一百个好,腿脚就是不动弹,即便和巴雅尔在一起喝酒,也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满都拉急了找到了额日敦巴日,用商量语气说:“要不,中午杀只羊,以我的名义请巴雅尔兄弟俩喝顿酒,拉近一下关系,接受草场补偿的价钱,苏木长就差点把宰羊刀架在我脖子上了。”
嘎查长答应着:“好,好!所长看得起我,我亲自动手杀一只大羯羊,犒劳犒劳你。”
他只字没提巴雅尔,心里在骂着:“今天你吃我一口,明天要还我一斗。白白破费了我1800块钱。你啥时请过客,都是带着嘴吃人家的。”转动着白眼球又说,“你车里有好酒?将就一下,我只有‘草原白’,是‘高草’。”
巴雅尔他们眼看就进门了。他说:“高草’劲大,就喝这个。几杯下肚,巴雅尔能说实话。”
酒醉饭饱后,巴雅尔对2.56元/平米的价儿,死活不同意。
巴雅尔借着酒劲把额日敦巴日教训了一番,酒的好坏与瓶的形状没有直接关系。不管是玻璃瓶,还是瓷瓶,方的也好,圆的也罢,要紧的是里面要装纯粮酒,不能掺水。他眼皮向上翻动了一下:“都是实诚人,不兜弯子了,捞点干货。以心换心把我们的事,当成你的事,嘎查长你能做到了吗?要是占用了你的牧场,你能接受这个价格吗?别站着说话不腰痛。”
“你也配在我眼前说自己是实诚人,你是实诚人,阿来夫算啥呀?大黄狗吃了我扔过去的肉包子,还摇摇尾巴呢。不是骂你,你连狗都不如……你可不要说嘎查是男人的乳房,有其名无其实,奶不了孩子。”
巴雅尔双手十指合拢,端庄的举在额头前,双眼自闭不闭慢慢地说:“饶
了吧,饶了我吧!亲爱的嘎查长,不要损我了,你是大人大量,要不……那就3元/平米。钱,是矿山的,又没让嘎查出,更没让你从腰包里往外掏,就像是花了你自己的钱。我不吃独食,会按比例提点辛苦钱给你……”嘘---用嘴撅了一下阿来夫和满都拉,轻轻扇了一下自己不住门儿的嘴。
“我不是菩萨,受用不起。别再折我的寿啦!挤牙膏啊,别再瞎折腾了。一口能吃个胖子吗?这2.56元/平米是政府规定的,你有三头六臂啊,跳出圈外。1706块一亩嫌少啊,非要2000块一亩,有这个价的吗?” 额日敦巴日给阿来夫递过一个眼神,本想让阿来夫点头同意,他却坐在那里痴痴的笑。
“玻璃窗里的苍蝇光亮一片,就是飞不出去呀。这2000比1706可是多出了接近300块啊。2.56元/平米,我看行啊。”阿来夫突然冒出一句,把巴雅尔气了个半死,红着脸说:“没人把你当哑巴。给个饼,狗会啃,还用你来说吗?不滚!欠揍是吧!”
嘎查长指着满都拉,说:“真正的菩萨是所长,送到你眼前了,还不跪下来拜拜。”
满都拉扫了一眼身边的巴雅尔:“嘎查长说错了,菩萨是你,今天我要拜拜你了。”
“受用不起,受用不起呀我的所长。”巴雅尔扯着满都拉的手说。
“光说不练,好嘴。2.56元/平米行不行?爽快点,能死人啊。”嘎查长在一边催促着。
满都拉耷拉着脸,敲打着巴雅尔:“嘎查长可没少帮你的忙,不给我面子,总该给他吧。抬头不见低头见,草场溜达都能碰见。”又重重咳嗽了一声,警告着说,“给人方便了,才能给自己方便。今天我求到了你,敢保证明天用不到我?聚着个眉头不说话,眉间不聚都没有个小手指宽,就这点度量?”
巴雅尔贴着笑脸:“所长平日没少罩着我。这长相爹妈给的改变不了,别哨我了。一切都听你的行吗?”他朝额日敦巴日撅了一下嘴,话里有话地说,“大羯子吃了,起码是三岁的。酒也喝了,这情我记在所长你头上,不会记在嘎查长身上的,明人不说暗话,当着嘎查长的面说。要是背后里说,那是乱嚼舌头。”
“你在哇哩哇哩的胡说些啥,所长没少罩着你,感恩才对呀。你吐句话,阿来夫说的那个价,行,还是不行!这不是剪羊毛呀,慢慢一铺一铺的来。你有闲时间唠叨,所长有功夫听吗?”额日敦巴日借火在烤巴雅尔。
巴雅尔退到了羊粪炉子前了,慢悠悠地说:“我回去跟老婆商议商议,行嘛。毕竟不是个小数目,要不她不让我进被窝。”
“商议啥呀,这点破事,捣鼓了多长了。尼玛的敢耍我,走着瞧。”满都拉满脸气的紫色,摔门离开了。满都拉前脚离开,巴雅尔后脚跟了出来:“所长再容我一天,给您回话。”随后笑嘻嘻地说,“您借我天大的胆,也不敢呀。我这小命,还不是攥在您手里,您张开手,我这小命就有救了;握紧了必死无疑,我心里亮堂着呐,嘿嘿。”
“松开手!别扯着我,烦着呐。晚上等你回话。”说完上了嘎查长的车。
离呼和巴日给俄日敦达来规定的时间还剩下四天。
满都拉没敢当面给俄日敦达来汇报,只是在电话里蜻蜓点水一掠而过,没往深里说。这四天要是放在平常,满都拉会觉得很漫长,说是度日如年有点夸张。可现在这四天对他来说,就像秋天牧场枯黄的草,一把火能烧掉几千几万亩。一眨眼过去了两天,满都拉坐不住了,开车去了嘎查,坐着一声不吭,低着头抽闷烟。
巴雅尔瞟了一眼试探着说:“所长,不要对我有看法。老婆呜呜哭了,我咋办呀。除了草场赔偿的事以外,咱俩之间一无怨二无仇,都是钱惹的祸。人爱钱没有错,不是我无理取闹,不给你方便,这么好的草场,少一分也不行呀。你帮我跟矿山说说?”
满都拉手拍的桌子轰轰响,喷着唾沫渣子:“给脸不要脸是吧!啥叫少一分也不行呀。你拿自己当皇帝啦!就没个来回锯?也太拿自己是个人物了吧。”
巴雅尔仍不死心:“所长,这话太重了,我受用不起呀。脑瓜子有病的苏白羊,也不会点头的,对钱有冤仇的人,才会答应,我闹不机密了。”
满都拉说:“咬定8倍不松口是吧?跳出圈外,要当领头羊啊。成了靶子,会先倒下的。想钱的人,又不是你一个,我也想啊,取之要有度呀。度,就是框框,不能依着性子来。”
巴雅尔说:“说到框框,我也说几句,框框就是规矩呗。干嘛要给2.56元/平米,不给3元/平米。”
嘎查长说:“指导价你是知道的,不要小看多出的0.44元/平米这个小数,你干嘛要跳出框框哪?”
巴雅尔甩了一把清鼻涕:“尼玛的呼和巴日!没放过羊,不懂牛羊的人,白扯……”
满都拉狠狠的扔下一句:“嘎查长的话,没闹机密?你说‘过牧’要看哪个数?是草场里点的数,还是落在本上得数?烧过的开水凉了再烧,和刚烧的响声不一样。早答应了,比晚答应了,要好。别人可不比你傻,老虎不发威,不要把它当病猫,咬到你了,抽不会手啊。”
巴雅尔有点没愣过神来,像喝了咖啡,兴奋的对嘎查长说:“我只是飞机的一个小轮子,高空中没用。起飞和降落没有它是万万不行的,我平时没多大用处,关键时对你不能说没用吧?选举时,我有一票的权利……我闹不机密,从小在草原上长大,草原养活了你,一当上官,就反过来就咬羊,帮挖矿的人找好处……”
所长急了:“别打岔,选举换届那是苏木的事。”
嘎查长来回走动着:“啥叫给矿山找好处?所长去牧场一户一户的查‘过牧’,是闲溜达腿吗?是管着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不顾草场的死活,多撒羔子,不要认为羔子啃不出草根来。”
巴雅尔很快把话题转移到“羊百捞”火锅店上来:“那是旗里的名店,你俩肯定去过,并且不止一两次。为啥叫‘羊百捞’?不就是筷子每次下去都有肉嘛,哪次筷子还有空的?哪次去肚子里不是饱的……羊吃好草,浑身都是好肉,草原破坏了,羊没草吃,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道理就这么简单,有人就想不通呢?羊倌想不到也就罢了。大楼里的那些人,有多少是牧民的儿子,能闹不机密?那可是朝庭的命官,拿着俸禄呢? ”
满都拉清楚他在说自己。没好赖意地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别拿保护草原当挡箭牌。我闹不机密你的意思?实话说了吧,智商没你高,是干不了所长,几天不见有尿啦。给你一根针,真的当成擀面杖了,干脆直接当成金箍棒多好,也把自己当成愿意打谁就打谁的孙大圣。”
巴雅尔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一根筋到底了。反过来逼问满都拉:“不要紧,天底下有说话的地方,我给北京的记着打个电话,过来采访一下我。去年夏天在我包里喝过酒,给了我名片,电话号码我手机里有,让苏木上报纸丢丢丑。”
“少拿大奶子,吓唬小孩。胆子小,所长的位子,就是你巴雅尔的了。”满都拉瞅着两头受气的巴雅尔,抬高嗓门说:“不听劝,一心打我的脸。惹下的祸根,回过头来哭都来不及啊。”
不到上班的时间,额日敦巴日早早来到俄日敦达来的办公室,两人嘀咕了好长时间。额日敦巴日离开办公室直接去了草监所:“该去牧点突击检查了,有些人的羔子蹦得欢。”
满都拉拍着大腿说:“给我气糊涂了。走,快走。”
今天的行动是绝对的保密,统一坐车不能单独走,手机统一放在所里,不能走漏了半点风声。
兵分两路直奔巴雅尔的牧场。
巴雅尔和满都拉摊牌后很害怕,担心他会像以前那样搞突击“检查”。
满都拉和额日敦巴日走后,他想把多撒的一百多只羊赶到阿来夫的牧场,躲开满都拉来草场清点数量,阿来夫打死也不愿意。救命的稻草断了,巴雅尔哆嗦着手,指着草场白花花的一片羔子说:“亲兄弟明算账,一只一天给你6块,嫌少就10块。给你1600,包住草钱了,够吗?”
瞅着摇头不说话的阿来夫,又说:“你也要把我往死路上赶啊。”
阿来夫的脑瓜子摇得像货郎鼓,指着岱钦说:“划算的话,撒你的牧场里。到嘴边的臭肉,你不吃,凭啥放我碗里,我不占这便宜。”
岱钦没想到阿来夫能一口回绝,他把一切的一切全推到阿来夫身上。摇着头拍打着巴雅尔的肩膀,无奈地说:“我和你差不太多,也多撒了八十多只,也愁慌没法消化。你们亲弟奶兄都不搭边,我这几杆子达不到的亲戚,白扯。”
牧场上雪白的小羔羊跟在母羊的后面蹦蹦跳跳,悠闲吃着柔嫩的小草。
轰鸣的车辆声夹杂着刺耳的喇叭声,从四面向中间回拢,分散的羊群顿时乱成一片,慢慢扎起了堆。
这架势这场面从来没有过,要坏大事了,巴雅尔慌了手脚。
草监所的十来号人开始清点羊数。他知道得罪了满都拉和苏木长,没有好果子吃,迟早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他笑嘻嘻地说:“不用点,不用数,超了,超了不到150,明白人眼前,我不说假话。锅里煮着茶,进屋,进屋。”他的胸脯里的两只兔子,扑通扑通一个劲的往喉咙眼里跑。脸上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认为和往常一样,塞给一些钱,走人了事。
这次检查足足提前了二十多天,清点羊数之后,草监所的人没主动提出“过牧”罚款的事。
中午喝酒没有推辞,一杯一杯的下了肚,巴雅尔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他有个习惯喝完酒必“诈金花”。酒过三巡,他开始装醉,喝一口出去吐两口,摇摇晃晃回到座位双手架着头,一言不发双眼叽里咕噜的转着,听着他们喝酒的神态,谁喝多了谁喝醉了他一清二楚。这次他错打了算盘,不用划拳不用唱歌,除了所长其余的人全喝大了。
牌局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巴雅尔门前堆了厚厚的一堆钱。他开始算计再有两个小时,草监所罚的钱,能赢回六成多,里外兑除罚款不到四成。
没等美梦成真,蒙古包的门突然被人拉开,白所长指着桌上的一堆钱,问道:“聚众赌博,人赃俱在,巴雅尔你有啥说的!”巴雅尔笑眯眯拉近乎说:“咱们可是有多年的交情了,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我认错,可错不全在我。人又不是我请来的,是他们自己来的,不是我组织的,不是聚众赌博呀。”
“少废话。你是死也要抓个垫背的,那破德行。他们为啥来的?你不清楚?你倒问起我来了,快收起你惯用的那一套。草监所的人点完数要走人,是你执意留他们喝酒的。你是有动机的,并且是在他们都喝醉的情况下,你提出‘诈金花’的。在这情形下,他们完全没有清醒意识,只是被动的从属。不是你组织的,是谁组织的?你说出来呀!你是主犯,他们是从犯,在量刑上是有区别的。”没有异议,在讯问笔录上按上手印,白所长步步逼问。
巴雅尔接过讯问笔录,看了一遍,战战兢兢刚写完“以上情况属实”几个字,像是掉进大雪坑,浑身哆嗦起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白所长看火候到了,拖着腔儿严肃地说:“不要哭哭啼啼的!还有啥要交代的吗?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在以上情况属实下面,签上名按上红手印。哭能解决问题吗?光凭几滴眼泪就能证明你是冤枉的?几滴眼泪不值钱,看守所和监狱里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白所长翘着二郎腿,大口大口吐着烟,滋滋润润对巴雅尔解释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条是这样说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这几个款项你都占齐了,拘留你十五日,罚款三千一点冤枉不了你。”
巴雅尔被拘留的当天下午,嘎查浩特全传遍了。
有人说他是阻挠矿山选矿厂开工,是呼和巴日下的命令,才抓人的;有人说他拉帮结伙抬高草原补偿价格,犯了法,让派出所抓走了,在拘留所里“蹲号”,不只是挨揍,每顿只给一个馒头一碗菜汤;有人说是在蒙古包里聚众赌博,他赢了一万多,桌面上的钱一小堆,让白所长一锅端了。
阿来夫吓病了,五六天没去草场溜达。
巴雅尔没少鼓动自己跟嘎查和苏木对着头干,把补偿价码向死里喊……真是这样,下一个抓走的人不,就是自己了。越担心越后怕,又回过头来骂自己胡思乱想。
岱钦说是因为赌博被抓进去的,觉得也不对,一起“诈金花”的人,为啥单抓他?闹不机密这些说法哪个是对的,他找额日敦巴日探个虚实,低着头搓着手说:“问你一句实话,他是犯了啥事才被抓的?岱钦说是‘诈金花’,让派出所逮走的。”
他直直瞅着嘎查长的嘴,在等着他说是‘诈金花’让派出所逮走的这句话。
额日敦巴日低头抽着烟,满脸忧愁低声说:“别听岱钦瞎叨叨,蛋球大的事闹不机密?来找刺激是吗?我比你更难受,毕竟是嘎查的人,想啥法子能把人捞出来。”
阿来夫歪着头递上一支烟,说:“对我还保密?球蛋的事,费这大的劲,不就一句话吗?闹不机密才问你嘛。”
额日敦巴日在吊阿来夫的胃口,没有正面回答,扔下烟头转身要走,又转过回头来,装作不耐烦的样子:“不想让人活啦!你有完没完。还不是牧场补偿那点破事,不守规矩和框框,就他知道钱多了,好花。狮子大张口,要一口吃个胖子。补偿那点钱是小事,选矿厂开不了工是大事,敬酒不吃吃罚酒。自作自受,怨不了嘎查,我苦口婆心的费了多少唇舌,死活听不进去一句话,满脑子里装的是钱。一条死路走到底,撞得头破血流,活该!”
第二天一大早,阿来夫搬走了那顶破旧的蒙古包,赶走了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