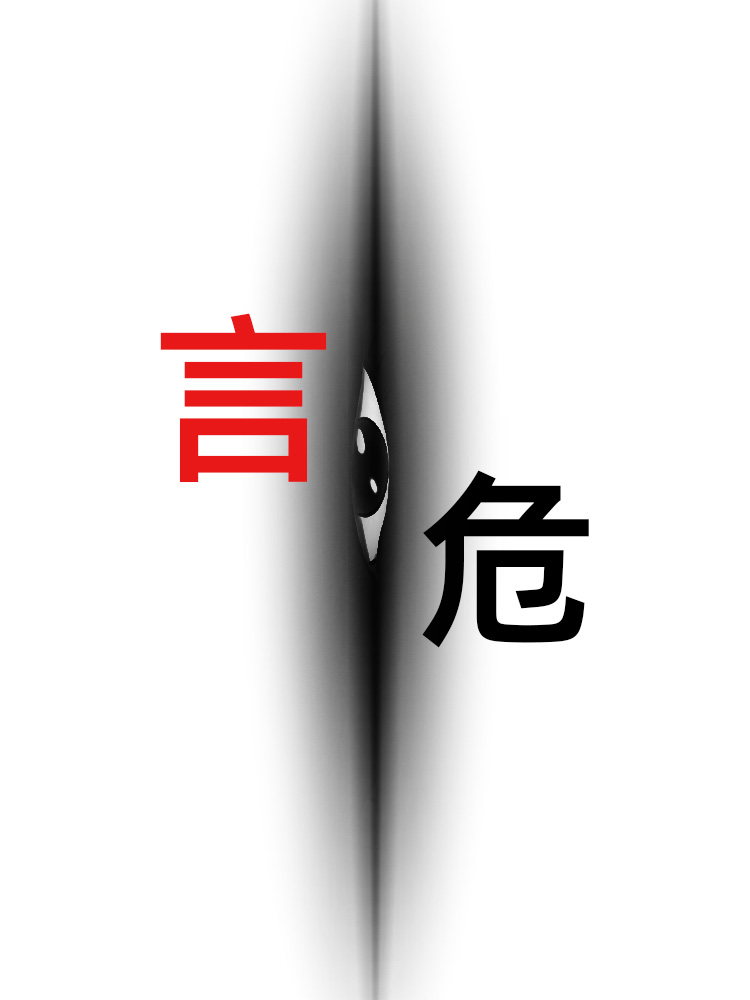郝瑟条件反射地一下弯腰,就差拿手捂住压根不存在的什么什么了。
卧槽,这两货该不会想让她也现场拿出什么飞鸟振翅的证据来吧。
郝瑟脸皮抖了抖,她拿得出来吗?
狠,一个比一个狠。
幸好这古代衣服裤子够宽大,除了振翅欲飞的画面,其他时候,倒也压根看不出有啥不对。
“看什么看,敢怀疑小爷?你们还没醒,小爷我就已经放过水了。”郝瑟匪气横生,也用手指了指某位置。
呵呵,据她所知,早上只要放过水了,就不会飞鸟振翅了。再说,又不是人人都会每日晨间振翅锻炼的。
用手戳了下嘟嘟头顶,怒斥景翊,“我说景翊,堂堂皇子,要点脸啊。”
随后一把将嘟嘟拍回被子里:“嘟嘟那么小,拉足马力也是冲不到帐顶的,别丢人现眼了。”
嘟嘟委委屈屈地低头瞅了瞅自己马力不足的设施,又瞅了瞅他老爹的,很是羡慕。
“我自然是可以的。”景翊很快被转移了注意力,低头看了看,又拿手比划了下,“xxxx技术牛。”
郝瑟表情管理有些崩溃。
大哥,你可以,你完全可以的,我隔着布料都看到了。
你可以去申请当消防员了。
天啊,她突然好怀恋李止。因为只有他,才能把景翊这个无耻社牛的彪悍话语云淡风轻、举重若轻地接下去。
只是那家伙,神出鬼没的,来和走,都不带打招呼。
到现在,她都只知道他来自燕南府城大理,至于身份为何,来盛都干啥,他没说,她也未问。毕竟,人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指望李止空降自然不可能,郝瑟只好硬撑着摇摇欲坠就要碎裂的脸皮,指着嘟嘟,继续转移她扛不住的聚焦点:“肯定是你流口水了。”
儿子,麻溜地,赶紧把锅背了!
“哼,如果不是尿裤子,那该不会是你们俩昨晚哭鼻子了吧。”嘟嘟哼了一声,才不当背锅侠,“有些大人就是,总是喜欢让小孩背锅。”
“切。”景翊不屑。
父锅子背,天经地义。
“哈。”郝瑟不以为然。
养儿子干啥的?就是拿来背锅的。
切完哈完的两人,却微微蹙了眉。
郝瑟突然有些恍惚,等等,她好像有点记忆,她似乎,又做了那些奇怪的梦了。
难道,真不是口水?
不是口水,难道是泪水?可是,她为什么要哭?
莫名地,就想起了篝火晚会时候,和景翊跳舞产生的各种错觉。
郝瑟心里颤了颤,突然有些害怕。
难道她和美人灯,真的有什么纠缠?比如狗血的三生三世纠缠?不不不,那个三生三世的古早梗,早就过时了。
可是,她确定,她在穿越来天辰前,根本未曾见过景翊。又何来纠缠一说。
郝瑟有些崩地胡乱揉了揉头发。
景翊也有些呆,他好像,记起来了,他似乎,又梦见那两个奇怪的男女了。
难道,真是梦里落泪了?
突然地,就想起当初狗子进他对付李汝应的连环阵法时候,他也莫名其妙地心神恍惚落泪。
又想起篝火晚会跳舞时候的各种无法解释的错觉,景翊心里一颤。
那一日,从篝火晚会回去后,他就让夜魂殿重新去查狗子的所有事情了。
可是,诡异的,郝瑟这个人的轨迹很简单,来盛都前,只是偶尔去过燕南几次,其他时间,一直都在老家徽州。
和他真的一点交集都没有,更别说去过西戎了。
再说,梦里是一男一女,可狗子,是男人。也许真是他想多了。
两人正各自愣神的时候,房间门被从外推开了,露出一张拥有两个酒窝的漂亮小脸。
“啊~~~”
秀儿发出一声尖叫,脚下一个趔趄,手里的水盆从头顶摔飞出去,盆里的水凌空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又哗啦啦全都淋在她头顶。
一头湿漉漉的秀儿,呆呆地看着床上的三人,脸上的两个小梨涡都似乎被惊吓到有些冻结,手指哆嗦,“你们,你们……”
郝瑟回神,抚了一下额头。
她想吐血三升好不好,忘记秀儿每天都会给她端洗漱的水进来了。
“那个,秀儿,你听我说,不是你看到的那样。”郝瑟欲哭无泪。
秀儿一副信你个鬼的样子,鬼鬼祟祟地看了眼外面,嘭地一声,跑去把院门上了栓,又跑回来。
景翊也有些风中凌乱。
“公子,看不出来啊,我就说你有时候看起来娘们兮兮的,原来真是断袖啊。”秀儿恍然大悟的样子。
郝瑟崩溃得想撞墙,却囧则生变,一下把嘟嘟从被子里拉了出来:“断袖你个头啊,昨晚嘟嘟来找我,太晚了,回去不安全。”
秀儿更惊悚,圆圆的眼睛瞪得如铜铃:“天啊,孩子都生了。”
秀儿一溜烟跑了出去,地上盆儿也不管了。不行,她得去找夏疯子压压惊。再顺便开发点新的鬼故事。
嗯,比如:王爷他又断袖了。
再比如:神鬼情未了,仙气一吹,一夜生孩。
再比如:……
“娘亲,爹爹,我是你们生的吗?”嘟嘟很应景。
景翊和郝瑟面面相觑,互指对方:“他生的。”
可怜的嘟嘟眨巴着大眼睛,一脸懵逼。
郝瑟一脚踹了过去:“都怪你。”
景翊侧身躲过,提醒她:“该去给更夫收尸了。”
郝瑟这才恨恨地收起拳头,自己跑去厨房里端了两盆水进来,三人各自洗漱。
因为睡觉时候习惯性把头发打散了睡,此刻的郝瑟头发是散开的,洗漱完后,从床头拿上常用的玉簪就要束发。
景翊瞅了瞅玉簪:“上次给你的飘带呢?”
郝瑟动作一停,疑惑道:“什么飘带?”
景翊突然有些支支吾吾。
郝瑟想了想,突然眯眼看着他,声音阴恻恻地:“好呀,我就说嘛!原来是你偷了我的飘带?”
她想起来了,去飞瀑山河滩篝火晚会那日,因为掉下深潭搞丢了玉簪,李止就送了她一条水蓝色飘带绑头发。可是次日醒来,那飘带就不翼而飞了,然后,她头上就莫名其妙出现了一条黑色飘带。
这货究竟什么人,堂堂皇子,居然偷人飘带!
被抓包的景翊,反而不支吾了,大大方方承认:“嗯,白无常东西不要拿,怪吓人的。”
郝瑟真想呸他一脸:“我觉得,黑无常的东西也怪吓人的。”
“不,黑无常貌美如花,你会爱屋及乌的。”景翊将他那蒙蒙生光的脸,往前凑了凑。
郝瑟:“白无常也很好看。”
景翊:“你说我技术好。”
郝瑟闭嘴。
算了,她不和社牛斗嘴。
旁边一直看着两人的嘟嘟,突然又从衣服里使劲掏。
“娘亲,女孩子要带花冠才漂亮。”嘟嘟掏出一个白银精雕的花冠,踮起脚尖,“娘亲,弯腰,我给你戴上。”
郝瑟有些茫然地看着那花冠,机械地弯腰低头,被动地接受了嘟嘟的花冠。
“娘亲,你好漂亮。”嘟嘟夸张地捂住小嘴巴。
看着嘟嘟天真无邪的样子,郝瑟也禁不住微微一笑。唉,嘟嘟真的认为她是女孩子呢。果然,孩子的眼睛永远最亮,永远能看到事物的本质。
对面正捞起毛巾的景翊,呼吸忽然滞了滞。
他的印象里,除了斗花魁那次,其他时候,狗子都是一身利落帅气的少年装束。头发也永远只是用一根白玉簪全部束起,整个人潇洒又飒美。
却从没见过如今这般的“少女”娇俏,姿态明媚。眉目间春光回旋,既妩媚,又清纯。
晨光从半敞的轩窗欢快地照进来,落在她的眉目间,光晕摇曳,却压不过她眉目自带的光辉。
景翊忽然微微别开眼,深呼吸一次,努力平息刚才那一瞬突然加快的心跳。
刚才那一刻,他差点又把狗子当了女子。
这一刻,他有些庆幸,幸好他亲自扒过狗子,确认过是男人,否则现在该陷入反复怀疑狗子是女人的想法里了。
郝瑟没注意景翊的神色,给嘟嘟欣赏满意后,取下花冠,快速用玉簪束起满头长发,对景翊道:“我先去安排下更夫收尸的事,等我回来。”
她记得,景翊说容绥应该清楚吸血鬼的事。
说完,就出了门去衙役们居住的地方找了蒋捕头后,才又折回来接两人。
“走吧,带我去找容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