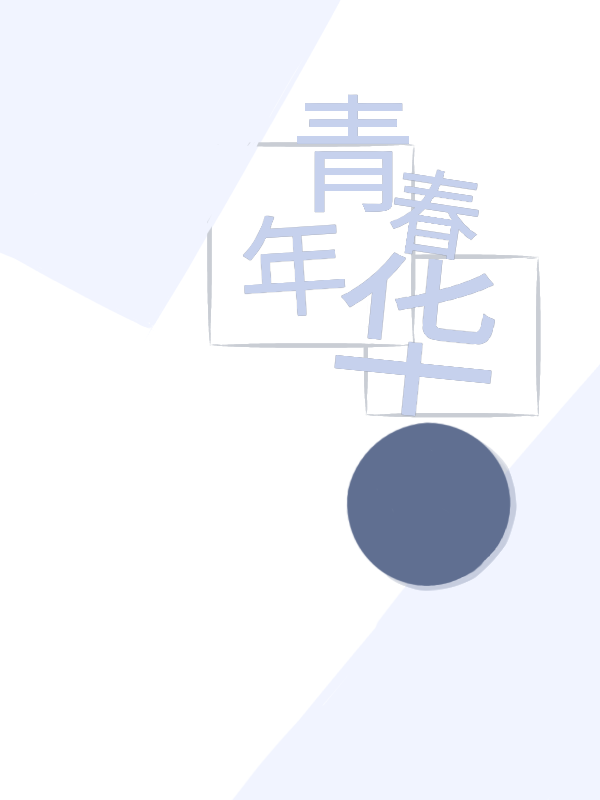庭院积满月色,晚风徐徐,老头坐在竹躺椅上吸了一口旱烟,眯着眼睛,和林慕然说:“小子,明天周五,三天过去了,你去不去上学?”
林慕然拿着铅笔在笔记本上刷刷的笔画着,头都不抬,冷笑地说:“去,怎么不去呢?等下辈子我就去!”
烟气从老头的鼻孔窜出,缭绕四周,使庭院的月色更浓,似仙境,他轻咳了一下,一脸正色地说:“不去我打死你。”
林慕然好像听到了世界上最为好笑的笑话,把笔记本放在龙眼树上,脱掉上衣,在月芒下露出触目惊心的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拳脚印,更有血丝在凝聚或已凝结成痂鞭痕,他扬起嘴巴讥讽地说:“打啊,打死我,我看你林家会不会绝后。”
老头点烟的手顿了顿,把水烟筒靠在竹躺椅上,说:“我这是为你好。”
林慕然撇了撇嘴,不屑地说:“我是你孙子,别人打我你不帮我也算了,还当着大家的面用鞭子抽我?我不要面子的吗?”
老头挠了挠头上仅剩下的几根银丝,拿起水烟筒,佝偻着腰,一声不吭的走进了房屋。
一分钟即逝,狭小的房屋内亮起了黯淡的灯光,淡黄色的光晕透过玻璃窗撒在了庭院上,与乳白色的月芒徐徐融合,在短短五分钟内就吸引了一群嗜光的昆虫环绕在窗户下。
庭院外杂草处响起了蟋蟀的声音,林慕然把竹躺椅搬在龙眼树下,精神恍了恍,一不小心“咔”的一声合上了笔记本,他看着笔记本上的密码愣了愣神,随即把手中的本子和铅笔抱在胸前,魂不守舍的躺在了竹躺椅上。
深蓝色的天空、满盈的月亮、零零散散的星星、晴朗天空过后的夜晚,天上的一切似乎都是静止的,就像是梵高画笔底下的星空一样。
“咳~咳”
屋内传出一阵咳嗽声,林慕然斜眼看了看,然后坐了起来,对着笔记本上的密码就是一顿操作,旋即“咔”的一声,本子开了。他拿起笔目不转睛的望着屋内的灯光,眼球如蜡烛上的火光,汲汲可灭,紧接着就在笔记本上刷刷的写着。
“咳~咳~咳”
屋内的咳嗽声更大了,连绵了十余秒,林慕然眉宇一拧,合上了笔记本,穿上拖鞋大大咧咧的往厨房走去。
刚进厨房,“吱吱”的老鼠声迅速安静了下来,四壁在烟灰夜以继日的熏陶下变得漆黑,灶台下的干柴从七点烧到现在仅剩下了灰烬。
林慕然用抹布擦了擦烧水壶盖上的灰烬,食指在壶盖上停留了几秒,感觉到还有些许余温,他二话不说就提起烧水壶倒了半碗水,小心翼翼的捧进房屋内。
林慕然敲着木门:“老头,要不要喝水?”
老头的言语带有厚重的鼻腔音:“放门外等下我再喝。”
林慕然眼中闪过一丝悔意,把碗放在门前的凳子上,大步离去,留下一阵踏踏的脚步声。
不知何时,天上的夜幕不再敷衍,星罗密布,林慕然的阴霾被星光一扫而空,炯炯有神的目光把整片星空映入眼帘。
以前,
林慕然问老头:“我爸妈去哪了?”
老头说:“他们一直在你的身边。”
林慕然不信:“为什么我看不到他们呢?”
老头说:“要晚上才能看见。”
晚上,
老头带着林慕然来到庭院,指着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说:“他们在那里看着你。”
林慕然虽然不懂老头在说什么,不过他知道他的爸妈肯定就是天上那颗星星了。
对于这点,他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从小到大老头都没骗过他。
林慕然知道他的爸妈变成了天上的星星。
自此以后,
林慕然想爸妈了,
他都会在庭院里睡觉,
他怕找不到自己的爸妈,
所以,
他眼里容下了星辰大海。
—
翌日,破晓划开夜幕,龙眼树上的水珠变得晶莹透彻,似钻石,闪闪发光。绣眼鸟从巢中探出脑袋,举目四望,眼神带着一丝警惕,发现没危险后,它扑扑的落在了树枝上,叶子上的水珠应动而落。
数颗豌豆大的水珠自由落体,打在地上,打在被子上,也打在了林慕然的眼角上,眉毛微颤,慢慢的从耳旁滑落,沾湿了枕头。
老头走了过来,拍了拍林慕然的手臂,说:“还不起床?太阳都晒屁股了。”
睡眼惺忪的林慕然拉扯着被子盖在头上,含含糊糊地说:“几点了?”
老头催促地说:“七点半了。”
林慕然从被子里撑开一个洞口,探出脑袋,不满地说:“才七点半你就叫我起床了?”
老头拉开林慕然的被子,说:“你不用去上学啊?”
林慕然揉了揉眼睛,大声嚷嚷:“不去行不行啊?”
老头冷脸地说:“不去等我老了,你拿什么养我?”
林慕然清醒了过来,一本正经地说:“等你老了,我搬砖养你啊!”
话一落下,厚重的被子砸在了林慕然的脸上,老头大怒:“你到底去不去,不去我就打死你。”
龙眼树上的绣眼鸟被惊走,林慕然怒目圆瞪:“你还真是忘恩负义,我没有爸妈,他们骂我爸妈可以,我忍了,因为从小到大你都叫我别惹事。可这次他们骂你,这我忍不了,我揍了他们一顿,你为了平息他们爸妈的怒火,当着他们的面脱掉我上衣把我揍了一顿,咱家穷,咱赔不起医药费,我理解。可你居然还叫我去上学?还把我往火堆里推?我可是您亲孙子啊!”
老头愣了愣,随后捂着脸,驼着背缓缓的走到了龙眼树下蹲了下来,脸埋在膝盖上,半响后,声音沙哑地说:“就是因为你是我亲孙子,我才叫你去上学,难道你想像我一样那么没用,连找一百块零钱都被人骗吗?”
林慕然见状,眼底闪过几分悲伤,然后一语不发的冲进房屋内拿起书包往外跑了出去。
—
穿过房屋夹裹的小巷,迎来了下坡路,林慕然踌躇了一会,还是走了下去。在其左边是一条车水马龙的沙石大道,摩托车,电瓶车在其中飞快行驶,学生坐在后座上玩闹。大道两旁桉树与大叶榕交错,夹路数百米,道路的尽头就是一望小学。
林慕然凝了凝神,在沙尘弥漫中穿行。
学校附近有数家小卖部,百花齐放,各争其艳,深得小孩的喜爱。走了十余分钟,林慕然来到了学校楼下,他看着学生嘴里的辣条、冰棍,抿了抿嘴,低下头向教室走去。
一望小学只有一栋五层楼的教学楼,周围没有围墙隔离,六年级在三楼最左侧,教师办公室在二楼最右侧。班上的同学已经来的七七八八,林慕然在同学们畏惧的目光下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上。
林老师是一个五十来岁的本地人,是学业有成回来报效母校的知识分子,不过却是思想古板的那种。他作为班主任,在讲台上说完下周考试要注意的事情,然后开始滔滔不绝的讲着课文,言语绘声绘色,激情澎湃,还时不时拿着戒尺敲着桌面。
为了防止挨揍,同学们都正襟危坐,少有交头接耳。虽然上课姿势感人,但认真上课的同学也就屈指可数。对于周围挑衅且畏惧的目光,林慕然露出不屑的笑容,心中暗忖,有爸妈真好,若我也有爸妈,他们安敢这般欺负我?
想到这,林慕然目光不禁黯淡下来,望向窗外。若说这学校还有留恋的东西,那也只能是窗外的爬山虎了。
这爬山虎是新学校建校时的第一任校长种的,是一个比老头还老二十岁的老头,桃李满天下,可惜的是他前年去世了。好在这爬上虎跟他一样那么出息,四季更迭,鸭掌大的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越长越大,连日晒雨淋的楼顶都有了它的生机,为学校荒凉的四周增添了几分绿意。
林慕然愣神片刻,随后回神过来轻轻地摇了摇头,余光无意间瞥向了左边角落的空座位,神色顿了顿,然后向窗外的远方望去,远方是一片金灿灿的田野,隐约有两道黑色的身影在田野间来回移动。
这两道身影林慕然很熟悉,是李田牛和他爸。
李田牛是林慕然在学校唯一交上的朋友,同时两人也是一望村出了名的可怜儿。林慕然年幼时爸妈双亡,与爷爷相依为命。李田牛年幼时妈妈死于车祸,爸爸虽死里逃生,却也落得了跛脚的下场。
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两人在班里就像旮旯角落里的杂草一样被同学随意欺负。后来两人知道双方的身世之后,都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一时的肝胆相照令周围的同学只敢骂几句难以入耳的粗口。
这周二林慕然打架时,李田牛也很讲义气的参与了进来。抱有“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的死志,两人在班里大发神威,以风卷残云之势把班上的同学给打的跪地喊爹。
可惜的是,刚打完架没多久,第二天李田牛他爸就叫他退学了。
在学校书读不成,还整天被人欺负,你读什么书啊,明天捡书包回来跟我去下田,多赚点钱才是王道。
这句话狠狠割碎了少年的心,李田牛心如死灰,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对林慕然说:“以后你要独自一人孤军奋战了。”
林慕然鼻子一酸,喉咙哽咽,不知如何劝慰,只能默视李田牛离去。
自从李田牛退学后,他就一直在家和田野徘徊,似乎田野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
林慕然发呆一会儿,将目光定在更远方,田野之后就是一片波光嶙峋的大海,海岸旁有一片红树林。
望着望着,他的眼睛逐渐眯成了一条缝。
三年前,那个比老头还要老的老头指着前方的那片红树林对他说:“当我看到你时,你在红树林下的半截塑料桶里哭,我还看到在海面上有一条似乎侧翻了的渔船。”
—
放学铃 “叮铃铃”的声音响荡每个教室,同学们一哄而散。教学楼下的家长们早已在等候多时,学生坐在后座上玩闹,沙石大道尘土飞扬,林慕然望了他们一眼,没有理会,在一阵冷嘲热讽中朝家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里,林慕然在院外和院内都转了一圈,果然没有看到老头,他骑着自行车往镇上飞奔而去。
日头微毒,公路两旁种着一望无际的稻谷,无形的热浪吹来,稻穗轻轻的晃动着,像海浪一层接踵一层,携来一阵阵细碎的稻香,吹散了林慕然因在炎热天气下骑车出汗而闷着的一口气。
他继续加速骑行着,用了大半个小时,来到了镇上。
小镇上人来人往,集市街道两旁尽是“人间烟火”,震耳欲聋的吆喝声充斥着整个街道。
林慕然在文具店买了两支铅笔,塞进裤袋,然后吧唧着嘴巴,在琳琅满目的街道小吃上来回穿行。
最终,他在卖棉花糖的小贩前停了下来,含笑着说:“老板,我要两根棉花糖。”,随后把钱递了过去。
小贩接过两张皱褶得不成样子的一块钱,稍稍失神,紧接着微微一笑:“好咧,甜甜的棉花糖准备可以啦。”
谈笑间,机器就“轰轰”的响,小贩拿起了一根竹棍,撒了一把糖在机器上,糖瞬间变成糖丝向上飘,刚好裹住了棍子,越缠越大。
五分钟转瞬而过,小贩拿着两根棉花糖,好意地说:“棉花糖来了,拿稳了,要快点吃哦,别融化了。”
林慕然拿着两根棉花糖屁颠屁颠的往熟悉的地方走去。
街道上人潮涌动,不过他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老头。
今天是“墟日”,别人的摊位都是人满为患,只有老头卖红薯的摊位空荡荡。
林慕然拿着一根棉花糖递了过去,漫不经心的对一脸愁容的老头说:“诺,老头,再苦的生活也要加点糖。”
“你不是说存钱去大城市生活吗,怎么又乱花钱了。”老头斜眼看了他一眼,扣了扣黑不溜秋的脚丫,叹息地说,“这堆红薯如果卖不出去,下学期的学费就交不起了。”
林慕然手里的棉花糖一抖,目瞪口呆地说:“不会吧,咱家穷到这种地步了吗?”
老头说:“你以为呢?”
林慕然满眼期待地说:“那你有什么兄弟姐妹吗?”
老头说:“没有。”
林慕然年龄虽然尚小,但脸蛋却已经有些俊俏的雏形,他迅速把两份棉花糖都吃光,然后摸着自己的脸鬼哭狼嚎:“不会吧?难道我年纪轻轻就要去当小白脸了?”
言罢,林慕然右手摸着额头,眼睛拼命挤出两滴眼泪,一副悲伤欲绝的样子。
老头猛的站起来踹了一脚林慕然的屁股,大喝:“说什么屁话呐!”。
林慕然拍着屁股上的灰尘,不服地说:“是你先说屁话的。”
老头说:“你还说?”
“我这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着想吗?”林慕然吓得连连往后退,等退到自己认为足够安全的距离了,然后壮着胆子,“话说,老头你有多少钱啊?”
老头把拖鞋放在地上,一屁股坐了下去,冷脸地说:“关你屁事!”
林慕然一听,急了,连忙凑近老头的脸,说:“怎么不关我事啊?你好好想想,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我这个亲人了,等你死了钱……哎,哎,老头有话好说,再拧耳朵就断了,我可是你亲孙子啊,亲的。”
老头满脸黑线,大吼:“滚,我没你这个孙子。”
林慕然没有理会吼叫,偷偷扯着老头的衣角,嘀咕说:“老头,你有没有发现这周围有点……不对劲啊?”
“又有什么……”话没有说下去,老头的大嗓音就好像被人掐住了喉咙,嘎然而止。
空荡荡的摊位不知何时变得熙熙攘攘,密密麻麻的吃瓜群众把他们围在中间,“咔嚓咔嚓”的照相声响个不停。
林慕然脑子一片空白,思维短路,慌忙制止,一边摆手一边拉着老头的胳膊,大声喊:“别乱拍啊,别乱拍啊,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呀,我跟他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来的。”
吃瓜群众叫的更欢了,个别照相声伴随着闪光灯“咔嚓咔嚓”的响,其中一个小孩走了出来,天真地问:“哥哥,既然你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你和他叫什么名字啊?”
林慕然下意识地说:“我叫林慕然,他叫~嗯~”,老头迅速捂住他的嘴巴。
霎时间,林慕然反应了过来,望着躲在大人后面一脸得意的小屁孩,心中肝肠寸断:“完了,丢人丢到家了,以后找不到媳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