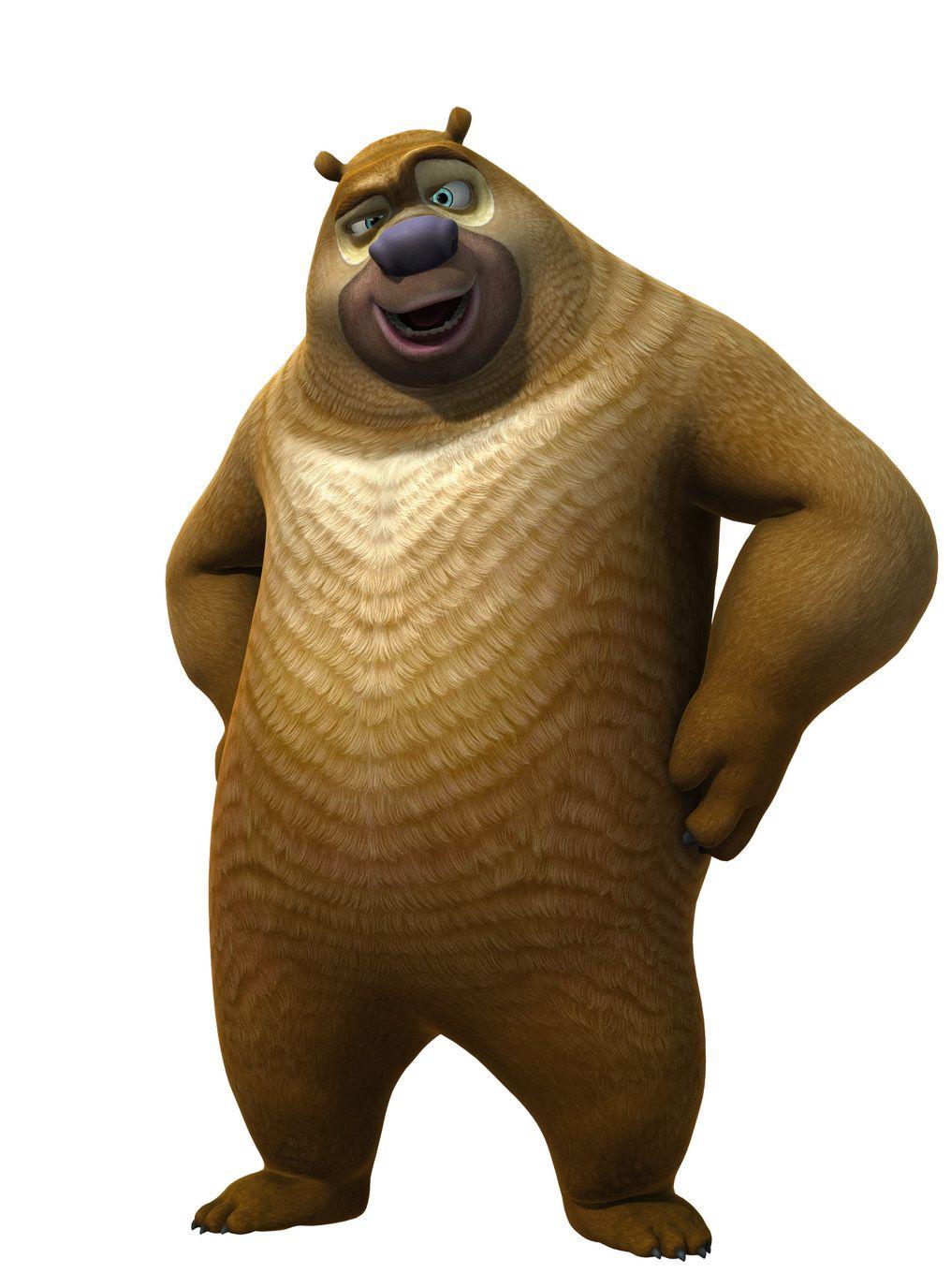姬发处理完公事过来看时,那陶锅内已冒出缕缕青烟,整只鸡贴着陶器底的部分已是一片焦黑,上部分被熏得焦黄。涂涂一看做坏了,自知理亏,转身便要跑。
谁知被姬发一把拽住了衣衫,未能得逃。涂涂像惹了祸的孩童,嘟嘴不言。姬发用双手抚住她的脸,轻声笑语道:“看着我,其实你的菜没有做坏!”
“没有的,你来看。“姬发将表层焦黄的部分扒开,细寻了半天,终于找出一些泛白的肉质来:“你看,这种藏在里面的肉质,才是入味最浓,最为好吃的。”
“真的?我不信,它们都被烤糊了。”
“真的,你不要吃,会死人的!”涂涂看姬发吃了,瞪大眼睛,仿佛吃了这些东西,便能变出一个怪物一般。
“你别再吃了吧,我要你活着陪我!”
涂涂不肯,将那陶锅端了起来:“你别吃,我给你再做一份。”
姬发将眼睛睁大,定定地看着涂涂:“你不觉得烫么?”
“什么?烫?”
“对啊,你的手。”涂涂听了姬发的话,低头一看自己的手,才感觉到有种灼烧感由指尖而来,忙将陶锅置于案几之上,不停地用口气吹手指。
“给我看看。”姬发将涂涂的手移了过去,不知道为什么,一股麻酥酥的感觉自手指尖传来。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碰触到涂涂。
在阴阳石镜中,姬发最初并无身形,后来才渐渐开始有了实体,并未与涂涂有过近接触,这次,是涂涂以人的身形,到人世的第一次。
“这,这便是你说的烫?”涂涂认真地问,见姬发点头,涂涂的脸上绽出笑容,“这次我算是知道了。”
姬发此刻突然觉得,自己居住的地方,就像一个关闭了门窗的古宅,充满了腐竹朽木味,自己长期居住在这里,并不觉得有异样。而涂涂,则是从这个古宅外长进来的一株绿藤,她顶开那些严丝合缝的门窗,到了这里,随她而来的,还有绿草鲜花的气息,还有阳光的味道。
姬发命人为涂涂备好住处,他安顿好涂涂,转身欲走。涂涂问:“你去哪儿?”
姬发顿了顿:“回我房间。”
“你不在这儿?”
“早些睡,有什么事,隔房有人,招呼就好,我明天早上来看你。”
第二天下午,涂涂随姬发到议事大堂门口,姬发派人陪涂涂先在庭内闲步。这时,涂涂突然看到一个人看着自己。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第一次自己闯周王府,那个围困自己的临观。
涂涂走上前去,直问道:“喂,你为什么老看着我?”
临观忙赔罪:“姑娘莫怪,姑娘像我之前所见过的一个人,不过—”
涂涂问道:“不过什么?”
临观慌乱答道:“不过不可能。”其实临观想说的是,不过那个是灵体,而你有肉身,所以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但他同时又心中思量,世间哪有如此相像的人,说话口吻都相近。但这个人现在是周王的座上宾,先不要惊动为好。
按理说,他应该第一时间将这件事报告给吕尚,说自己今天在府中见到了一个人,长得和上次闯入王府的人一样,但他没有。
晚间,涂涂在房间内闻木头的味道,是的,闻木头的味道。
那涂涂一直从桌椅闻到门窗,她住的屋子,房门被涂上了漆汁,晚上时泛着青黑的光泽,木门上面雕了简单的花纹,这些,都是涂涂未曾见到过的。她细细抚摸着,将门一点一点地打开。见眼前两步之遥站着个人,正是白天她遇见的临观。
那临观见涂涂对这儿的门极为好奇,便说道:“那门的颜色,并非本来面目,乃是涂上了漆汁。”
涂涂将身立在了门前:“又是你,你在这里做什么?”
“临观所司职责,查询安危,适才途经姑娘所住,见姑娘摸门索窗,想姑娘有所需,故有所停。”
“我无他事,多谢照应。”涂涂说完,便要退回房内。
“姑娘且慢,临观也对此颇有兴趣,恰巧身边无他人可问,随意向姑娘打听一物,还望姑娘不要推辞。姑娘是否听过‘岷山神草’?”
涂涂心头一惊,心想,坏了,那日一见,这人竟然还记得我的样子,而自己错就错在不该将散魂草遗于此人。怎么会想到此人单凭散魂草,能够知道岷山神草,知道了岷山神草,自己的身份就全然暴露了。说不定会给整个涂山氏族惹来麻烦,他已怀疑到了自己,想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了。
涂涂转身与临观言道:“我亦有听闻。今日已晚,我明天有事外出,前往终南山,你若不嫌远,可在兹泉相见。”
涂涂确实第二天要走,她到此处已三天有余,若再多时日,将会现出本相,唯余灵体。
涂涂临走时,姬发问她对这儿的印象。涂涂道:“你的胡子比前几日长长了一些,不过我喜欢,厨师老爷爷的饭菜吃了能让人精神的,他的话听了能让人睡着的。还有,这儿门漆的味道很是好闻。”
姬发笑道:“这门上的漆,是干了后,又熬制的,算不得好。虢山之上,有数株百年漆树,采来的漆,有淡而悠的酸香之味,到时我让人与你带来,涂于木碗之上,餐食更佳。”
“好坏有什么区别?”
“自然有的,那好的漆蘸起之时细而不断,有琥珀之光泽,转色之后,可得土、棕、血、墨四色。”
“好漆坏漆都是漆的,只要是你送的,我自喜欢,百年老树,已是不易,切莫要人砍伐。”
姬发要人送涂涂上路,涂涂上车前回过头:“有件事我忘记了的。你的手很大,很暖和!”
姬发听了看左右随从,皆掩面窃笑。他不胜尴尬,快步入内。
傍晚,临观到时,见涂涂站在一从水环绕平整之地,显然,在等他到来。
涂涂见了临观,朗声说道:“我与你打一赌。我们比试一番,如若你赢了,我定将岷山神草之事,一一告知与你;若是你输了,从此之后,你不知有岷山神草之事,此前也未曾与我有谋面之缘。”
临观道:“我无意为难姑娘,若是比试,必有损伤,多有不便,有几事不明,想向姑娘请教,望能答复。”
涂涂见那人甚为真诚,便放松戒备:“你且说来。”
“其一,姑娘来周王府上,是偶尔路过还是有意为之?其二,姑娘对大王,是否有亲近之意?其三,姑娘如何获得肉身,在下百思不得其解。”
涂涂道:“我喜欢你们大王是真,其他两个问题,我不想回答。你是否会逼我回答,我也有个问题问你,你如何知道岷山神草的?”
临观面色有些黯然:“我拿姑娘物品曾交与大师吕尚,从大师那儿得知此物为涂山氏族的岷山神草,因其性为雌,故名散灵草,特向姑娘求证。”
涂涂道:“你所知不假。”
“如果临观没猜错,姑娘当为九尾灵狐之后。”临观见涂涂冷眼看他,便言道:“姑娘不愿多说,临观亦不为难姑娘,再无他事,这便告退。”
涂涂没想到临观居然这样好打发。
“临观走前有一事提醒姑娘,此前及今日之事,临观亦不会与他人多言。近日王府之中大师吕尚多有走动,他知晓阴阳之道,有鬼神之法,他已知姑娘为涂山氏族之后。今天后若遇大师,姑娘请自行小心为是。”
涂涂刚要答话,突然觉得阴风阵阵,树叶作响,草向一边偏去,有十余个穿黑衣的人,在一灵将的带领下,将二人包围。
那灵将,便是这些人的首领,灵兵灵将是指没有肉身,只有形影的将兵,他们不是人,而是由鬼魅妖精变化而来。
人死之后,仍能有形影所存者,称为鬼,动物灵兽死后,仍能有形影所存者,称为魅,植物或动物受天地之气滋养,修炼得有了形影的,称作精,人或动物自己修炼得到形影,却未在神仙谱上有名者,称为妖,同样,后世也指未经官方批准,私自行动到达人间的神仙,或是被神仙界除名的,称为妖。
妖和精通常不以自己的原形示人,而是会幻化出其他外形来行走世间,将这种幻化出来的与本体不同的形象,称作怪。
对于鬼和魅来说,他们都是不怕死的,因为他们已经死了,你无法将他们再打死一次,但是他们通常怕魂消魄散,用古语来讲,是“没”,所以很多时候威胁鬼魅,用的词都是“小心我把你打得魂消魄散”。
精最怕的,是找到老“窝”。对于植物成精来说,找到老窝,便找到了他的本体,比如说树精,他幻化成人形,在外面活动,所有的法力和根基,都来源于那棵古树,每隔一段时间,得回去。找到老窝之所在,坏掉这棵树这个本体,很快,他幻化成的一切都将消失;对动物来说,如果是靠天地之气灵滋养修炼起来的,如若找到“老窝”,破坏了那儿的风水,便会失去气灵根基。
妖,最早的妖,是什么都不怕的,除了怕被打死以外。到了后来,更多的妖,其实是私自下凡的神仙或是犯了错被贬的神仙,他们都有自己的上司或师父,所以他们做任何不被允许或违反天条的事,都是幻化成别的形象去做的,所以没有人知道是谁做的,这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空间。
正是因为如此,妖最怕的,便是被“打回原形”,一旦打回原形,大家都可以认出你是谁的下级谁的徒弟,便会直接找你师父或上司反映情况,这样一来,妖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所以,对后世的妖来说,他们最怕的,便是“打回原形”。一旦被“记大过”处分,以后再想转型申请记入神仙谱,便极为不易了,入不了仙籍进不了神仙谱,数百年的修行,在很多妖的心目中,便白费了。
所以妖的最高努力目标,往往是修成正果,所谓的正果,便是位列仙籍,名字进入神仙谱。
那灵将见了涂涂,上前一步点头行过礼:“我等奉族长之命,迎接三姑娘回去!”
涂涂沉脸道:“我还没玩够,过几日便回!”
“三姑娘,”那人加重语气道,“这是老族长的意思,老族长说姑娘在外,已生祸患,要我等务必带姑娘回去,不得迟疑。”
“我若是不回去,你难道能绑我回去?”
“我等不敢冒犯,若为姑娘安全,不得不如此!”
“大胆!”涂涂愤而转身欲走。
那十余人呼啦一下全都围了上来。
临观见状,朗声呵道:“此处为我西岐属国,何人敢在此逞凶?”
那灵将行礼道:“我族素不与人为害,今有族内之事,不得已踏入西岐之地,还望行个方便为好!”
“行方便可以,你且放了那姑娘。”
“我定是要带三姑娘回的,除非你挡得了我。”
临观走近涂涂道:“我且拖住他们,之后你快走,一时半会儿料他们不能奈我何,等你离开后,我自有办法脱身。”
涂涂对临观心生感激,小声说:“他们抓不到我的,多谢相助。”说完,朝着那灵将说道:“劳烦你回去与祖母说一声,涂涂自会小心,请祖母和父亲不要挂念。说完,从腰内摸出一物,手往中间一伸,整个人凭空消失了。”
临观和众人都被吓了一跳,弄不懂涂涂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法器,可以让一个人的肉身凭空消失。
临观回到周王府中,吕尚差人找他,告诉他周公已回岐山,叫他择日顺便告诉周公,有人在岐山城邑看到了他的老师—终南山智者。
这日文真出得山来,却见有邰氏国四处一片狼藉,随处都能看到被火烧过的痕迹,再寻那户人家时,房屋皆坏,院门的挡板只余下一半,空空地倚在那里。
那店主还在。“唉,人老了,走不动了,很多人都去了岐山,我还是在这儿待着,待一天是一天。你也该去岐山换东西了,这儿人少得很。”
文真笑了笑,安静地喝水。
他还是去了岐山,马蹄声声,铃铛作响。这儿曾是15年前的岐山,他心目中的岐山故郡。
是的,他习惯称这儿为岐山故郡或岐山城邑,而今,这里成了都城,偶尔有几个孩子追闹着从他身边跑过,嬉笑声中,这儿仿佛还是以前。然而满街的兵丁,让人备感王城的森严。
他在一客栈吃饭之时,有十余人走了进来,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十多年前的学生姬旦。
姬旦见了他,先解下身上的兵器、佩饰,正了衣襟向前一步道:“先生好,弟子有事外出,刚回来听闻有了先生的音信,特地立时赶来,迎接先生回府。”
文真见了姬旦,也自是欢喜,与姬旦言道:“你且叫他们回去吧,你与我一起吃罢再回,省得你我吃饭,却还要劳烦他人站着,好叫人不能心安。”
姬旦只得照做,只留下两名贴身护卫,站于门外,文真起身,邀二人进屋,二人面露难色。直到姬旦说,你们也进来一起坐着吃罢,方才缓坐下来,身子却直直地挺在那里。
文真一到王府,便有人传过话来,大王晚上设宴款待文真。文真言说此事不必铺张,后姬旦说来人不多,仅有姬发、姬旦、吕尚、姬奭、姬度、虞仲、伯廖。
文真往席位之上一坐,一股莫名的悲伤感突上心头,竟不知从何而来。
当时姬发座位中,坐北朝南,文真在右手第一位,姬发在左手第一位,文真旁边是姬旦,姬发旁边是吕尚,正好迎面而座,其他人依次排开。
这天文真一直话很少,宫女们来来往往给众人倒酒,文真喝得有些慢,停停喝喝。
姬发今天心情大好,频频劝众人酒,却唯独对文真心存几分敬畏之意,任他缓喝慢饮。
那姬旦知晓文真不喜铜器玉器,便替他专门备了木碗饮酒,然那木碗中的酒冷得更快些,一见酒偏冷,文真自是降缓了速度。
“我替你换杯温的吧!”文真回头正欲道谢,那女子并未看他,低垂着眉眼,用心将木碗内的酒倒进冷酒壶内,将碗放回案几之上,准备替他倒上新温的酒。
文真见她眉宇间有一丝淡淡的愁意,知有挂念之事,便轻声言道:“不愁的!”
那女子听了,轻抿一下嘴唇,将头倾向一边,款款地将酒倒向他的碗内,倒到最后时,她缓缓地将手向上一移,脸上泛起一丝笑意。
文真心生好奇,不知她因何变得这般开心,便移目去看,正巧那女子也在看自己。
那女子面似玉盘,洁净透亮,眉目间犹如藏着潭水清波,宛转流动,长长睫毛闭合间犹如蝴蝶飞舞。
文真突然心底有一丝的隐隐作痛,不知因何。她不是别人,正是有邰氏国,院内有桃花的女子。
那女子见文真看她,微微低头,眼帘垂得更低,猛然间不知想起了什么,她让自己脸侧向一边,朝着文真,嫣然一笑。
或许那一刻,她想起了文真第一次见她时,竟然慌张地说:“我,我路过。”他比自己还要笨拙还要胆小,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或许那一刻,她想起这个隔三岔五来古镇上换日用杂货的男子,又怎么会是终南山上的智者,世间竟有这般出人意料的事。
或许那一刻,她在想为什么眼前这个人要用木碗来喝酒,喝起酒来还是那么笨笨的样子。
或许那一刻,她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她不知道文真是为寻她而来,不知道文真最后的宿命,与她有关,不知道这个男子已经毫无缘由地爱上了自己。
一世逃亡
宣纸洮砚
浓墨狼毫
定是可以描绘出我们 相遇的绚烂
你的容颜
惊落我笔尖 一世的婉转
印迹斑斓
那庭前的冷雨
斑驳了画卷
无人落款
那满卷的长诗
酝酿了光影
怎分浓淡
繁花哪堪一季
落英乱如雪
拂了一身还满
我一世逃亡
又怎能敌
宿命 张望几番
料得他年相见时
顾首欲语 忽念已非终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