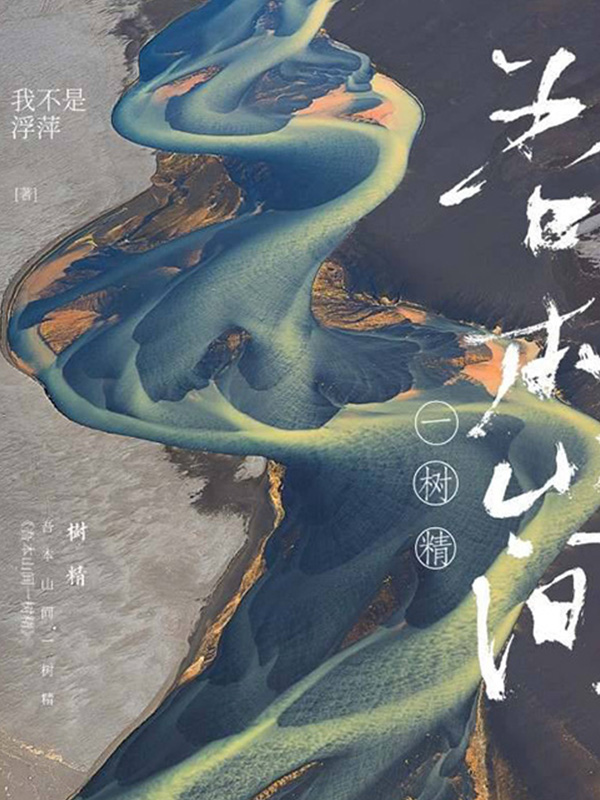富国走出房门离开征北军很顺利,除了必要的交接,几乎没有任何阻碍,还顺带领了一声新衣服,都是军制的,能耐磨,能防水,还透气,这可不是奴隶营几块破布能比的,只是乱糟糟的头发使得富贵看起来仍然像一个难民。
想必左青也想的是富贵快些离开,省的惹人口舌,但是富贵临走之时也没备一匹马,这让富贵在心里不止一次诋毁左青“抠门”,至于必要的水壶,干粮倒是随富贵拿了个够。
崭新军制牛皮毡鞋踏出凉城的一刻,富贵不由的回头望了望,不高城墙上,还是阵阵黄沙,已经高扬的大秦标志性麒麟旗帜屹立风中不倒,一瞬间所有记忆一幕幕涌上心头。
富贵想起了大壮拿着半块馒头挑逗已经快被饿死自己,还有第一次上阵冲锋握着木棍都颤抖双手,直到后来自己偷偷藏了块石头打掉大壮半颗大牙,但自己也断了几根骨头,才没被人欺负,抢掉所有吃食。
自从打过之后,富贵主动给大壮献上吃食,恳求大壮教其武功,慢慢的和大壮越来越熟络后,两人一起密谋干掉当时的奴隶营长,大壮偷偷下药,富贵则负责晚上摸到床头抹脖子,这事之后,奴隶营也就尽归大壮之手。
再随着后来年纪稍大,略有武技之后,随着其他奴隶的上供,倒也不缺吃食,慢慢制定一系列的攻城保命策略。
直到近些年,富贵和大壮已经在慢慢尝试杀敌,积累军功...借此来脱离奴籍,只是军中对于奴隶营的要求太过苛刻,需百人斩,方可脱奴籍,能脱奴籍者,在军中数年也只是寥寥几人,但无一不是能修行之人,像大壮,富贵这样的凡人之姿,若想脱离奴籍更是难于登天。
加之军中恶习,历来喜以奴隶笼斗来博个彩头,虽然监军已有警告,但是每次屠城之后也成了平常士兵茶余饭后的一项“娱乐”活动,成为军中一种解压方式,左青是知道的,只是每每屠城之后,普通士兵的宣泄方式各有不同,常年战争的压力,也需要得到释放,也就被默许了下来,加上底层几个百夫长可以从中牟利,也就促使成了奴隶营笼斗的形成,甚至是一种“特色”,这也是奴隶营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富贵和大壮也无可赖何。
初始大壮也被点名笼斗过,只是由于大壮身体素质实在过于强悍,以至于普通奴隶往往在其手中撑不过几回合,使得百夫长博彩的赔率太低,就再没被点名上场过,而富贵出入时则是孩童之身,并未有战力,直到近些年才被点名过一次,只是在笼斗之前富贵便和对面奴隶商议好,没过几个回合,富贵假装不敌进笼装死,后来以富贵太过瘦弱为由,百夫长还更改了赔率,这惹的很多士兵不满意,至此之后便再也没参与过这项运动。
但是富贵好勇斗狠的战技则受笼斗影响不少,本来大壮大开大合的刀法,也被富贵运用的极其猥琐,不出刀则以,出刀则必置之死地而后生,示敌以弱,攻敌以破。
一想到这些富贵就摇了摇头,只是还是有些忘不了...陪他一路走过来的大壮而已,随即整理好背带,头也不会的踏步离去,脸上的泪痕也被风干。
随着富贵大步流星的走远,即将消失在茫茫黄沙之中...
站在城头的左青亲卫营营长也将手中的弓弦拉的越来越满,单眼瞄准富贵即将远走的身影,只是箭将离弦之际,一只宽阔的大手闹闹握住即将离弦之箭。
大壮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城头,目送风沙中远走的富贵,看着即将被射杀的富贵,大壮伸手握住了箭矢,对着矮自己一头的新营长摇了摇头,说道:“长官,别...你若放箭,我便告诉将军。”
大壮本来就有武术底子,加之富贵的龟息法加持,修行军中八法数日,就已经摸到了修行门槛“感气”,牢牢的握住了箭矢。
左青的亲卫营长当即收弓,一拳将大壮打翻在地,狠狠地说道:“才初入感气境,就敢威胁我秀三郎?还知道我是你上司吗?”
而大壮顿了几秒,眼看富贵消失在黄沙之中才捂着被打肿的脸接话道:“小的不敢!”
秀三郎看着消失的富贵,再也寻找不到射杀机会,恶狠狠地瞪着大壮说道:“小子,接下来有你好受的。”
大壮则皮笑肉不笑的赔笑到:“大人您大人有大量,放心,我兄弟跟我一样嘴很紧的,绝不会坏了大人您的名声。”
大壮从入营被打得时候,就看出这营长不是善茬,只是奈何军营之中不便动手,果不其然秀三郎怕富贵走漏风声坏了其名声,传其抢军功的恶名,在富贵出城之际埋杀富贵。
秀三郎正在气头上,看到大壮一副奸计得逞的模样,一脚又踹到大壮脸上,踢的大壮鼻血直流,默然走下城墙,只是幽幽飘来一句:“城中我不杀你,但是以后有你好受的,你给我小心点!!!”
军有军规,大壮知道自己脱了奴籍,已然是正规军制,秀三郎不敢在营中对自己下杀手,哪怕是左青的亲卫营长,也不敢在军纪方面触左青的霉头,残杀同僚可受车裂之行,秀三郎最多揍自己一顿。
看着走下城墙的秀三郎,大壮抹了抹鼻血,一改憨厚模样,眼底厉色渐起...只是转身望向富贵消失的地方之时,眼中却充满了温柔,干裂的嘴唇轻启:“兄弟...好走!!!”
富贵看了看地图,朝着禹州方向走去,一路向南而行,沿着凉城官道一刻不停.
只是走了半天,也看不见个头,以前行军之时,富贵就练出一副好腿力,只是架不住路途实在太过遥远,看样子徒步而行得到剑宗的计划可能会提前破灭。
富贵都是走的官道,富贵不得已路上搭乘几次商队车马,花了些银两,甚是肉疼,却也规避了不少的风险,兵荒马乱的年代,到处都不容易,流寇,土匪更是数不胜数,一路上大批大批的难民向南而移,只求到中原讨个生计,富贵还好一身军中制服,虽然怀中还有些银两,但也没什么流民敢上前来找其麻烦,甚至讨要吃食的都少,只是商队却苦不堪言,若不是雇佣的镖师足够多,怕是一路上的货物早就被哄抢而空。
不过三天两夜的功夫,就到了禹州,富贵犹记得当初破了禹州之时,曾屠城三日而不休,但是再次来到禹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墙体防御等大型工事已经开启修缮,城外被马蹄践踏过的谷物,也露出点点金黄,只是城头旗帜却是换了一副模样。
看着迎风飘扬的麒麟旗,那是大秦的标志,办理完入城手续之后,富贵来到禹州城中,没有想象中的萧条与混乱,跟富贵印象中那时屠城的模样依然不可同日而语,只是来往行人的确寥寥,显的有些冷清,一些流窜进来的流民难民,还是能随处可见,富贵踏步而行,正要去寻一处落脚处的时候,突然前面敲锣打鼓,偌大几辆马车在人群的簇拥之中缓缓的向着城中广场走去。
伴随这敲锣打鼓声人群本来要死不活的难民流民,一下来了精神,向马车奔涌而去,挤的富贵大了几个踉跄,富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几人推开,对着富贵说道:“死要饭的,别当道...李大善人施粥步善,晚了大爷可就分不到了。”
富贵别推搡倒一旁,倒也不懊恼,只是自己讪讪的衣襟,顿时一阵尘土飞扬,不由的摇了摇了脑袋,心想到:“你们才是要饭的,全家都是要饭的...”心里暗暗呸了一声。
随后又自然而然的摸了摸怀中的巨款,还有十余两,看着奔向施粥铺的流民,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对着刚才撞飞他的那几人,吐了一口水,说道:“夏虫不可以语冰,去粥铺求施舍,小爷看着像这种人吗?”,整理完因为赶路已经破烂不堪的衣服,富贵的肚子也“咕噜噜“的叫了起来,看起和流民没什么两样的富贵眼睛向旁边的一家酒肆,这家酒肆看上去并不怎么气派,只有一个小小的招牌,歪歪的写着“同福酒家”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