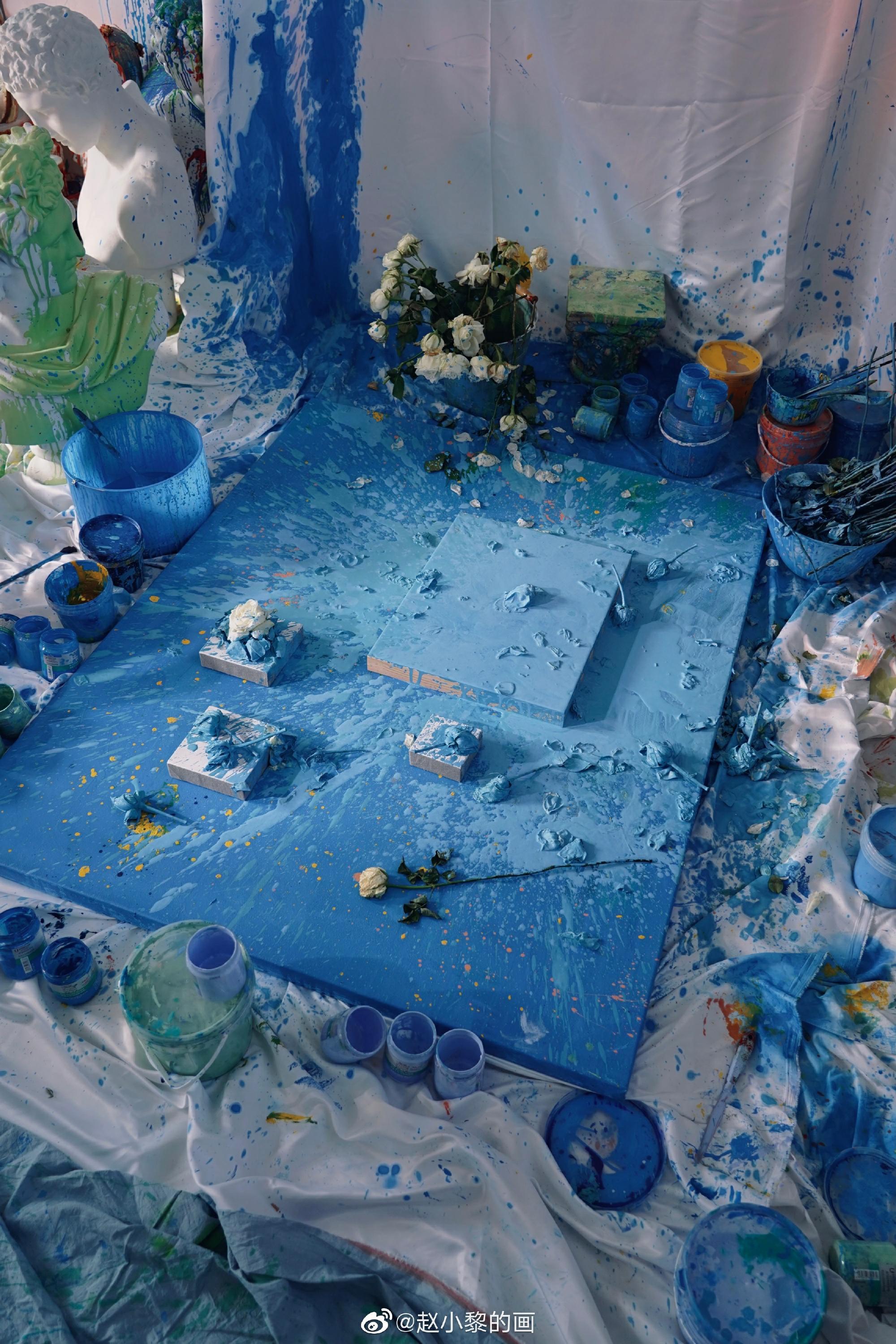第二天早上,秦娴按时同负责黄昆吾案件的警官碰面。昨晚电话里说,会面地点是办公大院里一座翻修没多久的新楼。
密陀市是个没火车站的小地方,只有这栋大楼外观气派,虽然不高,风格略显陈旧,但透着一股子雄霸气势。这楼年年翻新,是小地方最醒目的建筑。有人说,楼是一位大设计师没出名时的作品,现在人家发达了,年年出钱翻新,留个念想。也有人说,楼是港商台商捐赠的,内中有什么弯弯绕绕,外人可说不清。
说法很多,无凭无据没个准。反正少有人关心楼的来历,因为不愿意扯上关系:那地方从有密陀老城,就是老衙门,至今还是衙门口。
秦娴在胸前挂好证件,进新楼的东侧门。
一直往西走,下四级台阶,刷门卡,转个弯再下十级台阶,再刷一次门卡,往前两步,就是防卫严密却乏人问津的冷衙门。
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档案库,占地颇有些规模,装修却懒于费心思。走廊两边的门,无论样式还是材质都带着各自的时间特征,没有统一换过。走廊最前端两扇门是当下流行的保险门,继续往后看就奇怪了:七七八八的门透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七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气息。第一次来时,秦娴怀疑不小心开错门,就回到解放前,不由得感慨:“想不到下面这么大呀。”
负责人指着黑魆魆的走廊深处,说:“都是原始卷宗,要紧东西。好些案子还没解决,可不能丢。”
提起“好些案子还没解决”,他的口气既无奈又悲凉。秦娴以专业的眼光看得出来,他因为某些缘故,对“悬而未决的案件”耿耿于怀。秦娴有自信判断:他自己也曾遇见过至今尚未能昭雪的冤情,不是发生在他身上,是发生在他的家人身上。
就算挂上了证件,秦娴也不敢乱走。在摄像头的注视下,她总是在右首第一间办公室外敲门,目光躲躲闪闪地眺望安静的走廊尽头,但从来没有试图去窥探。
今天她看着走廊深处的昏暗,忽然想:密陀市这么小的地方,竟会有这么多卷宗要管理,真是不可思议。按说现在都办公电子化,他们竟还锁着整屋子的老物件,不舍得放去档案馆纪念馆之类的地方。秦娴想着,又觉得,似乎从来没有听说本市有档案馆和纪念馆。
在这里度过整个少女时期,年近五旬,她才发现对自己长大的地方不怎么了解。
那么……这走廊里,封锁的就是密陀市的历史?秦娴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莫名其妙地打个激灵。
办公室里有人爽快地大声说“请进”,秦娴匆匆推门走进去,躲闪走廊里的阴凉气息。
胖警官像弥勒佛一样体态宽大,连“弥摩”这名字,也像含有某种奥义。不过他的谈吐却完全找不出超凡脱俗之处,是人海中再普通不过的临退休大叔。
“你说他知道你的资料,是什么情况?”乐弥摩客气的微笑中带有迫切地语气。
秦娴眼皮一沉,不知道如何讲起。说二十六岁的黄昆吾,知道三十年前一个女生的初恋?太荒诞了。她的嘴唇微微地开启,换了一种方式提起这情况。
“乐警官,你有没有,在黄昆吾的故事当中,遇到过似曾相识的情节?”秦娴谨慎地试探乐弥摩的反馈,但他的神情充满茫然。“有没有感觉,某些故事的情节,好像与自己的经历有交集?”
乐弥摩仔细想了想,摇头。秦娴顿感泄气,心想果然是自己太无聊了。
“最近有什么进展?”弥摩苦笑,“他还是在叨念‘豆芽巷’?”
“没错。”秦娴拿出档案袋。最初她准备的是一个20P的插袋文件夹,现在已经换成了能找到的最结实的档案袋。之前用一个不太结实的,被打印出来的故事撑破。
“又一个新故事。”秦娴无可奈何地说,“他可以写出一本新天方夜谭了。”
弥摩快速浏览打印好的文字,眉头紧锁,目光却像狐狸一样精明。他看完之后,熟练地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图表。图上画着一枚巨大的豆芽,豆瓣用一圈数字镶边,从入口处逆时针排列。
“一号,来生坊。”胖警官在数字1旁边标注“来生坊”三个字。
1号来生坊,收售香料香水。3号奉慈书房,主营文房四宝。4号浣月坞,种子店。5号瑞英馆,买卖字画。7号羽宫,音乐用品。8号菱花苑,工艺剪纸。9号流彩庭,玻璃制品。10号藏缘楼,代制标本。11号润霞庄,专营糖果。14号镜屋,卖木偶皮影布娃娃。15号饕斋,糕点屋。19号太岁轩,花圈寿衣店。22号百草庵,药店。26号嘀哒之家,钟表店。31号香轻堂,花店。还有在广场中央,没有门牌号码的城隍庙。
“现在有15家店铺的名字。他从来没有重复命名,也没有搞错门牌号码和主营业务。”秦娴双臂抱胸,愁眉暗结。“连几十个店主的名字,也从未弄混淆。他对那地方了如指掌,简直像一辈子都在那里生活。”
“他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是一栋建于上个世纪的单元楼,只有4层,连黄家一共16户。前几年拆了。”弥摩开始习惯性地挠头,“他说过很怀念那地方,梦到回家时,总是回到那里。你觉得这些店铺,跟他原来的家有关系吗?”
秦娴早就想过这种可能。听了来生坊的故事之后,她按捺不住,去黄家老楼的所在地走访。楼已经变成三十多层的大厦,住户大多不是老居民。秦娴可以确定,安毅的生活跟这里没有交集,没有亲戚朋友住在附近,甚至没有要好的同学曾经跟这里发生瓜葛。也就是说,这里没有人会知道三十年前,有个十八岁的少年送给十八岁的少女一瓶香水这么小的事情。
秦娴对弥摩摇头。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乐弥摩问:“秦医生,昆吾的病还有治吗?”
秦娴从他口中听到浓厚的怀疑。他本来就不太相信心理学,觉得心理医生跟算命的差不多,唯一的差别是算命的捧着《周易》分析人的一辈子,心理学捧着弗洛伊德和荣格。他看得起秦娴,因为她是个留过洋、治精神病的专家,会治病是件实实在在的本事。
秦娴无法对外行解释太多,而且这里面还有个奇怪的缘故:她从未弄清楚,黄昆吾究竟摊上什么事。
她只被告知,黄昆吾掌握了一点不为人知的新线索,在追查一桩陈年旧案。是什么案子、什么线索,只有他知道。可他自己也摊上了案子,有个女人跟他在一起失踪。
黄昆吾出现的时候,那女人没出现。而他发了疯。
至于那女人是谁,“上面”反复叮嘱:暂时不能公开。有必要让你知道的时候,会告诉你。黄昆吾的事情要严格遵守保密原则,不要让外界知道办案警官精神崩溃。
秦娴看过不少病人,唯独这回,从头到尾遮遮掩掩。到头来,却拿重重压力来压她,嫌她提交的方案收效甚微。
黄昆吾的病还有治吗?
秦娴微微地绷起嘴,挤出简短的套话:“又给他开了药。”说完去拿档案袋。
弥摩按住纸袋,说:“留下我看看。”
档案袋本来就是拿给他,秦娴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如此糊涂,又像舍不得似的要带回去。她暗自诧异,投身这案件之后,她好像时常恍惚,变得粗心大意。“对了,有两份记录,是黄昆吾前天口述,我昨天晚上整理好的,你还没看过。”
她拿出两份订好的纸本,静静地放在弥摩面前。不……不是粗心大意,而是不情愿。不情愿让别人看到那些故事。
难道她竟在无意中把来生坊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怕别人看到自己的初恋?秦娴不由得打个哆嗦。
“月桥社,一醉庵。”胖警官戴上眼镜,神情变得认真。
“2号和12号。”秦娴说,“一家卖灯具,一家卖酒。”
弥摩拿起笔,好好地把它们标在图纸上,颔首示意秦娴可以先走。秦娴刚转身,弥摩突然想起什么,叫道:“秦医生,有件事情,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跟你说清楚。”
“乐警官请讲。”
“黄昆吾警官,并不是犯罪嫌疑人。”弥摩双手放在宽厚的胸脯上,吐了口气,“他只是最后一个见到失踪者的人,从此之后精神错乱。给他戴手铐,是他还没完全疯掉的时候,自己要求的。他说他担心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希望你不要对他产生误解。”
秦娴放下脸,沉声道:“我只当他是我的病人。”说罢昂然离开。
弥摩冲了一杯浓咖啡,又坐回办公桌后。对面的桌子上,还放着昆吾的玻璃杯。昆吾总是在下班前把杯子洗得铮亮,只有那天走得匆忙,杯里还留着整杯茶水。弥摩一直没给他倒掉,时至今日,蒸发剩下的茶都干透,杯身留下一圈圈烟黄色的茶渍。
现在竟然只能从纸上见见昆吾了。
弥摩叹息,开始浏览昆吾讲述的故事。
有没有在黄昆吾的故事当中,遇到过似曾相识的情节?有没有感觉,某些故事的情节,好像与自己的经历有交集?
乐弥摩无法忽略秦娴刚才的问题。坦白说,他对这位半神婆半医生的专家不怎么信任。
想要找出昆吾的心结,他更愿意靠自己。
唯有一点,他和秦娴是一致的:他也感觉,一切的关键都在故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