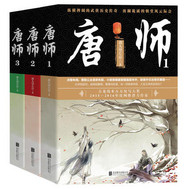秋意渐浓。
凉凉的秋风荡起,晃动着高大雄壮的雪枫树枝,一片晶莹洁白的掌形叶片趁机飘落,打着旋儿,坠落在“灵枫镇”的牌匾上。
站在牌匾顶上打盹的乌鸦被落叶惊动,扑棱着翅膀飞起,脚下,一幢幢错落有致的木屋往后倒退,一棵棵粗实的雪枫树也在向后移动。
飞过了民宅,飞过了街道,最终,乌鸦停落在一幢最高的木楼顶,四处张望。
这幢木楼共十二层,建立在两棵百年老树的中央,由老树粗壮的树干,支撑着它屹立不倒。
木楼的第一层进门处,一副斑驳了字迹的对联呈现在眼前。左联是:当官须为民作主。右联是:执政当为民谋福。横批:国泰民安。
“嘎吱”一声,一个身穿粗布衣裳的妇人右手推开木门,左手挎着菜篮子走了进去。
妇人大概四十五六岁,长相普通,穿着朴素,挎在左手上的菜篮子里,摆放着三种便宜的素菜。
“噔!噔!噔……”空旷的木楼里,行走的脚步声格外清晰,声音一层一层的往上传递。
到了第十二层,妇人推开木门。
屋内,一个身穿补丁衣服,长发凌乱的中年男人正坐在桌案前发呆。桌案上,整齐摆放着一堆纸质文书,身旁则是一盆即将燃烧完的炭火盆。
“唉!”妇人看了男子一眼,目光中的失望难以掩藏,叹了一口气,将菜篮放到桌上。
她深吸了一口气后,一脸郑重的对男人说道:“宋江河,我们和离吧!”
中年男子看了看妻子,有些诧异,又有些意料之中。但还是开口问道:“能告诉我原因吗?”
妇人坐到木凳上,悠悠道:“你觉得,我们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宋江河想到了很多,但却沉默不语。
他妻子继续说道:“本来,这话我十二年前就想跟你说的,但那个时候你刚任职镇长,加上清欢也还很小,我便说服自己,‘镇长这样大的官,以后一家人的生活都能有盼头’。可是,这十二年的时间里,我攒够了失望。起初,一家人住在这幢别人不要的鬼楼里,我还能说服自己,可后来呢,你可曾为这个家考虑过?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前进,反而越过越差。你不是经常跟清欢说,让她多跟其他小伙伴交朋友,增进友谊吗?那你知不知道,她穿着旧衣裳,吃着从家里带去的粗粮,与那些家境优越的伙伴在一起,到底有多自卑?
多年来的委屈,化成说不完的心酸,两行清泪流下了妇人的眼眶。
宋江河苦涩的张了张嘴,不知如何安慰,不知说些什么,最终,也只有沉默以对。
“你是做了镇长,在外人眼里,是个了不起的大官,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你的俸禄,几乎都补贴在整个镇子上了,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再看看别人做官的,那怕只是一个镇护卫队的队长,谁过得没你好?与其跟你一条道走到黑,不如早点分开。我们还是和离吧!”
“唉!”宋江河叹了一口气,面带愧色道:“这些年,苦了你们娘俩了!和离了以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去我哥的布坊帮忙也好,去别人家找点事做也行,反正,肯定比现在强。”
“好!”宋江河点点头,“给我两天时间,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眼见妻子起身,宋江河叫住了她:“再给我做顿饭吧,以后要想吃……可就吃不到了。”
她起身,站了站,随后便开始择菜,洗菜,切菜,做菜,如行云流水,十分娴熟;他呆呆看着她,十多年来,第一次发现,怎么也看不够。
这顿饭,两个人沉默的吃着,有意无意的,都吃得很慢。直到桌上的菜被吃得一点不剩,才放下碗筷。
“婉儿!”宋江河叫道,但又似乎觉得这亲昵的称呼,不好再叫,勉强笑了笑道:“秦慧婉!能不能最后让我再抱抱你?”
两人相拥,就此分别。
她离开了,顺手将门带上,屋内变得灰暗。宋江河呆呆的坐着,炭火盆内的炭火已经熄灭了。
“唉!我这一生,其实挺失败的,镇长没有做好 ,生活过得乱七八糟,现如今……这个家也散了!”宋江河哽咽。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边。外面,秋风萧瑟,雪枫叶落满地。
“李秀才,是我宋江河无能,尽了力也没能保护好你们,是我无能啊;铁衣,你回来吧,我不逼你当镇长了,你想修仙就去修吧,不逼你了;清欢,以后就看不到你的笑脸了,你要好好的生活,将来,可不要找像你父亲这样失败的男人;婉儿,和离书我就不写了,免得以后你的名声不好,丧偶吧,丧偶好听些……”
……
木楼下的雪枫树底,宋江河的妻子秦慧婉靠着大树,神色哀伤,不时转头看向木楼的入口处,她已经在此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日夫妻百日恩,感情的事,那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咚!”
一道影子从她边上坠下,重重砸在地上,巨大的声响吓得她心惊肉跳,转过头,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躺在地上,鲜红的血液正慢慢向四周扩散。
“不!不不……”
她双腿发软,使不上力,就连站稳都成了问题。踉踉跄跄走过去,看清地上熟悉的身影正是宋江河时,她只感觉到天旋地转,随后,便失去了知觉,整个人软绵绵的倒下。
这里的巨响,惊动了周边的人们,有人急冲冲跑来,随后大呼:“宋镇长坠楼了!”
木楼下,陆续有人赶来,就连镇上的大夫也匆匆来了。最终,昏迷过去的秦慧婉被人送上楼去休息,而大夫握着宋江河的手腕,无奈的摇了摇头。
一个凡人,从十二层的木楼坠下,纵然有医术超凡的大夫,也无力回天了。
天空中,不知何时起,飘起了绵绵的雪花,带着冬天的哀愁,缓缓落下。
秋天已经过去,冬天到了!
木楼上,乌鸦上窜下跳的怪叫了十几声,随后飞走了。木楼下,百姓自愿的来到,围在宋江河尸体的四周,默默低头站在雪中,久久不愿离去。几个年长者,曾经受过宋江河的大恩惠,眼见恩人逝去,更是湿润了眼眶。
……
小镇中央,建筑奢华的员外府内,身穿金丝绵衣的王少城展开下人送来的书信,深邃的眼睛不停转动,嘴里自语:“宋江河死了!嘶!死了?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一边自语,一边移动着略胖的身体,在屋内走来走去的,随后,又停住脚步,叹了一声:“也罢,死了也就死了,只是这盘棋又得变动,麻烦!”
……
小镇镇西的叶兴家,是两层一般建筑的木楼。大儿子叶顺匆匆推开木门,双眼看向叶兴,道:“刚刚,宋镇长坠楼身亡了!”
“不可能!”叶兴放下烟袋,“那里听来的?别胡说八道。”
他的妻子陈凝放下了手中的活,问:“是那个烂嘴巴的传出的谣言?”
就连只有六七岁的小妹叶真真,也挥舞着小拳头,叫嚷着:“说宋伯伯坏话的都是坏蛋!”
但看叶顺脸色严肃,不像是在开玩笑,叶兴脸上没了光彩,叹了一口气,道:“你把惊鸿叫回来吧,我总觉得以后的日子估计不太安稳。宋镇长对我们家有大恩,我们要晓得。”
“已经给惊鸿写信送去了。”
叶兴点点头,站起身来,道:“我们先到宋镇长家去,看看有什么帮得上忙的。”
叶真真悄悄窜到叶顺身边,扯了扯叶顺的大袖,小脸希冀,小声问道:“二哥要回来了吗?”
“嗯!”叶顺点头,随后又道:“不过他肯定没有时间带你去吃梅花糖葫芦。”
叶真真小脸一红,不争气的咽了一口口水,哼道:“我才不是想吃梅花糖葫芦。”
……
小镇镇东的宁清闲家,身穿“正义”字样衣服的宁清闲打开信条,突然“噗嗤”一声,矮小身材的他高兴的哼着小曲,乱而密的胡茬像是在舞动,双手胡乱的打着拍子,悠闲得很。
“宁总队长,哦不对,宁副镇长,小的先在这里恭贺您了!”身穿同样印有“正义”字样的下属,恭维道。
“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别乱说。”宁清闲脸上笑开了花,就连斥责下属也未曾板着脸。
……
宋江河的死,就像是天空中连绵不断的雪花,飘散在整个小镇上。每个人的心思,都不尽相同,尤其是他离开后,镇长之位由谁来坐,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丧事,就在宋江河住的那座木楼的第一层举办,一切从简。
木楼的第一层,类似于大堂,只有几根承重的木柱子及上楼的木梯。棺材上摆放着白花,大大的“奠”字贴在最前面,后方墙体上,挂着一块大大的白布,简单写着五个大字:“祭奠宋江河” 。
一切从简,这是宋江河生前的理念。
宋江河的妻子秦慧婉身穿素衣,头披素帽,站棺材侧面,泪红了双眼。站在她左侧的,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孩,身穿孝服,灵动的大眼蓄满眼泪,她是宋江河唯一的孩子——宋清欢。最右侧的,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剑眉星目,穿着苍白孝服,他是宋江河收养的义子——宋铁衣。
木楼的第一层入门处,有两个年青人身穿素衣,站在两侧,用于招呼宾客。他们不是下人,是叶顺店内比较机灵的伙计,叶顺安排他们来这里帮忙。
最外面,十几个帮忙的人正忙活着,烧的烧水,切的切菜,还有一些正露天中搭建棚屋,用以接待前来祭拜的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