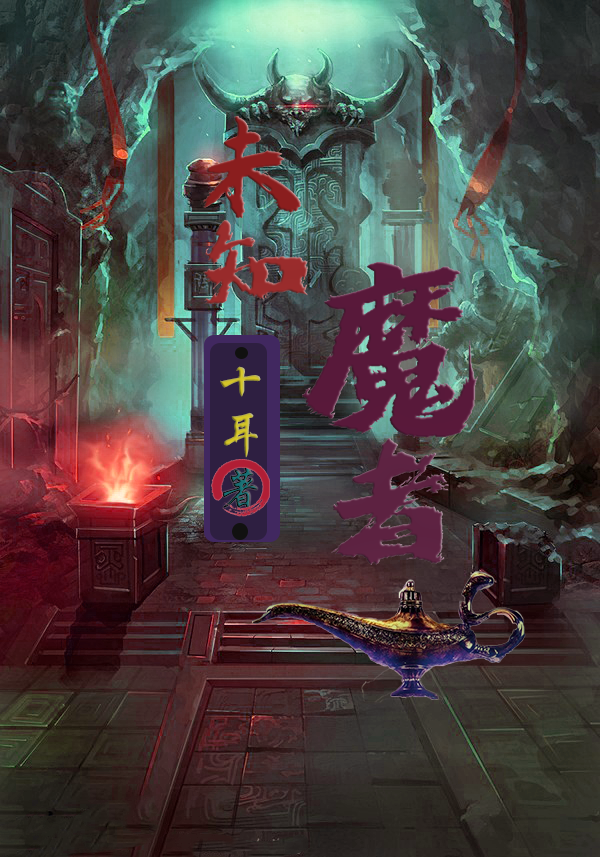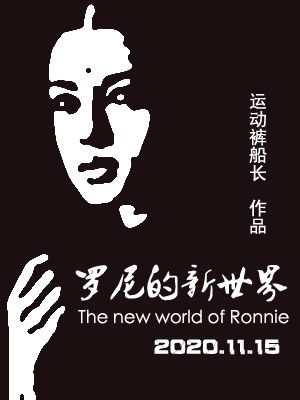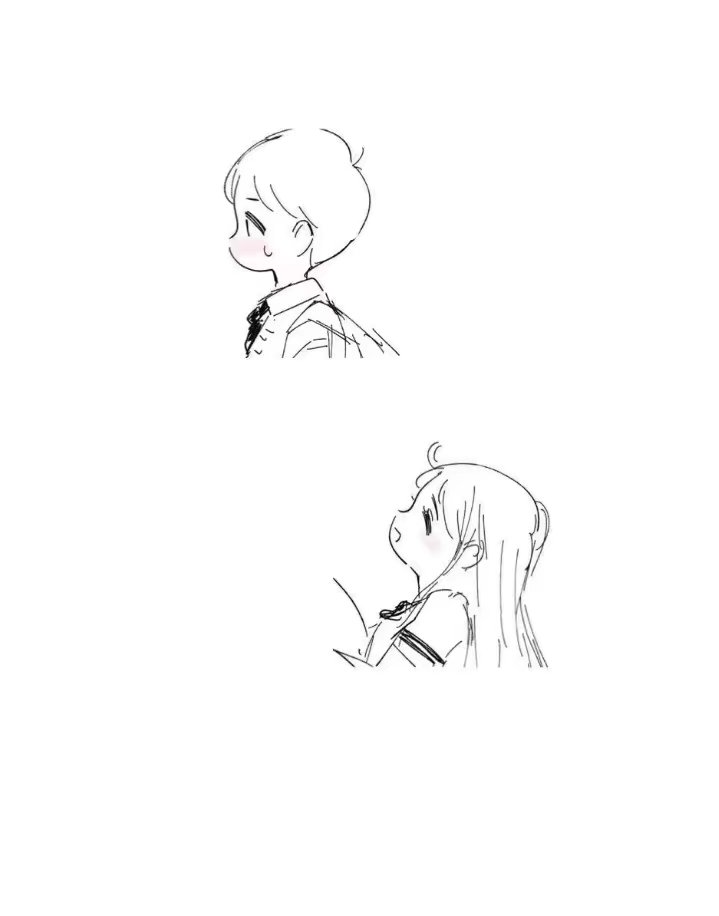巍峨雄城外,又一场战事刚刚落幕。
几十具尸体用一种狰狞的姿态堆叠在战场各处,鲜血从残肢断躯中淌出,在大地上绘出一幅淋漓肃杀的修罗图。
与这座雄城时常经历的战事相比,方才这一战充其量只能算是小仗,敌我双方的兵力加起来也只有几十人,但这一场厮杀的惨烈,令雄城上那些观战的百战将士都为之深深动容。
一番追逐,短兵相接。
无一后退,无一生还。
士死战方休,将同归于尽。
双方的将领在重伤后,同时用残存的力气举起手中刀,向对方发起了最后一次冲杀。
沉闷的利刃破腹声中,两员将领就这么互相瞪视着,用插入对方胸口的刀来支撑着自己的身躯,双方都不肯倒地,彼此恶狠狠的瞪着对手,没有握刀的手互相按着对方的肩膀,粗重的喘息声咫尺可闻,又转瞬轻微。
最后,彼此看着对方脸上的生机一丝丝熄灭,直到血尽而亡。
有风吹过,仿佛卷起了一地的呜咽,城上将士都默默的低下了头,即使身经百战,早看淡了生离死别,可看着袍泽战死城下,依然黯然。
一声轻柔的叹息从十丈城墙上响起。
在这道被世人称为一线墙的城墙上,上千将士林立处,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名女子。
女子一身戎装,一袭猩红披风猎猎飞扬。
杀伐本是男儿业,可这女子俏立城上,在一片刀枪寒芒,铁甲森然中,不显一丝突兀。
女子身材极高,迎风而立,宛如一面耀眼的旗帜,猩红色的斗篷遮盖了女子大半张脸,但露在斗篷外的半面眉眼,清丽不可方物,
峨眉黛扫,凤眼艳冶,竟是人间绝色。
女子的语声带着抹鼻音,在长风吹送中低沉悦耳:“十名斥候,对五十追兵,人人以寡敌众,算是一场小胜,却是---”
女子顿了顿,又是一声轻叹:“可惜了。”
身周的将士默然垂首,尤在为方才落幕的战事哀悼,立于女子身侧的一名将领微微点头:“是可惜了,这一曲十名斥候,尤其是领队的将领,身先士卒,以寡敌众,若能侥幸活过今日,再由大帅亲自调教,来日必为一方名将。”
这出言的战将高大雄伟,全身铁甲,五官冷厉如刀,立于城上,仿佛一尊铁铸战神,可立于女子身边,丝毫不显出众,反把女子衬托出一抹不逊须眉的英姿。
女子摇了摇头,右手抬起,在城墙的墙垛上轻轻一拍,目光从城上看向城下平原,又微微抬头,看向远处那一片险峻山岳,淡淡道:“这处平原,从来容不下侥幸一说,莫说是这十个名不见经传的斥候,铁相,便是你我,便是我们身后,那万里山河中的一位位当世名将,若今日在此,出城一战,也是生死由命,得不到这侥幸二字。”
名为铁相的雄伟战将点了点头,目光也随女子看向远处那一片仿若恶兽般蜃伏在大地上的山岳,随之轻叹:“身后,万里河山,身前,修罗平原,身在此地,生死一线,无非先后---”
城楼上忽然响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女子和铁相转头看去,见军士们纷纷点指城下。
遍地狼藉的城外平原,几具堆叠的尸体处有了一阵蠕动,先是一只手臂从尸堆下慢慢探出,随后,又露出了一张满是血污的脸庞。
有军士认出那人,激动的大喊:“是我们的斥候。”
城上顿时响起了一阵欢呼,刚才的厮杀着实凶狠,己方以寡敌众,最终拼了个同归于尽的惨烈结局,此刻见己方仍有袍泽存活,人人振奋。
从尸堆下爬出的人遍体鳞伤,右臂已被齐肘砍断,仅剩的左手按在膝盖上,摇摇晃晃的站直了身子,嘴里吐出一大口血,他向四周看了看,便趔趄着一步步向城墙这边走来,满是血污的脸高高抬起,看向城上。
是个很年轻的男子,还不到二十岁的年纪,满脸血污也掩不住他脸上的稚气未脱,看他一步步走近,城墙上已有人认出他来,方才一战,这少年第一个和带队的牙将回身杀向追兵,一柄长刀锋锐无匹,连杀五敌,为掩护牙将后背,被人砍断右臂后,只咆哮了一声,左手拾刀,继续杀敌。
“他一人杀敌九个,是除了那牙将外,最后一个倒下的斥候。”城上有军士一直盯着这少年,看着他当先冲杀,看着他断臂再战,看着他力竭倒地,此时,便用敬佩的语气说出了这少年方才一战的勇猛。
铁相立刻下令,“开暗门,速速接应这少年回城。”
有军士应命,立刻便要打旗语令城下守军开启暗门,接那少年回城,女子却一抬手,示意军士停下。
铁相诧异,正要开口询问,女子微微抬头,被斗篷遮掩的脸庞看不清神情,只是示意铁相看向城下。
那少年还在一步步走向城墙,走过处,一地血痕,头却高高抬起,正看着城上众人。
他抬起仅剩的左臂,擦了擦满脸血污,眉眼挤了挤,大概是触到了伤处,脸上露出痛楚之色,但仍努力向城上挤了挤眉眼。
看到少年龇牙咧嘴的模样,也不知他是要呼痛还是呼救,铁相和一众将士都有些不明所以,女子带着鼻音的语声淡淡浮起:“这少年,往日里必是个不安分的,都这时候了,还不忘扮鬼脸。”
铁相和众将士这才明白,都有些哑然,想笑,可笑意才到嘴边,便化为了黯然。
谁都能看出,这少年已是油尽灯枯。
铁相向城下高喊:“撑住,我这就来接应你。”
出人意料的是,少年却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向城上众人摇了摇头,他此刻伤重垂危,这一摇头的动作做来很是艰辛,却又无比坚决。
城上众人都觉莫名,女子看着城下,面无表情,只微微颔首。
这时,少年又伸长手臂,向后指了指。
他所立身的这平原外,便是如上古恶兽般匍匐的千里山峦。
城上立刻有将士取出用来侦敌望远的千里目镜,凝神向远处看去,铁相和其余将士也全神戒备的看着远处山峦,只有那女子默默的看着城下少年,看他拖着随时要倒下的身躯,一步步走向城墙。
用千里目镜望远的将士很快开口示警:“至少上万人,正从阴山密林中走出。”
城上将士顿时了然,原来这少年早已察觉到身后有大股敌军蜃伏,方才的短兵相接,只是一个引他们出城的陷阱。
铁相看着踉跄走向城墙的少年,忍不住叹了一声:“这少年郎,是把好刀,更是条好汉---”
铁相又觉惊讶,既然这少年不想回城,为何还要拖着残躯,一步步走来。
女子低下头,在心里自语了一句:“就当是看在这个鬼脸的份上,只这份洒脱,便值得我给予一份敬重。”
女子开口:“名字?”
她没有看向任何人,只是说了两个字,身边的铁相立刻回答:“这少年是汉朝人,姓风,名士杰,半月前入关投军。”
女子点了点头,脸上有些赞赏之色:“想不到,已是暮气沉沉的汉朝,竟也有如此少年。”
女子抬起双手,褪下了头上斗篷。
于是,一张绝美的容颜出现在雄城上。
城上将士虽早睹得这女子的倾世风华,但此刻看向女子的目光中仍是一片钦慕。
只是钦慕,虽然风华咫尺,但所有将士脸上都没有一丝男子对绝色的爱慕。
因为这女子不但貌倾城,也是这一城之帅。
女子看向城下步步走来的少年,抬高声音,语声清朗:“风士杰,你可有何未了心愿?我厉红萝今日城上许诺,无论你有何心愿,必倾尽全力,了你心愿。”
女子的语声随风而送,声虽轻柔,却有着五岳为重的气概。
少年抬起头,看向城上,在看到厉红萝的绝美容颜时,似乎也有了一刹那的目眩神迷,但只是看了一眼,便摇摇头,继续蹒跚走向城下。
虽然远处伏兵重重,但城上将士还是好奇起来,都不知这少年心思,他既不肯回城,为何还要一步步走来,而对他们最崇敬的厉帅所给出的承诺,这少年似乎也是漫不在乎。
难道他不知道,即便他命不久矣,可不论他所求何事何物,厉帅既已许诺,便一定会为之践诺。
红颜罗刹一诺,便是整个天下,都将为之动容。
因为,便是一诺,这本该步入朝堂,享尽人间繁华富贵的女子,单骑入关,为身后的万里山河,镇守了十年。
那一诺,令世间无数对她有着好逑之心的男子为之神伤,却也守住了十年的人间安宁。
少年风士杰已走到了城下,他不再抬头,整个身子靠在厚重如山的城墙上,仅余的左手按在被齐肘砍断的左臂伤口上,随后,满是鲜血的左手摸索着指向城墙。
虽然强敌即将再次来犯,可城上将士都按捺不住好奇,一个个探出头,睁大眼睛看着少年的举动。
女子厉红颜也是忍不住好奇,却不肯如其他将士般探头探脑的看向城下,只是默默的立于城头。
已有探头的军士大声的说出了少年的举动:“他在写字,用手指蘸着伤口的血,在城墙上写字,这---这也太---太---”
那军士本来想说一句这少年的行径太傻,但想到他即将死去,硬生生忍住了没说出口。
厉红颜低下头,悄悄翻了个白眼,心说:“再是洒脱,也别写下风士杰到此一游啊。”
又有军士高喊:“他写了个草字---”
边上立刻有人矫正:“是个蒋字,你这丘八,字都不识---”
有个站在棱墙的军士,干脆拿起那望远的千里镜,看着少年在墙上的涂抹,一字字跟着念了出来:“蒋小小,我---我---”
他身后那些没有千里镜的军士急不可耐的追问:“我什么呀?快说啊,这兄弟写了什么字?”
拿千里镜的军士回过头,一脸哭笑不得:“他写了,蒋小小,我喜欢你---”
其余将士的表情顿时也变得哭笑不得,虽知不该,还是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军士们议论纷纷:“这蒋小小是谁啊?”
“想必是这少年的心上人吧,可这---再是喜欢,也别写在咱朝歌的城墙上啊?”
有人低声说了句:“这小子,有种!”
边上立刻有人频频点头。
厉红萝听到那少年竟写下了这么几个字,脸上神色也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低声喃喃:“这厮---这厮---”
即便是这一生都纵横捭阖,不让须眉的女子,此时也委实不知该如何点评。
那叫风士杰的少年已经写好了那一行字——蒋小小,我喜欢你!
然后,他像是做下了什么最了不得的事一般,晃晃悠悠,却又得意洋洋的倒退着离开城墙。
他的头一直高抬着,应是想让城墙上所有将士都能分享到他此时的喜悦。
即便断了右臂,即便满脸血污,还是能看到他此刻的得意。
终于,可以向心爱的女子告白,即便你在千里之外,但我,还是鼓起勇气,写下了一直不敢对你说的这句话。
少年高举起仅存的左臂,向城上将士挥了挥手。
脸上,神采飞扬。
虽然他一个字都没说,虽然城上将士对这初来乍到的少年都极陌生,但大家都能毫不费力的读懂了他此时的快意。
将士们脸上都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这样的飞扬跳脱,便是年轻吧?
这般的少年对少女的好逑之心,便是人间美好吧?
即便是那位身形高大,面容冷厉,一向执掌城中刑律的铁相,一贯冷峻的脸上,也浮起了一丝笑意,隐约想起,很多年前,当自己也还年轻时,也曾想对心仪的女子,这般表白一句,即便羞于启齿,也该如那少年一般,洒然书下。
铁相很用了些力气,才忍住让自己没有在此时,悄悄转头去看身侧。
他身侧,站着这座雄城的主人,红颜罗刹,厉红萝。
当年,她也是个韶华少女,一身红裳,从晚霞中走来,一颦一笑,便惊艳了人间。
铁相深吸了一口气,平稳了有些涟漪的心神,看向城下。
城下,那叫风士杰的少年,正用仅存的左手,吃力的捡起一把刀,然后,又向城上诸人,洒然一笑。
随即,风士杰回身,仗刀,一步步走向雄城之外的平原,
那里,他的袍泽刚刚倒下。
城上忽然一片沉寂。
少年年轻,却已油尽灯枯,他在临死前,写下了他对这世间最美好的心愿,即使心愿未成,已不枉他在这人间来过一遭,活过一遭。
最后,他便要在这守护整座中原的雄城之外,用自己的残躯,做最后的守护。
少年蹒跚的步伐已经停下,背对着城墙,站在了片刻前,他和他的袍泽搏命死战的平原上,停下脚步,站定了身躯。
左手刀拄在地上,支撑着身躯,一动不动。
有风吹过,带起了少年的衣襟。
他背对着身后城墙,于是看不清他脸上最后的表情。
城上将士都黯然的低下了头,他们知道,这少年脸上,必是带着和方才一般的快意,呼出了此生最后一口气息。
汉朝,风士杰,长安人,年十九。
半月前单骑入关,半月后力战而死。
归来时,笑容依然。
归去时,依然年少。
他用最后的力气写下了他想对这个天下说的话。
他用最后的生命站在他想守护的这个天下之前。
生,不负此生。
死,何其快意。
远处,隐约的尘烟逐渐清晰,黑压压的敌军,正在平原上罗列成一道吞噬人间的恶潮,汹涌而来。
这座雄城的主帅,红颜罗刹厉红萝看着远处,语气平静:“临战!”
城楼上,金鼓齐鸣,杀意贲张。
这就是天下第一雄城,朝歌城了。
百里雄城,虎踞中原之门。
战争,是这座雄城最不缺少的特产。
年年有血战,日夜备长战。
而这连场大战后,是他们为整个中原天下的镇守。
厉红萝紧了紧衣甲上的丝绦,淡淡说:“是我想差了,我们都知道,敌军必有伏兵,我们想靠地利,居高临下的打一场守城战,减免将士伤亡,所以眼睁睁看着这十名斥候在城下死斗,却未曾出城救援。”
铁相悄悄看了厉红萝一眼,他追随了厉红萝整整十年,能听出她平淡的语声里有一丝悔意。
“我错了,朝歌能在此屹立十年不倒,靠的不是我这厉帅,也不单单是将士勇猛,而是我们,从不会舍弃袍泽,从来都生死并肩,是我一念之错,致使这十名斥候战死城下,所以这一战,我改主意了。”
厉红萝语气依然平淡:“不打守城战,朝歌,开城,迎战!”
城上将士没有一句质疑,只是齐声尊令。
厉红萝右手平伸:“这一战,我为先锋!”
铁相犹豫了一下,想劝,没有开口。
厉帅决意,无人可逆,这是朝歌最大的规矩。
边上的亲卫双手捧上一杆鲜红色的五尺长枪。
这是厉红萝的兵器,五尺枪,寸寸血,名长锋。
她是主帅,其实不需要亲自迎敌,但在今日,她很想亲自用手中长锋,饮一饮恶敌之血。
厉红萝的视线,一直停留在那个在她的城墙上,留下那一行于此雄城似是不伦不类,甚至有些惹笑题字的少年背影上。
少年已然瞑目,但她想多送上几颗敌首,为他殉葬。
厉红萝接过亲军奉上的长枪,淡淡问:“上一次,汉朝派人往我朝歌送来兵马粮草,是什么时候?”
“约是---足有一年,汉朝的朝廷,没有派兵过来增援了吧?不过---”身后铁相也早端起了斩刀,打算陪着主帅亲自出城,“汉朝民间,一直有义士自发前来,这风士杰,便是半月前来的。”
厉红萝轻轻一笑,很轻的笑颜,却不是妩媚动人的红颜轻笑,而是真正的轻蔑一笑:“刘永这厮,也算是汉朝几百年来,难得一遇的昏君了,我辈义士,在这朝歌城长战长歌,他却躺在他的长安皇宫里,夜夜笙歌。”
城楼上,已做好了大战将来的准备,一个个高大魁梧的箭士,端起了一人多高的铁胎弓,城门内,铁骑列下锋矢阵型,只待城门一开,便如利箭般冲杀而出。
铁相走到厉红萝身侧,低声说:“大帅,刘永昏聩,不必与他置气。”
“我怎会与这等朽物置气,我朝歌城上下,日夜在此,日夜苦战,也从不是为了替他刘永守护天下---”厉红萝已往城下走去,在亲军簇拥中淡淡说:“我们守护的,是天下苍生。”
朝歌将士的脸上都露出了正是如此的笑意。
厉红萝走了几步,又转头看向城外。
平原上,那叫风士杰的少年仗刀而立,身虽死,顶天立地。
厉红萝眼中有了一抹与临阵恶战所不符的柔和,低唤了一声:“鹰奴儿。”
一声清亮的鹰呖声中,一头展翅后足有丈余长的苍翼雄鹰飞掠而来,在众人头上一个盘旋,雄鹰收翼,稳稳停在城垛上。
一个少女坐在雄鹰背上,轻盈落地。
这少女身材姣好,蜂腰翘臀,一身短装,短袖收肘,短裤齐膝,在满城男子面前,若无其事的裸露着她麦色的手臂与小腿。
只不过,这被唤做鹰奴儿的少女,容颜虽极美艳,身材也是诱人,但眉眼顾盼之间,先有一股桀骜杀气扑面而来,而在她腰间背后分别悬配的四柄无鞘匕首,也足以让人一眼便知,这女子绝不好惹。
鹰奴儿走到厉红萝身前,低眉顺目,脸上的桀骜瞬间变的驯服。
“你去城下,把那少年写的字拓下来。”厉红萝替鹰奴儿拂了拂额前秀发,看着这少女总是旁若无人般裸着的小臂长腿,微微叹了口气,“你这便走一遭长安,找到那个叫蒋小小的女子,她有何心愿,都替她了了,她的后半生,只要朝歌城在一日,便管她一日,她要衣食无忧,你便给她一世的锦衣玉食,她家若有什么血海深仇的对头,你便去把那家给灭了门,那风士杰,在朝歌战死,便是我朝歌中人,规矩,你懂的。”
鹰奴儿先老实的低头应了一声,随即抬头,带着点不甘的小声问:“能不能等打完这仗,我再去啊,你都要亲自上阵了---”
鹰奴儿拍了拍腰上四把匕首,很孩子气的笑笑:“我这春夏秋冬四把刀,也想沾点血啊。”
这少女笑起来,眉眼间的桀骜凶戾顿时消失,看上去还颇有些女孩家家撒娇的娇憨气,只不过她这话里还是杀气十足。
边上的将士都露出了不知该如何面对的表情,这鹰奴儿,是朝歌城上下公认的美艳尤物,但这尤物,也是举手投足间便能取人性命。
厉红萝对这少女倒是一直都有些宠溺,略一想便说:“也行,就依你,打完再去,不过城墙下那字,先给我好好拓了。”
鹰奴儿一声欢呼:“厉帅最疼我了。”
欢呼后,鹰奴儿随即一跃而起,竟笔直向城外跳了下去。
城上将士也都面色如常,似早都习惯了这少女的言行举止。
停在城垛上的雄鹰一声尖呖,展翅飞下去接应它的主人。
铁相在边上轻声说:“大帅,寻那蒋小小的事,是替战死将士料理后事,这等事,我们一向是派涌泉客过去,你把这杀气腾腾的鹰奴儿派过去干这事----”
铁相苦笑了一下:“不太合适吧。”
“若是别处,当然不合适,可去长安,鹰奴儿最合适。”厉红萝有意顿了顿,似在沉吟措辞,又扫了眼身边的将士,还是直接说了出来:“长安就要大乱了,刘永那厮,是个只顾着自己荒淫享乐的昏君,可他的皇宫里,还有个极厉害的女人,那个女人,不会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刘永一直糟践汉朝江山的---”
厉红萝笑了笑:“在那个女人眼里,这汉朝江山,是祖宗传下来的基业,也是他儿子的家业,哪能再容得刘永这么个不会当皇帝,更不会当老子的角色,一而再的伤了汉朝的元气。”
厉红萝迈步,向城下走去,语声淡淡:“女子柔弱,为母则刚,若我所料不错,就这几个月内,汉朝皇宫里那个女人,就要腾出手来,只手补天裂了,大乱一起,难免死伤,鹰奴儿那四把刀,可以杀人,更可以救人。”
城楼上的铁甲将士中,至少有三成是来自汉朝的人,其中还有一些曾在汉朝出任仕途,可听了厉红萝这番话,谁也没有流露出一丝自己君皇被冒犯的忿忿,反在仔细品过之后,为他们曾经效忠的王朝,长舒出一口气。
金鼓声中,厉红萝的语声突然激昂起来:“朝歌将士,听令!”
城下,缓缓拉开的城门内,厉红萝一身血色披风,手举五尺长锋。
枪锋指向,是拉开的城门外,那名叫风士杰的少年,挺拔不倒的身躯。
“今日城外一战,便以风士杰立身之处为界,所有人,都要冲杀在这少年身躯之前,即便力战而死,也不许退过,这少年所立之处。”
厉红萝催动坐骑,一马当先,第一个冲过大开的城门。
女子清喝,响彻天地:“战争来去,军魂常在! 朝歌!”
“朝歌!”无数吼声随着女子清喝,昂然奋起,无数铁骑,纵马出城,迎着汹涌而来的恶潮,迎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