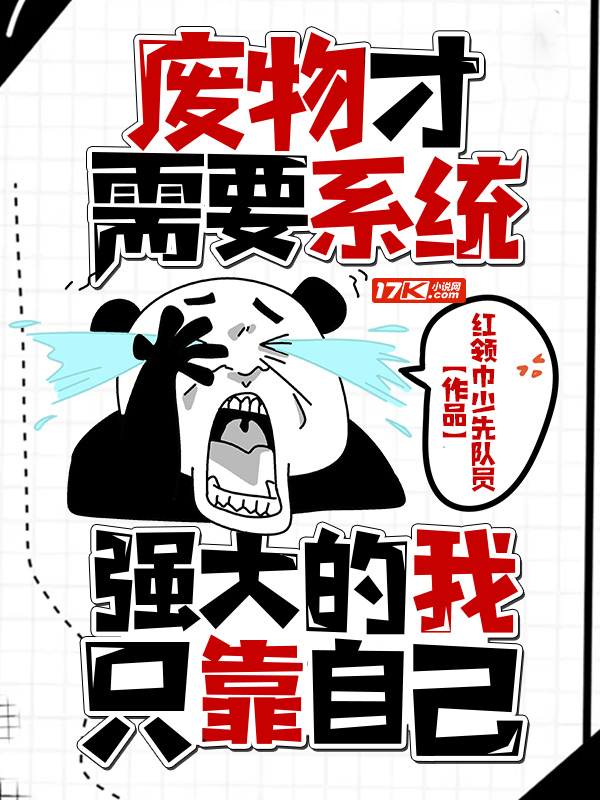永乐皇帝大败蒙古瓦刺部落之后,蒙古鞑靼部落又逐步崛起,横扫其他部落,渐成蒙古草原上的霸主。部落首领阿鲁台自恃兵强马壮;又恨永乐皇帝曾经的征伐使其坠马,大迭颜面,遂时时纵掠寇边,并于永乐十九年十月大举兴师,亲帅铁骑五万攻打兴和,数日便攻破了兴和,兴和守将王祥战死。消息传到北京,永乐皇帝大怒,欲再帅师亲征,让户部尚书夏元吉、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刑部尚书吴中议北征粮,皆言粮储匮乏,不宜劳师,永乐皇帝心有不豫,命查开平粮储,回报仓满粮足,永乐皇帝遂以隐瞒实情,阻扰北征为由下四人狱,兵部尚书方宾害怕锦衣卫诏狱里的种种酷刑,于入狱当夜自杀。擢兵部左侍郎李庆为兵部尚书,命与隆平侯张信全国督饷备征。调民驴三十四万余匹,运粮车一十七万七千五百余辆,役夫二十三万五千余人,粮食三十七万余石,悉征调至开平,以备北征之用。永乐二十年三月,敕封中军都督府都督朱荣为骁勇将军,令领前锋,左军都督府佥事薛贵为副;以神机营都统、安远侯柳升领中军;宁阳侯陈懋领御前精兵,恭顺伯吴克忠领御前马队;武安侯郑亨领左哨,保定侯孟瑛为副;阳武侯薛禄领右哨,新宁伯谭忠为副;英国公张辅领左掖,安平伯李安为副;成山侯王通领右掖,兴安伯徐亨为副;成国公朱勇领后卫,永顺伯薛斌为副。帅精兵三十万往征阿鲁台,五月出宣府的鸡鸣山,闻阿鲁台遁,众将皆言当精兵速击,永乐皇帝弗许,谕众将士曰:“兵行犹水,水因地而顺流,兵因敌而作势,水无常行,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取胜者,盖得势者也。”六月出应昌,令结方阵以进,谍报阿鲁台分兵攻万全,诸将请分兵击之,永乐皇帝谓众将士曰:“此乃诈也,彼虑我大军捣其巢穴,欲以牵制我师,岂敢攻城也栽?”遂命只加速进兵,勿理万全之敌,旋果报万全之敌遁去。兵进至阔栾海南岸,见阿鲁台辎重部族正在转移,纵兵击之,杀阿鲁台部族数百人,俘获百余人,余皆散走,收其粮储牲马,余皆焚毁之。从俘虏口中获悉阿鲁台闻明廷进兵急,抛下辎重部族越阔栾海北遁。此正盛夏,阔栾海水宽浪急,渡海追之恐为所乘,绕道又路途遥远。永乐皇帝遂放弃北进,集众将士曰:“虏遗辎重部族,领精骑北遁,乃诱我深入,进恐蹈邱福之覆辙。阿鲁台敢悖逆,恃兀良哈为羽翼也,今阿鲁台狼狈远遁,而兀良哈之寇尚在,当还师剪之。”众将皆曰‘然’。兀良哈部,时人又称朵颜三卫。洪武二十年,太祖遣冯胜、傅友德、蓝玉率兵二十万,绕道庆州包围了驻扎在金山的北元太尉纳哈出的部队,纳哈出被迫投降,北元辽王阿札失里失去了可以依赖的金山屏障,不得不向明廷投降。洪武二十二年,太祖将辽王阿札失里所属塔尔河流域翁牛特人生活的区域设为泰宁卫,乌裕尔河流域乌齐叶特人生活的区域设为福余卫,屈裂儿河上游朵颜山一带兀良哈人生活的区域设为朵颜卫,均为宁王朱权就藩的大宁都司所统辖。刚设三卫时,泰宁卫最强,福余卫次之,朵颜卫最弱。 可是不久,朵颜卫逐步强盛,而且远强于另外两个卫所,人们遂称三卫为朵颜三卫,又朵颜卫以兀良哈人为主,故又称三卫为兀良哈三卫,亦称兀良哈部落。建文元年,燕王以‘靖难’反,饵之以利,尽得三卫精骑相助。既得大位,感朵颜之功,迁宁王权于南昌,将宁王大宁都司藩属悉与朵颜,至是兀良哈部落强大,成为与鞑靼部落、瓦刺部落可以相提并论的三大蒙古部落之一。明失边藩,难制胡虏,终为所寇。阿鲁台败邱福军,亦有朵颜三卫的精锐骑兵相助。
永乐皇帝选精锐步骑分为五路,每路两万,各路领兵大将分别是:第一路朱荣、薛贵,第二路孟瑛、谭忠,第三路张辅、李安,第四路徐亨、马忠,第五路朱勇、薛斌。临行永乐皇帝授之方略:“兵贵神速,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也。”于是人衔枚,马勒口,五路兵马倍道急驰,直捣虏巢。五路大军去后,永乐皇帝谕余下众将曰:“我大军骤至,虏必不敌西走,朕以兵西要害之地伏击之,虏可获也。”永乐皇帝命武安侯郑亨、成山侯王通、阳武侯薛禄领后军戒虏谨慎行动,徐徐回撤。自与安远侯柳升、宁阳侯陈懋、恭顺伯吴克忠带领神机营、御前精兵和御前马队共计五万余人,星夜兼程,来到兀良哈部西边捕虏川设伏,不久果见兀良哈步骑辎重逶迤而来,连绵数里,走在前面的是骑兵部队,待兀良哈的骑兵部队进入伏击圈,永乐皇帝一声令下,柳升带领神机营万铳齐发,一时间声震山岳,光耀四野,兀良哈先头骑兵纷纷坠马,死伤极多。随后永乐皇帝和忠顺伯吴克忠带领御前马队两万余骑出击,对那些负隅顽抗者一一枭首,并沿路焚烧辎重。最后宁阳侯陈懋带领御前精兵两万余人,收其牲口降众数千计。原来兀良哈精骑一部随阿鲁台北遁,一部留下来保护族人财产,闻明五路大军征讨,仓促间组织了数千骑兵去迎战明五路征讨大军,其余的带了族人辎重西走,那数千兀良哈骑兵自然不是明五路大军的对手,全都被分割围歼。此战斩兀良哈曲帅十余人,杀万余人,俘获数千人,致使兀良哈部险遭灭顶之灾。永乐皇帝以大胜班师,传谕全国。兵回宣府,永乐皇帝谕众将士曰:“阿鲁台以为我得胜回师,必然无备,定速来寇边,我偏兵不解甲,马不去鞍,整肃以待,可获而擒之也!”于是兵住宣府,传旨皇太子继续监国,礼部尚书蹇义辅政;令宁阳侯陈懋、新宁伯谭忠领骑向北日夜巡哨;令隆平侯张信、兵部尚书李庆全国督饷至宣府。
永乐皇帝久不回京,喜的赵王朱高燧眉开眼笑,朱高燧乃永乐皇帝第三子也,既无大皇兄朱高炽传位嫡长之优势,又无二皇兄朱高煦靖难功高之威望,本无皇权之念。然太子行事,常令永乐皇帝不满,人皆共知;又朱高煦被贬乐安,无皇命不得回京;由是赵王朱高燧以为可窥大位。明制王可拥三个护卫,赵王朱高燧亦有三护卫,取名常山左、中、右护卫,乃因三国常山赵子龙的盖世武功而名之,常山中护卫都指挥孟贤,赵王贴身侍卫长,与钦天监官王射成友善,射成秘谓孟贤曰:“吾观天象,帝星衰微,不久将易大位。”贤告赵王,欲得大位。于是孟贤、王射成和永乐皇帝內侍杨庆养子等秘谋:造伪诏,进毒于帝,俟晏驾,矫诏废太子,立赵王。常山中护卫总旗王瑜姻亲高以正,乃常山左护卫千户,亦参与了此谋,谋定告瑜,瑜秘驰宣府上变。永乐皇帝闻之曰:“岂应有此?”秘回京师,捕孟贤等人,得所造伪诏,召赵王上殿,举伪诏质问高燧:“尔为之耶?”燧大惧不能言,太子力为之解,曰:“此下人所为,高燧必不与知。”燧得以免死,贤等皆伏诛。是夜永乐皇帝梦见二儿子朱高煦领兵杀入京师,削去了太子的头颅,并举剑逼自己退位,醒来后口吐数碗血,已然是忧愤成疾了矣。时为永乐二十一年的五月。七月又报阿鲁台领兵犯境,永乐皇帝不得不带病出征,九月兵至西阳河,闻阿鲁台已为瓦刺所败,遂驻师不前,十一月哨马报有鞑靼军南来,遂继续北进,在上庄堡遇鞑靼王子也先土干帅部来降,封忠勇王,赐名金忠。鞑靼王子与言亦不知阿鲁台之踪迹,永乐皇帝遂不得不下令班师。
永乐二十二年正月,阿鲁台犯大同、开平,诏群臣议亲征阿鲁台,礼部尚书蹇义谏曰:“陛下病未痊愈,不宜鞍马劳顿。且漠北广袤,胡虏又飘忽无所踪,劳师远征,恐无所获。宜派骑兵袭击之。” 永乐皇帝大怒,道:“吾师未出,汝却言劳师无所获,意欲乱我军心乎?待我擒获阿鲁台,与汝一并斩于午门。”命将蹇义下锦衣卫诏狱,无有再敢谏者也。遂敕令边将整兵俟命,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辽东五都司兵期会北京,得兵三十万。时朱荣、薛贵已往镇辽东,遂安伯陈志已故,其子陈英袭爵。遂命宁阳侯陈懋、忠勇王也先土干领前锋;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领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孟瑛领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领右哨;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领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领右掖。兵出北京,往征阿鲁台,五月初到达隰宁,悉阿鲁台已逃往答兰纳木儿河,永乐皇帝命全军急速追击,六月中旬追至答兰纳木儿河,并未见敌踪,命穷搜周边山谷三百余里,仍无所获。只得驻兵河岸,遣前锋陈懋、也先土干继续北进,至北邙山,以粮尽还。永乐皇帝正自气恼,不知该往何处进兵,有阿鲁台使来见永乐皇帝,道:“大王有言欲告陛下。”永乐皇帝道:“贼首何言?”阿鲁台使道:“大王言‘尔自东逐我,则我乃西走;自西逐我,则我乃东走;终不与战,尔欲奈我何?’”这恰戳永乐皇帝心中痛处,大军出塞,每日里不见敌踪,空自劳师,如何向臣民交代?永乐皇帝捂头大叫一声,栽倒军前,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张辅命割阿鲁台使耳鼻,逐出大寨。永乐皇帝是夜方醒,第二天病转沉重,不得不下令班师。兵行至榆木川,已是数度昏迷,知大限将至,传张辅吩咐后事,道:“太子已经历练,足以当国,传位与太子。蹇爱卿乃是爱惜吾身,吾不之察也,望太子善待之。”言毕而崩,年六十有五。九月皇太子朱高炽即皇帝位,曰明年为洪熙元年。上尊谥曰: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长陵。
建文帝于‘皇印’一河湾处题诗北去,来到幺滩场,择街尾处一个叫幺店子的小客栈住下,向过往行人打听灯笼山的所在。幺滩场乃四川北道大竹路邻水县辖的一处交通要道,西河到此西拐,逆水蜿蜒向北直抵华蓥山南麓,且延伸旱道可达陕南。陕南、川北的客商,大都喜欢用这条水道运送物资。中原经荆襄去往川藏的一条旱道,又恰从幺滩场经过。陕南、川北的大米、煤炭、木材等物资,经水道运来这里,再上岸或东出荆、襄甚至更远的中原,或西去川、康甚至更远的西藏。中原的陶瓷、布匹,康藏的药材、染料也常常到这里转走水道,北去甘陕,南达滇黔。至是这里十分繁华。幺滩场沿河而建,修有南、北两个码头供船只停靠和物资转运,街上客栈、茶楼林立,街的中心有一个戏楼,每晚戏楼前总是人满为患。建文帝白天茶楼里喝茶,晚上戏楼前看戏,逢有陌生面孔,总要打听灯笼山在哪里?一晃三个月,仍是没有打听到灯笼山的所在。建文帝心里着起急来,身上的盘缠,除几两散碎银子,本来是有数锭银子和御玺包在一起的,已随了御玺沉身水底,大拇指上一个玉指环,也当来花的殆尽,眼看无以为继,这日信步来到北边码头,已经十月了矣,刺骨的寒风从山脊上下来,和西口的河风交汇,打在人的身上,更增添了些许的寒意。建文帝见码头一角有一老者在替人代写家书,只需一桌、一椅、一招牌,再加上纸、笔、墨、砚,便可开张,亦想代书糊口,但看了一晌又打消了此念,老者衣衫褴褛不说,而且来代书者也是寥寥。兀自气馁,忽又转念:何不写了启示来张贴,让更多的人看到,引来知悉者,亦未可知?于是他回到客栈,写了三张启示,贴于南、北码头的张贴栏和戏楼门口的墙上,启示的内容如下:
吾妻向氏,娘屋在灯笼山下,孤身远嫁与我,数月前回娘屋暂住,离家不久吾家遭遇火灾,将家烧为灰烬。因吾未及拜会岳家,故不知灯笼山之所在。今孤身流落至此,有知灯笼山者,往告必酬!
无名旅居客
幺店子客栈二零二室
启示贴出的第二天上午,一中年人来见建文帝,道:“吾知一处叫灯笼岭的地方,那里有一户人家,常年深居简出,不知是不是你要找的那户人家?”建文帝听说,便随那中年人去了那户人家,那户人家在幺滩场隔河不远一个叫杜家朝的地方,杜家朝前有一山叫雷公山,后有一岭,叫灯笼岭,岭上有石酷似灯笼而得名,那户人家就在灯笼石旁一山凹处,三间土坯瓦房。建文帝他们来时大门紧闭,叩门无人,寻屋后山坡,有母女俩在挖红薯。闻言母亲道:“吾夫家姓杜,娘家姓黄,吾只有此女,未及婚嫁,汝所寻向家,非是吾家也。”建文帝见那女孩儿灰头土脸,衣着补丁,非为向氏也,自然是失望,衣兜里拿出两个铜板,递给那中年人,道:“此非吾所寻之人家,吾盘缠将尽,仅此薄谢,乞望笑纳。”中年人道:“吾非为酬谢也。此既非汝所寻人家,汝又盘缠将尽,见所书启示笔墨上佳,当是一读书人,不如就吾东家的私塾堂里做先生,再慢慢打听汝所找寻之人家,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建文帝道:“甚善。”杜家朝为一个叫陈称的人所有,陈称在川北道果州做参政,家小均在果州路,此地为其二十年前偶得的一处产业,聘了当地人来做管家,事无巨细皆由管家做主。陈氏私塾堂在雷公山下,依山而建。私塾堂里的先生已年届七旬,是蜀郡重庆府巴州路长寿县的一名秀才,年前便说要告老还乡,只是一直没有请到合适的先生。建文帝幺滩场的客栈里退了租,来杜家朝陈氏私塾堂里做起了先生。寒来暑往,不知不觉五年过去了矣。这日建文帝放罢学生,抬头望见雷公山顶被落霞覆盖,非常美丽,想天正渐凉,今年的落日余晖也不知还能见到几回?于是他沿着私塾堂侧后的那条石级路一路向上,想看看今日之落霞。雷公山为周边最高之山,站在山顶,不但可以看到层峦叠嶂的远山,还可以在日出或日落的时候,看到太阳一点点的升起或掉落。于是人们修了上山的石级路,供闲暇时去山头看美景。建文帝来到山顶,太阳还只露有半个脸颊了矣。山顶上有一白发老者,正向西极目眺望,见到建文帝,赶紧跪拜!道:“臣杜景贤叩见陛下!”建文帝扶起,道:“吾失国久矣,早已不是一国之君。何先生在此?”杜景贤道:“吾生于斯,长于斯,杜家朝乃吾杜氏祖先留下之产业,失之于吾!”建文帝道:“乃吾失国所致?”杜景贤点了点头。道:“‘正学先生’在蜀献王府任世子师时,每年的春、秋都要在蜀献王府进行两次公开的讲学,吾曾前往聆听。因之同僚陈称告我‘正学先生’的弟子,遂遭籍没充军,受吾牵连的杜氏至亲十余家共计三百余人,悉数发往青海的几个卫所戍边,大都不耐边关寒湿,死于戍所,活下来的已不愿还乡了矣。吾坚持活到了今日,且还乡,乃有妻女遗留于此也。”‘正学先生’乃方孝孺也。建文帝道:“汝妻女为谁?”杜景贤道:“灯笼岭的那对母女。当年官兵来家逮捕,吾妻带了三岁的女儿越窗而走,得乡民相与掩护以幸存,结庐灯笼岭,躬耕以活。”建文帝做私塾堂的先生后,又见过那对母女几次,每次那女孩儿都是泥灰抹面,破衣蔽体。建文帝叹曰:“原来乃忠臣后也!”杜景贤字坡石,号溪泉,蜀郡四川北道大竹路邻水县人,建文二年进士,初为翰林待诏,旋入蜀任四川北道果州路参议,后值朝廷倾覆,为同僚陈称所陷,失其家业,发配充军。
远处落日陷去了最后一粒金边,留下霞光万道,射于空中。建文帝、杜景贤回转身,望眼灯笼岭。夹于雷公山和灯笼岭间的是很大一片平整肥沃的土地,建文帝指了那片土地,道:“整个杜家朝都是汝家之祖业?”杜景贤点头道:“包括陛下讲学的私塾堂和上山口的那栋三重堂的陈家祠堂,原来它们是叫杜氏私塾堂和杜家祠堂的,陈称得之冠以陈氏,陈称还想把杜家朝更名为陈家朝,然民不买账,仍呼之曰杜家朝。”建文帝道:“偌大之产业,先生失之可惜乎?”杜景贤道:“望眼所及的山外青山,曾陛下之产业,陛下失之可惜乎?”建文帝越过灯笼岭,看着远处的那些崇山峻岭,陷于沉默。崇山峻岭之外的大河奔流呢?还有那数不尽的城郭村落!能不为之可惜乎?杜景贤见建文帝陷于沉默,道:“陛下可知高煦事乎?”建文帝道:“知也。”时已为宣德四年的十月,永乐皇帝朱棣、洪熙皇帝朱高炽已相继亡故,皇太孙朱瞻基已即皇帝位,以宣德为纪年。朱高煦见父、兄已亡,遂于乐安反,学父‘靖难’,依样画葫芦:上疏指斥朝廷数罪,并索诛二三大臣蹇义、夏元吉等为奸臣。宣德皇帝议欲遣阳武侯薛禄将兵讨之,杨荣力言不可,道:“独不见李景隆事乎?”蹇义、夏元吉等亦力言亲征,宣德皇帝遂御驾亲征。大军围定乐安,以火铳射城,声震如雷,城中人股栗,多欲执献高煦者,高煦得悉大惧,狼狈出降。颈系煦及诸子入京,削煦庶人,系于西内。察天津、河北、山西都司指挥约举城应者凡诛六百余人。一日,宣德皇帝往视煦,煦出不意勾其踣地,宣德皇帝大怒,以煦力多,命用三百斤铜缸扣住,缸上积炭如山,燃炭至铜缸赤焰,煦被活活炙死,并致尸焦发灰,其凄惨之状,勿可以言。朱高煦子、孙数十人悉皆处死。宣德皇帝朱瞻基由是倍感忠臣的可贵,尽赦建文忠臣戍边者悉皆放还。致杜景贤得以还乡。杜景贤道:“朱高煦父作子述,直以‘靖难’之举为可世业者也,致彼骨肉相残,此亦乃朱棣逆取之报也。”建文帝一声长叹,道:“皇家岁月,不乏血雨腥风,去则去矣!”杜景贤见建文帝释然,己亦释然。两人相携下山,天已擦黑,此去灯笼岭,还有数里之程,更有两三里的山路,建文帝道:“天就快黑,山路难行,先生不如就这里暂住一宿。”杜景贤道:“吾妻女知我雷公山看夕阳,见黑必举火把接我。”果见远处一忽明忽暗的火把在淡夜中飘摇,于是两人拱手以别,建文帝站私塾堂边的路口,直到火把回走,消失在了夜下的黑幕。
溥洽因道衍的临终遗言得释,一路去到云南,闻建文帝离滇入蜀久矣,遂入蜀相寻,多访蜀地寺庙,耗十余年矣。这日来到川东北的一处山夹,时已黄昏,溥洽站在一小山堡上,乃一大片平地中间凸起的一个小山头,左边是一山,右边为一岭,山高岭低,小山头上立有一碑,碑上刻有三个字:杜家朝,碑已有些年岁了。溥洽知道是这山与岭所夹的这片土地叫杜家朝。他四下里望了望,觉得这杜家朝好大。见从山那边走过来一对父子,觉得那位父亲似曾相识。父亲身穿长袍,头系蓝巾,背了一个木架书匣,前面走了一个男孩儿,大约五六岁的样子,走到小山脚下,溥洽看的清楚,那父亲不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建文帝吗?溥洽伏拜于地,泣曰:“陛下!臣寻得你好苦阿!”可他的声音,被一个女子温柔的声音所覆盖:“相公!我们在这里。”溥洽起身,拭去眼泪,循女子的声音看去,只见山堡另一侧一条斜路上,有位盘髻花衣女子在向父子招手,女子腿上,靠着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儿,女子一手叉腰,一手捧腹,已然是有孕在身了矣。父子走近,女孩儿叫了一声:“爸爸!”扑进了建文帝的怀里,女子伸手牵了男孩儿的手,建文帝路边掐了一朵野花,插在女子的发髻上,女子嫣然一笑。然后一家人沿了斜路说说笑笑而去。溥洽轻声喟叹道:“多好的幸福一家阿!又何逊于帝王之家呢?”他腰间取下刻刀,在刻有杜家朝的石碑上刻道:
弘略难遮夺位耻
青山不以败为羞
溥洽刻罢,抛掉刻刀,走下山堡,走向遥远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