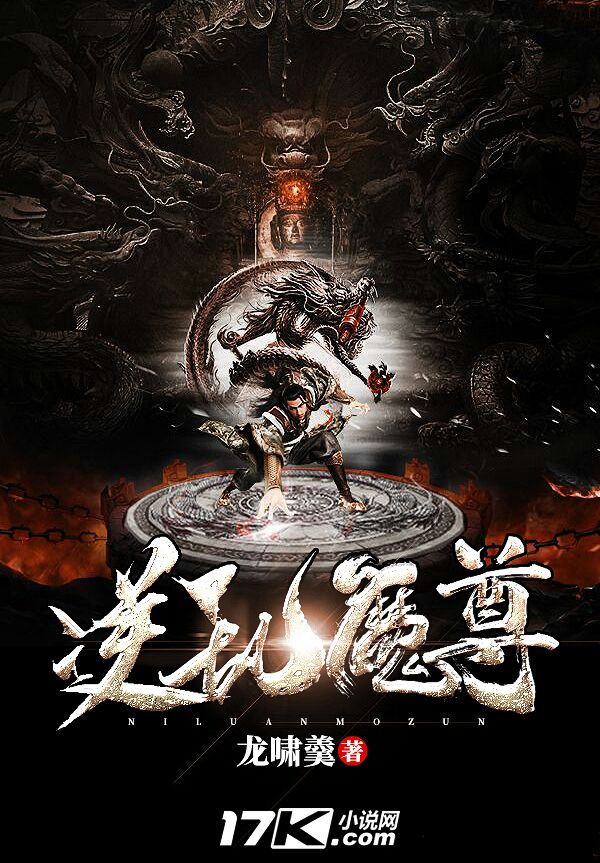阮稚一身素白衣衫,站在南疆的城墙之上。城墙高耸,寒风让人忍不住打哆嗦。
远处的兵马乌压压一片让人看得不真切,只能听得到将士们冲锋陷阵的嘶吼声。
刻着“大梁”二字的旌旗在西风中猎猎作响,好像要将这南疆撕个粉碎。
五年了,她被困在这荒凉的南疆整整五年。终于等到了大兵压阵的这一天,她却早已没了欢喜。
兵马逼近,大梁皇帝李胤亲率五十万兵马将南疆围得水泄不通,这一次,南疆的命数定了。
一个身材魁梧,面目骇人的男人抬起手中还挂着几滴鲜血的刀重重地架在阮稚的颈侧。
冰冷的寒气袭来,女人的身体不由轻颤了颤,眼神却依旧平静,像是一波古水,激不起半分波澜。
“李胤,你够狠!今日你大兵压境,屠杀我族人数十万!不就是为了救这个女人吗?”
男人说着将手中的刀又往女孩的脖颈凑了凑,锋利的刀刃划破女人娇嫩的脖颈,流下一道血红。
“哈哈哈!我偏不让你如意,今日我就要让她为我族人陪葬!”
“纵使我败了,你...也不会赢!”
李胤沉重头盔下的眉头顿时紧皱,抬头往城墙上望去,恰好对上了女人向下望的目光。
李胤忍不住慌了神,那女人看自己的目光...像是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
不、不能慌。
李胤藏在盔甲里的手死死地攥紧,方才打仗时划伤的伤口又重新流出了鲜血。
再抬起头时,他又变成了那个满眼冷情的帝王,胸有成竹,笑指江山。
嘴边勾起一阵嘲讽的笑,“呼延烈,你当真是蠢得可怜!”
“你真以为一个女人就能让我停止发兵吗?呵呵,她...不过就是我闲来无事养在身边的一个玩物罢了,既然我能将她送到你们手里,我又怎么会在乎她的死活呢?”
一句句诛心的话传入阮稚的耳中,字字句句敲打在她的心上。
男人的话半真半假,她不想去猜。这么多年,她真的累了。
她的父亲为了助李胤上位,死前仍背着乱臣贼子的骂名。
哥哥为了李胤的江山率兵出征,却因为援兵久久不到被活活困死在了虹脉山脚下。
就连她的母亲也因为自己远赴南疆,最后抑郁而终。
可是纵使她付出了这么多,他依旧还是娶了妻。
呵呵...她这一生何其可笑!明明该死的人是她,老天却硬是让她活到了最后。
够了!李胤,如今你爱不爱我,于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这么多年原是我痴心妄想,如今梦该醒了...
就当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吧,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这辈子都不认识你。
风吹动女人素白色的衣裙,她抬起头对着城墙下的男人微微一笑。
这一笑,让马上的男人身体一震,心不由狠狠颤了颤。仿佛回到了两个人初遇之时,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整日跟在自己身后叫哥哥。
李胤的眼睛里染上了红血丝,这些年迟来的爱意与思念一瞬间开闸泄洪似的涌了上来,差点将他淹没。
这一刻,他好像知道了女孩要做什么。
下一秒,女人的身子猛地向刀靠过去,动作干净利落没有丝毫的犹豫,连拿着刀的呼延烈都没有防备。
“不要!”男人顿时额角青筋暴起,紧握着缰绳的手用力一拽,身下的汗血宝马一下子提起两条前腿,冲着天空嘶鸣。
女人的身体从高高的城墙倒了下去,重重地落在了冰冷刺骨的地上。
鲜红的血染红了女人身上的衣衫,她抬头拼尽全力想要看清男人的脸。
眼中的泪模糊了视线,终究没能看清他最后一面。
就这样吧...
李胤的呼吸一滞,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地上满身血迹的女人。
俊朗的脸上不知何时挂了泪痕。
他的身体僵硬,喉咙紧锁拼劲全力说不出一句话,只能听得到自己沉重的呼吸声。
不知过了多久,李胤整个人一下子从马上滚落下来,身后的将士吓得连忙想要上前搀扶。
可是男人不管不顾、发了疯地往女孩的方向爬了过去。
“皖皖、皖皖...别怕,少阳哥哥来了...少阳哥哥...来了。”
男人将女人的身体紧紧抱在自己的怀里,下巴紧紧贴着女孩的头。
“是哥哥错了...哥哥知道错了,皖皖跟我说说话...好不好?”
“哥哥再也不会把皖皖一个人丢下了,哥哥来接你回家了,皖皖...跟哥哥回家好不好?”
“皖皖,别丢下我一个人。我只有你了...我只有你一个人了!别丢下我,求求你...”
那天,一向杀伐果断、冷血无情的大梁皇帝就这么跌坐在地上抱着怀里的女人,嘟囔着要带她回家,一遍遍哀求。
然而,怀里的女孩再也没回过一句话。
“哈哈哈哈...”
男人忽然仰天大笑,笑声传彻九霄掩盖了眼角的泪。
“杀!一个不留!”
一声令下,大梁士兵瞬间冲破城门,里面打斗声、哀嚎声不断。
城墙底下,李胤就这么一直抱着怀里的女人,好像自己一松手,她就真的会离自己而去一样。
他想起当年她和自己的对话。
少女娇羞中带着期待,问自己,“哥哥,你...你以后真的会娶我吗?”
当时他是怎么答得呢?
“当然,我要你当我李少阳唯一的妻!”
他终究是负了那个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小女孩,所以,皖皖,这是给我的惩罚吗?
这个惩罚太重了,能不能换一个?
只要你醒过来,江山给你,后位给你,我的命给你。
去他妈的江山,去他妈的家族,这些我都不要了,我只要你一个好不好?
“皖皖,南山的桃花开了,我带你回去看,好不好?”
李胤抱着女人站了起来,“皖皖,别怕,哥哥这就带你回家,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永宜五年秋,施行国丧,举国上下皆着素衣,皇帝大病,卧床不起数月。
第二年,皇帝废后,后宫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