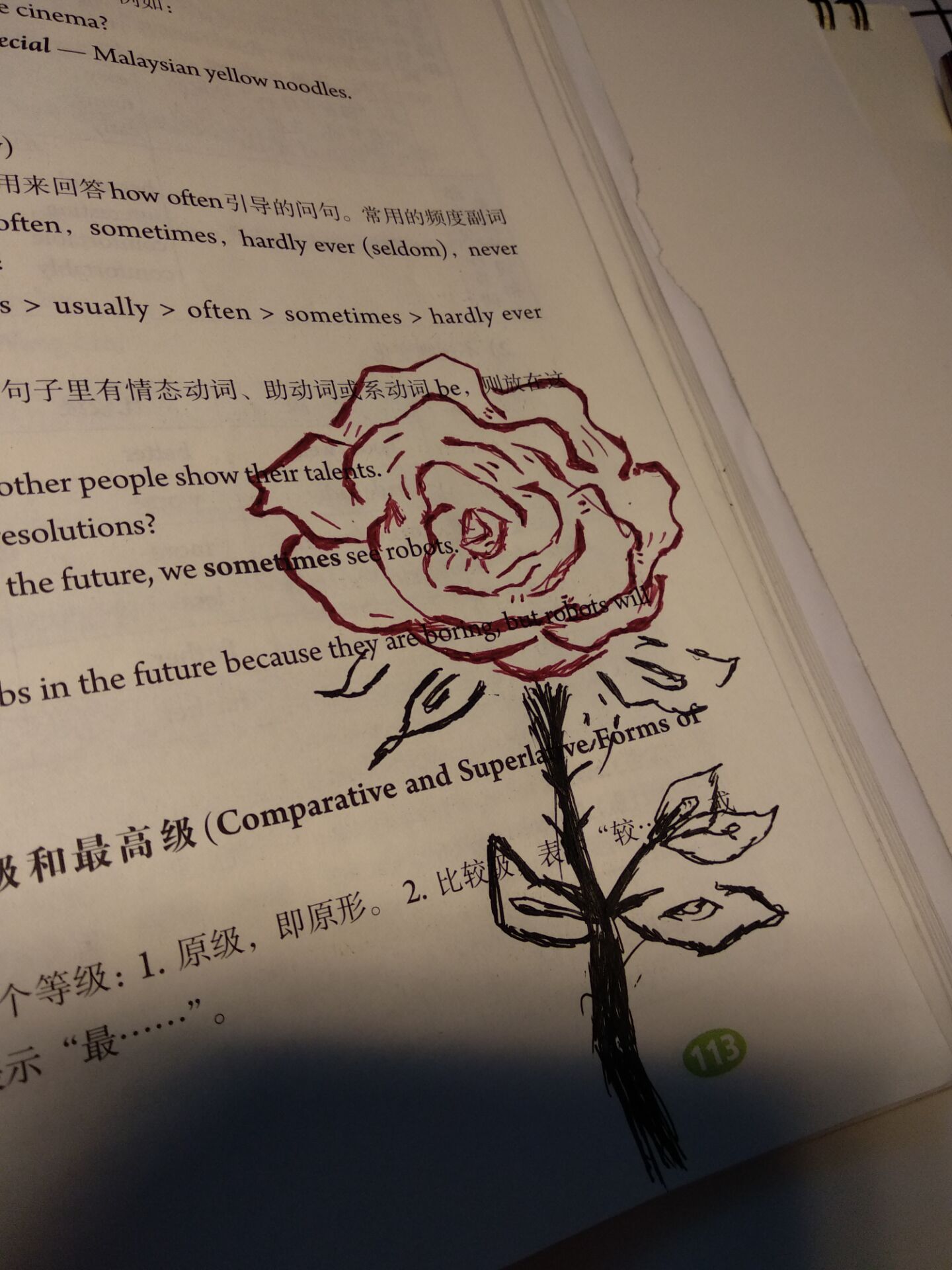尧舜净,汤武生,桓文丑旦,古今来几多角色;
日月灯,云霞彩,风雷鼓板,天地间一大戏场。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初的长安城已然有了初夏的燥热。
甜水井大街二十二号付家大院的青砖院落里,一袭白衣的陈凤良舞动着一把太极长剑,在清晨微光中剑若霜雪、秉气凛然,动作间足不沾尘、轻若游云,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周身银辉、须眉冉冉,浑身透出壮年人才会有的温润飘逸。作为长安城秦腔锦绣班班主,当他闻听到国府要将长安城改名为西京市、预备为战时陪都筹建的消息后,心中便敏锐预感到,不久的将来,全国各大剧社为了躲避战乱,必将蜂拥长安城以求生存。眼下他最感焦虑的,是要尽快完成长安秦腔界“五社合一”这件心头大事,以期应对变幻不定的时局和即将到来的乱世纷争。
陈凤良自觉年事已高,从锦绣班创始人晋长隆手中接过班主之位,已有数十年光景,锦绣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两代人的苦心经营,已从原来游走荒村僻壤、求衣索食的野班子,进驻到素有盛名的长乐坊大剧院,跻身为长安城赫赫有名的正俗社、青衣社、益民社、三易社五大剧社之一。德高望重、技艺精湛的陈凤良,又被五大剧社公推为长安秦腔界名誉总社长。从锦绣班进入长安城那天起,弟子冯其中便再三央求师父,同意将锦绣班更名为锦绣社,也好与其他四社名望对等,陈凤良却迟迟没有答应,因为他心里有着更为长远的想法。
这些年来,从各个秦腔班社残酷竞争、相互博弈中,陈凤良深切体悟到,如果想让千年秦腔艺术绵延有序传承下去,绝不能仅靠一家独大,更不能狭隘地只为锦绣班的发展思谋筹划,而是五大剧社必须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在这纷乱不堪的世道里存活下来。放眼当下的长安城,东西南北的剧社已然纷至沓来,以往的长安梨园行固有格局逐渐模糊,重新洗牌的帷幕已经悄然拉开。秦腔虽为本土剧目,倘若别省剧种班社像潮水般涌入长安城,势必会上演一场新的更大规模、更加激烈的梨园竞争大戏。
自从国府预备将长安城定为陪都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后,全国各地达官贵人、巨商名贾各色人等已经云集而来,带来的是福是祸、是悲是喜,或许只有上天知道了。而这一切的发生,使得陈凤良内心深处隐隐不安,他总感觉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还有自己所处的梨园行即将有大事发生。
陈凤良当然是位睿智亦有远见的梨园中人,他把眼前的情势看得清清楚楚,舞台戏院从来都是当下社会的晴雨表,更是政治经济的提线木偶,尽管他很不情愿如此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自己所处的梨园行,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陈凤良曾经数次努力撮合“五社合一”这件大事,可到头来,美好心愿屡屡化为泡影,这让他的心常常在沉默中黯然神伤。
把长安城秦腔社做大做强,何尝不是历代秦腔人的梦想。陈凤良始终难忘恩师晋长隆临终前对他的叮嘱,要想把散兵游勇式的秦腔人黏合在一起,既不能靠官,亦不能靠商,只能依靠梨园行同心共德的力量。胸中怀有千丝万缕心绪的他从衣怀里摩挲出一块玉佩,专意放在掌心久久抚摸着,这是块脉理坚密、古拙名贵的蓝田玉,阳光下透出质厚温润的泛青色光泽,玉佩雕工甚为精当绝巧,中央赫然镌刻着“高风峻节”四个行笔庄重的文字。
陈凤良也不清楚此物件究竟是从哪朝哪代秦腔班主传承而来,只知这是自己接任锦绣班班主之位的前夜,师父晋长隆郑重其事交予他的,并说了一句令他毕生难忘的肺腑之言。
“世人皆说我们梨园中人轻佻浮浪、薄情寡义,岂不知祖师爷早有‘高风峻节’四个字,用以教化规劝历代弟子们,要做个有风骨节操的梨园人。万望你能从此怀玉在身,日日心向往之,行必能至。”
牢记恩师的谆谆嘱托,加持古玉佩上“高风峻节”的梨园信条,陈凤良带领锦绣班奋发图存近乎十载,终于凭借过硬的功力,一路绝尘唱进了长安城。遥想当年锦绣班进城首演《游西湖》吹火绝技一鸣惊人之后,那场场一票难求的情景,似乎依然历历在目。尔后,锦绣班摸爬滚打、一鼓作气,接连以《三回头》《游龟山》《赵氏孤儿》《窦娥冤》四本全剧,稳稳当当奠定了行内地位。
这些年,声名显赫的锦绣班除了依靠繁音激楚、热耳酸心,使人血气为之激荡的表演功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班主陈凤良身上有着凝聚人心、德位相配的人格威望。如今锦绣班声名鹊起,师徒众人个个意气风发,然则陈凤良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踌躇和迷茫。
早晨的阳光透过院落一棵偌大的梧桐树,斑驳的光影投射到青灰色的地砖上,晨露微湿的高墙边,一株丝瓜藤蔓郁郁葱葱地生长着。这是一处清幽古朴的院落,原本是一户家境殷实的付姓人家的宅院,后来家道中落,锦绣班唱进长安城后,陈凤良就买下了付家大院,自此,锦绣班总算在长安城有了落脚之处。晨练后的陈凤良习惯坐在茶桌前斟饮数杯功夫茶,享受着每天中难得的一刻安宁,在这份安静中,他会把每天纷乱如麻的事情梳理个明明白白。但今天的这份宁静,已被刚才一丝细微的开门声打破了,他知道寒梅已站到身后。
寒梅是陈凤良最为得意的女弟子,她不仅是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名角,而且练就一身轻功,特别是她深藏不露的飞刀神技,百步之内可以分毫不差地命中目标,并且百发百中从不失手。付家大院的后门,只有寒梅和徒弟冯其中进得来,冯其中进门往往是大动静,寒梅却心细如发,每次进门时都是轻手轻脚,生怕惊着师父似的。
陈凤良清楚听到寒梅那丝慌乱的喘息声,心里猜到肯定有事发生了。他飘然起身,盯着寒梅那双略有不安的眼睛,声音无比低沉地问道:“是青衣社要退出吗?”
寒梅轻轻地点点头说:“师弟让我赶紧过来告诉师父,昨天夜里,杭州来的越剧班主陈竹君,再次拜会了青衣社社长杨元厚,两人一直谈到后半夜,天快亮时陈竹君才离开杨宅。消息是今儿一大早,杨社长的女儿‘九岁红’偷偷跑到咱们锦绣班晨练场告诉师弟的,结果被青衣社的人发现要押着回去,师弟不放心就跟着过去了。”
陈凤良听罢,一只拳头重重地砸向椅背,随之仰头望着天空中明媚的阳光长舒口气道:“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你不要慌张,马上把你师弟叫回来,这时候千万不能再生乱子。”
寒梅又急迫地询问道:“城里到处都在疯传,日本人要从潼关打进来,国军撑不住了,所有人都往关内跑,师父觉得这是谣传吗?”
陈凤良望着神情惶惑的寒梅,只是苦笑着淡淡说了一句:“无论怎样,唱好戏才是我们的本分。”
就在两人说话间,冯其中气喘吁吁跑进来,随手将大门和后门全都关闭,然后“扑通”一声跪在陈凤良面前说:“师父,现在情况已是很明朗了,杨元厚就是想要坐头把交椅,这才和越剧社开始拉扯上,他无非是想攀附长安城的江浙沪籍政商势力,以求壮大自己实力,从而把您取而代之。请师父别再顾忌我和‘九岁红’这层关系,该咋办就咋办,弟子认为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冯其中的这些话,近乎是从喉咙里吼出来。
陈凤良何尝看不清楚杨元厚玩的这手“一箭双雕”。想起前不久,他俩私下见面时,杨元厚竟然赤裸裸要挟自己,要么让冯其中迎娶自己女儿,要么他来做长安城秦腔总社社长,杨元厚压抑了半辈子的胸中怨气,似乎终于寻见了发泄机会。
但是,陈凤良深知秦腔剧社首任总社长这个位子何其重要,此人不仅要有膺服众望的品行,还需有重整旗鼓、引领秦腔人行大道、做大事的能力。从陈凤良内心来讲,他宁可让正俗社赵兴怀来担任总社长职位,也不想让性情粗爽而又变通不足的杨元厚上位。这些年里,他与杨元厚屡有摩擦,并非他对其本人有什么天然成见,更非外界所猜疑是因为自己贪恋此位,而是真正为了给长安秦腔人选出一个好的当家人。
在这场选拔“当家人”的较量中,陈凤良有时不得不顾及弟子冯其中和杨元厚女儿‘九岁红’这份感情,但他定然不会拿秦腔社的未来当筹码、耍儿戏,如果因为宠溺弟子的这份感情而淹毁了秦腔剧社的利益,这是陈凤良万万不能接受的。冯其中是自己亲手带大的得意弟子,他从来就不像个儿女情长之人,陈凤良也正是看到弟子身上这些特质,才会不失原则地选择与杨元厚抗争到底。
随着年事渐高,陈凤良心里愈发清楚,无论锦绣班还是整个长安城秦腔剧社的未来,迟早属于冯其中和寒梅他们这代年轻人,或许到那个时候,自己才能真正得以心安。望着眼前这对他最为欣赏的男女弟子,陈凤良纷乱的心绪稍感安慰,他认定在眼前动荡不安的局势面前,自己有责任让长安秦腔在即将到来的残酷竞争中聚拢壮大起来,这也许是冥冥之中天意所定。再说了,放眼当下的长安梨园行,能把人心涣散、七零八落的各个秦腔班社合并一起,除了他陈凤良有此把握,恐怕真的再难觅得其他胜任之人。
陈凤良缓缓走到中堂屋八仙桌旁的香案边,用鸡毛掸子轻轻拂拭锦绣班老班主晋长隆画像上的尘灰,抬头沉吟挂在墙壁的那两首自己最为喜欢的诗文条幅。
一首是:
坠泪闻歌第几场,
西安又遇殷桃娘。
万千粉黛无颜色,
化作迷离扑朔装。
连着第二首诗文是:
连宵相约看桃娘,
顾曲周郎枉断肠。
最是月明如水夜,
长安市上听秦腔。
陈凤良沉吟片刻后,旋即转身说道:“其中,今天你就去分头拜帖通知正俗社赵兴怀社长、益民社罗增荣社长、三易社胡淑曼社长,还有青衣社杨元厚社长,明早九时共聚长乐坊大剧院议事厅,就说有要事商议;寒梅,你马上给我备车,我要去书院门沈金书会长家。”心情极度复杂的冯其中与寒梅双目对视,他俩望着师父背过的身影,心中清楚意识到,又一幕好戏即将在长安城梨园行上演。
清晨的书院门一片冷清,这里是长安城最具风雅流动的街市,街口矗立着一座古韵十足的高大牌楼,牌楼上方镌刻着“书院门”三个金色颜体大字,青石铺砌的街道两旁是一排排青灰色古旧建筑,长安城但凡是博文好古之士,平日里往往喜欢留恋于此。街道远处传来一连串“嘚嘚嘚”的马蹄声,那是陈凤良乘坐的红绺白马小篷车到了。
“我刚要去您府上拜访,没想到您老亲自登门了。”沈金书面带谦逊微笑,连忙迎接陈凤良落座客厅上位。陈凤良举目四望,只见偌大的屋梁墙壁上挂满了京剧脸谱、烛台、灯笼、扇子、手绢等物,桌案上文房四宝一应俱全,旁边的水旗、风旗等京戏常用砌末摆置得整整齐齐,一间客厅活脱脱像个小小的京剧舞台。
神情凝重的陈凤良一开口,便将弟子冯其中早晨带回的消息告诉沈金书,并说在这个关键时刻,他非常担心“五社合一”这件大事,极有可能再次化为泡影。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往后时日里恐怕更难办成。
沈金书何尝不知,此事一直是陈老班主耿耿于怀的心事,他苦心孤诣奋争数年,一边煞费苦心经营壮大锦绣班,一边用尽心血化解班社旧有的恩怨壁垒,继而不厌其烦地给梨园同行拆解融通五大班社合并的必要性。番番苦口婆心背后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团结长安城所有秦腔人,共同联手发展壮大秦腔曲艺。如今,好不容易收拢人心可以谈论聚合了,又偏偏遇到眼前这般混乱的动荡时局,于陈凤良而言,如果一生谋划的事情,最终功亏一篑,对于他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金书啊,你是从北平城来的京剧泰斗,也是咱长安曲艺工会会长。因此,凡事我肯定是要与你提前商量的。不瞒你说,我已让其中去通知其他四社明早议事,想说什么你该是知道的。”陈凤良神色焦灼,连续呡了几口茶水继续说道。
“昨晚,杨元厚与越剧社陈竹君又见面了,你也知道,他俩之间拉拉扯扯,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也想好了,成立秦腔总社这事,如果再这样没完没了拖延下去,不知又会生出什么乱子。所以我一大早跑到你这里来,就是想再次表明心迹,无论我和杨元厚矛盾有多深,都不是我和他之间的个人恩怨,绝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影响了秦腔总社成立这件大事??????”说到激动处,陈凤良不由地咳嗽了两声。
“明早开会之前,我必须把实情说与你,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只等秦腔总社哪天能顺顺当当成立了,我也就死能瞑目了,它日命赴黄泉见到师父,也算是有个交代了。”这番情真意切的话语,听得沈金书心里怪不是滋味。性情开朗、为人坦荡的陈老班主,今天能吐出这些肺腑之言,着实令沈金书百感交集,他深知长安秦腔界确实到了该规整的时刻了。
对于沈金书而言,至始至终都难以忘记早年初到长安城时,陈老班主给予他的鼎立支持与帮助。尤其是怀想起先辈们当年那场“徽秦合流”的壮举,每次都能让他感到心潮澎湃、热血在胸。
那还是在大清初年,北京城戏曲舞台上还是昆曲一家独大。这时候,秦腔艺人魏长生带领秦腔双庆班由陕入京,只演出了一场《滚楼》,便轰动了京师。秦腔曲目众多、唱腔委婉、技艺精绝的特点,赢得了戏迷们的满心欢喜,又因为秦腔祖师魏长生扮相俊美、嗓音甜润,魏氏双庆班旋即被誉为“京都第一”。
秦腔在京城的迅速崛起,直接导致了昆曲的日渐衰微。彼时,京城六大名班之大成班、王府班、余庆班、裕庆班、萃庆班、保和班的演出,逐渐变得无人问津。为了讨得活口,很多艺人纷纷搭入秦腔班谋生。
一晃到了乾隆五十年,清廷忽而以魏长生的表演有伤风化,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师演出,并将魏长生逐出京城。自从,魏长生被迫离京,秦腔开始一蹶不振,秦腔艺人为了生计,又纷纷搭入后期崛起的来自安徽的徽班,形成了徽、秦两腔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过程中,徽戏广征博采,吸取诸家剧种之长,特别是将老派秦腔技艺完美融入徽戏当中,同时广泛取纳秦腔唱法、表演技巧,并进行大量剧本移植,为徽戏形成以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光荏苒、世事变迁,到清末年间,徽戏又逐渐开始没落,很多人改调京腔学习京戏,至此之后,徽戏、京戏又合流为一,逐渐形成了“联络五方之音为一致”,以皮黄为主、其他曲腔兼唱的京剧。
正是源于京剧与秦腔的这份历史渊源,沈金书向来笃定秦腔是京戏的先祖,很是尊重秦腔在长安城的特殊地位,又因他是长安曲艺界共推的行业会长,为了让各派剧社取长补短、各展所长、共同发展,沈金书也是呕心沥血,特别是碰到当下这样的纷乱时局,更不能任由梨园行四分五裂,成为帮派势力利用的工具。
这些年来,沈金书鼎力相助陈老班主共同筹划,好不容易将秦腔九门十八派的混乱局面,归置到今天的五大剧社,眼看就要五社归一,千年秦腔艺术总算迎来了合力奋进、重现辉煌的机会,而这个机会,不知是多少代秦腔艺人梦寐以求的。所以,沈金书铁定心思,誓要帮助陈凤良完成这最后一刻的壮举。
看到沈金书坚定支持自己的态度,陈凤良的忧心散去了许多。恍然间,他感觉到了屋里闷热,不知何时,一身青衫已被汗水浸透。沈金书吩咐弟子拿来一把蒲扇,并搀扶陈凤良坐到庭院石桌前喝茶。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隐约听得门外大街传来一阵阵喧闹声。
沈金书手拿蒲扇,缓缓踱步庭院中央,沉思片刻后说道:“我让弟子任欣荣代表长安曲艺工会,明早随你一起去长乐坊大剧院。你只管按照我俩以前议定好的去做,不必顾忌杨元厚的态度,只要五社中有三家同意,我即刻再以工会章程确认‘五社合一’通过,你看如何?”
陈凤良清楚沈金书暂不出面,先由弟子任欣荣出面前往,这样做的道理起码考虑有二,一则首先顾及了杨元厚的面子,不去刺激他,并给了他下台阶的机会;二则又能在合并原则和章程上,不给任何人留下挑刺的地方。因此面对沈金书的安排,陈凤良连连点头认可。
其后,沈金书坦然说道:“我个人建议,还是再争取一把杨元厚吧。他和您老在台面上争了一辈子,不服气您我看是假,主要还是斗一口气。即使杨元厚再不仁义,青衣社还有我们三十多号梨园子弟,他们可都是无辜的。所以,我想让任欣荣今晚再去青衣社找他好好谈谈,您看如何呢?”陈凤良热眼近望着眼前这个仁厚敦义的汉子,越发觉得当年坚定支持沈金书担任长安曲艺工会会长是最正确的选择。
就在两人说话间,任欣荣已闪身进来,只见他身穿一袭长衫,气质忧郁且身形消瘦,眉宇间透着几丝青涩与稚气。此人不仅是沈金书的得意门生,还是他的义子,这个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已经是长安京剧社社长了。
沈金书叫来弟子,就是想当面给陈凤良吃颗定心丸。而当任欣荣得知秦腔界明天召集会议的真实意图后,当即欣然答应师父,晚间他会独自去见杨元厚。末了,沈金书和陈凤良又一再让他捎话给杨元厚,劝其不要再受旁人蛊惑,多以秦腔曲艺未来为重,别再坐地自划、随性而为。任欣荣只管默默记住两位师父叮嘱的每句话。
辞别沈金书后,陈凤良感觉浑身轻松许多,一路碎步走出书院门,坐上了街口停靠的红绺白马小篷车,顺眼看到书院门牌楼两侧柱子上刻着“碑林藏国宝,书院育人杰”的醒目对联,心中滋味可谓是五味杂陈、不可言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