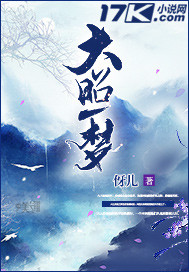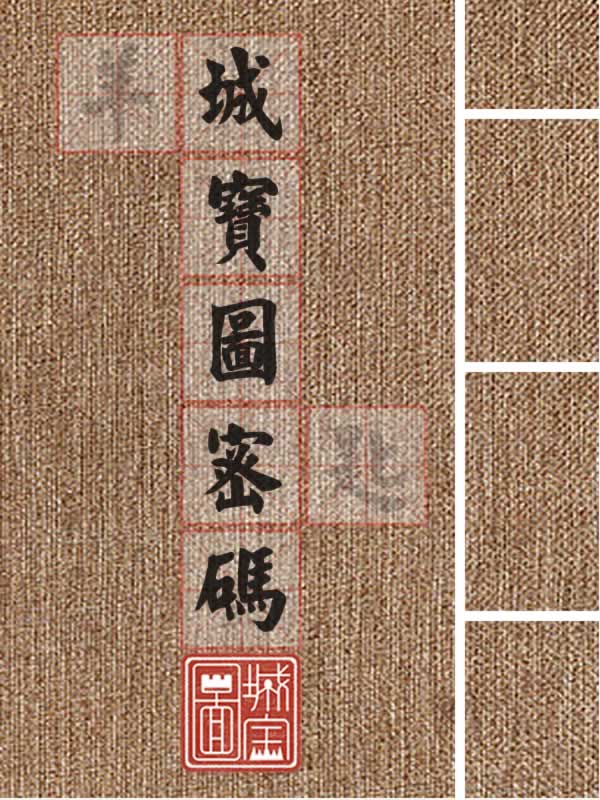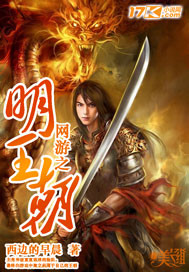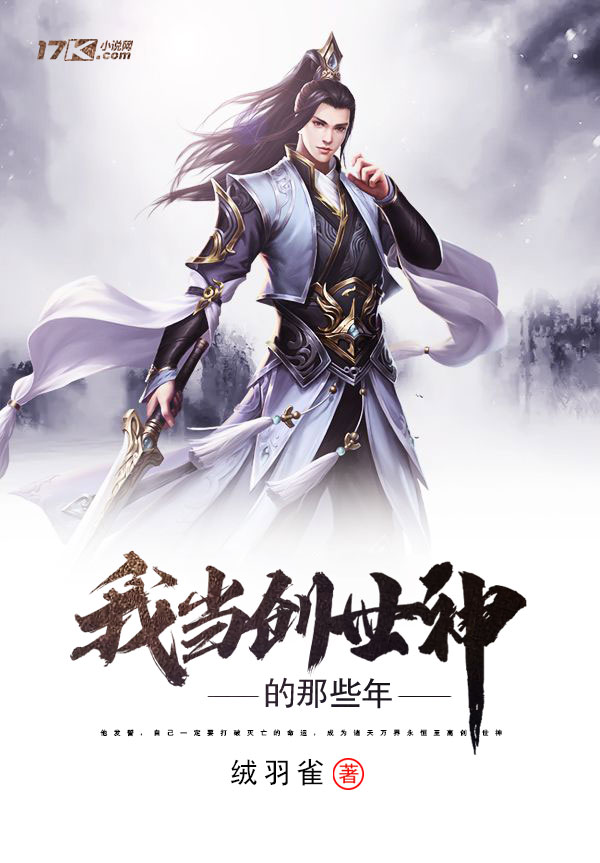孟承珩黯然神伤,颓然自放。他逃出了宫躲在太明寺后山那一间让他一生都放不下的院落中。
孟承珩想做个仁君,做个明君。
想让大简政令清明,国富民强,盛世延绵,像父皇一般,像太祖一般。但他又想做个平凡人与心上人过着平凡的日子。
左顾右盼,摇摆不定,注定一事无成。
念桂娇对他的声讨控诉字字诛心,而朝堂局势云谲波诡,政党对立,坊间更是谣言四起百姓对长公主远嫁和亲愤懑,对他钟情戏子不齿。与榕姝决裂,与老臣离心,亲近之人尽是别有用心之人,世人皆欺他,轻他,侮他。对自己身处的困境,孟承珩实则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他想不明白为何总是事与愿违。
房门轻叩,师太悟缘声音从屋外传来:“陛下,可愿与贫尼一道礼佛静坐,明心净念,烦忧自解。”
孟承珩跪坐佛前虔诚礼拜,双手合十,神情肃穆。悟缘师太站立一侧灰青法衣持珠念诵,静如止水。
青灯古佛,香烟缭绕,万物俱静,余钟磬音。
“方才礼佛时,朕向佛祖发问该如何忘却执迷之事?朕曾不止一次如此发问,究竟该如何是好?”
“不必忘记,只需放下。七情六欲,贪嗔痴念,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放下”二字让孟承珩陷入了沉思,谈何容易。
佛前送走一红尘痴迷之人,又迎了另一人。
李隐躲在佛堂暗处不知有多久,自一处隐蔽角落走出:“永王妃,未经他人之苦,何能劝他人放下。”
“施主,贫尼皈依佛门多年,俗世种种已然成空,望施主以贫尼法号相称。”悟缘师太对凭空走出一人的诡异情形倒是不意外,好似早就知有人躲在暗处多时。
李隐入了佛堂既没有礼拜也没有焚香,听了悟缘师太的话反而抬眼打量了佛像许久。
“众生皆苦,佛心慈悲,普欲度脱一切众生。可我本世间一游魂,且看这纷扰人世间更添烦扰,佛不度我也无妨。”
“佛不度人唯人自度。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皆有佛性,本已成佛。若众生执迷自甘沉沦苦海,自弃自累,世间便无佛也无神。” 看透红尘的悟缘师太再次开口时带着不可追忆的沧桑感慨,有了世俗的情绪:“施主,长得很像贫尼的一位故人。”
“师太,方才称自己遁迹空门前尘往事皆成空,怎还会记得故人样貌?若还记得,又怎会忘了你口中的故人是何种下场,您的夫君永王又是何种下场?”
昔日之人提起昔日之事,勾起了李隐心中最痛,他也不复以往的淡然自若,带着几分讥讽冷笑。
悟缘师太自初识李隐起便觉得这年轻人眉眼神情让她极为熟悉,而后此人有意提及当年之事,悟缘师太便有了几分把握她的故友之后尚在,就在她的眼前。
常伴佛前,片刻的神伤不足以迷失,悟缘师太轻捻佛珠,人在眼前一字一句却如自从远处传来的超脱佛音:“缘法即灭,自当归于虚无。贫尼半生青灯古佛,往昔前尘如烟。半生辛甜愁苦,余生无忧无怖,足矣。”
李隐一开始压抑发笑而后便不加遮掩哈哈大笑:“踩在至亲骨肉的尸身上苟且偷生,师太大觉可轻叹一句‘缘灭且随风去’。而我不行,我能活下来,便定要让那被掩盖的尘封往事重现于世人眼前。”
李隐神情渐渐变得扭曲悲怆,“罪人之后可安然无恙活得荣华自在,坐拥江山。而无辜枉死之人早已化成黄土,侥幸活下来的人一生煎熬苦痛。你们出家人口中的因果轮回,善恶有报在何处呢?”
所有人都不知道李隐就是个装成常人的疯子。棋局已成,他无惧身份暴露,或者说他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份大白于天下,叫世人都莫要忘了忠勇为国的樊家当初是如何家破人亡!他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以天子自居,粉饰太平的帝王之家灰飞烟灭。
李隐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控,随即又冷静下来。
悟缘师太不禁叹息:“施主,年纪尚轻,年华大好,何苦如此?”
“执迷不悟的又何止我一人,师太天天在佛前捻珠念诵是为忘却前尘往事还是为自己忏悔赎罪呢?”李隐别有深意的继续说道,“太明寺日夜都有护城军看守,当今圣上还在寺中守卫更是森严。师太,就不好奇我是如何潜入?寺中有条密道,师太不会不知晓。当年师太明知可以通过密道逃命,为何将月粟娘子带往后山?你扪心自问那一刻是不是打算让那女人一尸两命,好报你夫君的仇。”
提及当年太明寺失火一事,面对李隐的质问悟缘师太面如死灰,她声音颤抖问道:“你究竟还知道什么?”
“火是我命人放的,原本也不想取了那女子性命,托师太的福倒是让这出戏更加精彩。”李隐掩饰不住的轻蔑和不屑:“这世间本就是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一姓天下,陷害忠良。连出家之人都是道貌岸然之辈,口口声声说教的‘众生平等,回头是岸’不过如此。你们有何颜面劝我不要偏执己见。”
李隐走后,悟缘师太放下了手中的念珠独自在佛前瘫坐了很久,一瞬间她老态尽显,口中呢喃:“‘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君不在月华流照何人?”
斗转星移二十载,那时她还不是“悟缘”,她是永王妃胡照君。
年近半百她犹记得自己夫君服毒自尽那日的情景,是她亲手将丈夫还带着余温的尸首送到了崇光大殿前。
身披素缟长跪于大殿前,无论任何人说任何话她都听不见,她也不在乎。
“你还不到三十,还有大把好时光,好好活下去。”她如他所愿独自一人也好好地活着,心安理得地活着。
如果不是那叫月粟的女子来到了太明寺,或许她胡照君可以自欺欺人了此余生。那一日鬼使神差,是试炼是磨难。
一心佛国,一心地狱,一念善恶。
她将人引向后山,可当那女施主真的难产之时,她后悔了。
一念之差她便坠入了无间地狱,犯下了忏悔千年都难以洗清罪孽。
这些年来,她明白冥冥之中早有定数。她日日在后山无字牌位前诵经,愿意付出余生为月粟母子二人的冤魂超度。
李隐今夜颇有兴致,或许是撕下了他人惺惺作态的假面莫名爽快吧,他在私宅院中自饮自酌,祝白乖觉地在一侧静候他的差遣。
“恶念即起,便一恶到底。既已作恶,又半途知返,愧疚五内,余生不安,这才是庸人自扰之。”
“主子,太明寺那老尼姑该如何处置?”祝白问道。
“本以为背负同样的血海深仇,我还能多一个盟友。罢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寻人仿了她的字迹写封遗书,我这故人之后给师太加个以死谢罪的戏码,也算全了父辈与永王之间的情分。”说罢,李隐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念桂娇在内狱中如何?大简皇帝可有查不出什么?”
“审讯当夜,娇娘她已在狱中服毒自尽。了断前她已认下全部罪责不曾透露半分有关您和永王的消息。”
听闻念桂娇的死讯,李隐丝毫不觉地手中一颤,稳了稳心神他转而满上了空杯。“她想要的,我会让她得偿所愿。”
太明寺的悟缘师太悬梁自尽于自己的禅房内。
一时间坊间对这位皇室宗亲出身的师太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与当年永王谋反一案有关,又有人称据可靠消息是师太自己破了戒愧对佛祖才自行了断。
孟承珩下旨撤了凤鸾宫外看守的禁卫军,允了榕姝出宫祭拜悟缘师太。榕姝来到寺内祭奠完,还是决定去趟后山。
秋意正浓,尽染山岚,一寸断阳,一阵秋风,惊得满山红叶款款纷落如蝶。古道之上皆是零落,落叶成殇,静幽苍凉。
百年公孙树,满地银杏黄。金叶映青砖,岁岁复年年。孟承珩负手于身后在树下站了良久,等待着某人。
榕姝踏上铺满银杏叶的石阶,来到孟承珩身后。孟承珩回身递给了榕姝一封信,是悟缘师太的绝笔信。
读完信榕姝才知晓原来当初月粟之死另有隐情,照悟缘师太信上所说当年是宁王孟承琛命人纵火,而师太为了报自己夫君冤屈自尽之仇阴差阳错成了帮凶。
纠葛不清的恩恩怨怨,令无辜之人受尽牵连。回想起记忆中那女子脆弱又坚定的面容,榕姝心中不禁一阵唏嘘,陷入了沉默
孟承珩已是满眼通红:“我一直当六年前那场火是意外,孟承琛手段够狠。”
榕姝倒吸了一口凉气,她顿时明白悟缘师太这封绝笔书信无疑会成为孟承珩与孟承琛兄弟二人反目成仇的导火 索,劝道:“三哥,逝者已逝。只要二哥真心悔过,前尘往事就一笔勾销吧。我们兄妹四人不能再手足相残了。”
“姝儿,你可知你总是用这般局外人的口气劝我,叫我心寒。孟承琛为了皇位杀我妻儿,可有把我当过手足?在他孟承琛眼中我不过是低他一等的庶出,只配俯首称臣。他背地里的谋划真当我全然不知,我念他是兄长多次旁敲侧击他毫不在意。他要夺位,好啊,可以冲我来!还有一个帮凶竟恬不知耻地劝我放下,看来你们都当我是傻子,觉得我软弱可欺罢了。事已至此,我不会再退让。这窝囊皇帝我也当够了。”
孟承珩深深吸了口气,“杀人偿命,无人可以例外。”
孟承珩和榕姝兄妹二人争执不休,谁都不曾留意有人影在暗处一闪而过。
孟承琛派去太明寺的探子回来了,听了探子回禀孟承琛眼睛眯成一条危险的缝:“本王大功将成,老尼姑在此时往本王身上泼脏水,究竟是何居心?”
李隐开口道:“王爷,先不管那悟缘师太是何种用心,圣上已有心结长公主大婚后必定是会处置王爷。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
“按计划行事,本想留他孟承珩一命,现在看来他必是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留着也是个隐患。”
冬月初四,大雪,榕姝和亲之日。
这一日终究还是来了,自和亲诏书布告天下,自被囚于寝宫到绥国皇太子入简以来,榕姝终日浑浑噩噩。
远嫁绥国,若说心中没有半分畏惧,倒是自欺欺人了。
宫中的老嬷嬷为她一下一下梳着长发,口中念念有词。榕姝看着铜镜中面色苍白,双眼空洞的女子竟是如此的陌生。
回想过往,她开始为自己的婚事谋划之时属意婉姐姐的胞弟,那是她理想中的夫婿。若是能成,虽不曾有过动情,但贵在能与之相敬如宾。
后来,当心有所属才明白想要携手一生并不需要筹划,她想嫁的人自己的心早已做出了选择。为之牵肠挂肚,为之奋不顾身,为之放弃一切又想拥有一切。
而如今,罢了。
那从不认命整日为心中所求不停前进的女子,此刻却也屈服于弄人的天意。囚于笼中的雀鸟无论作何挣扎都难逃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