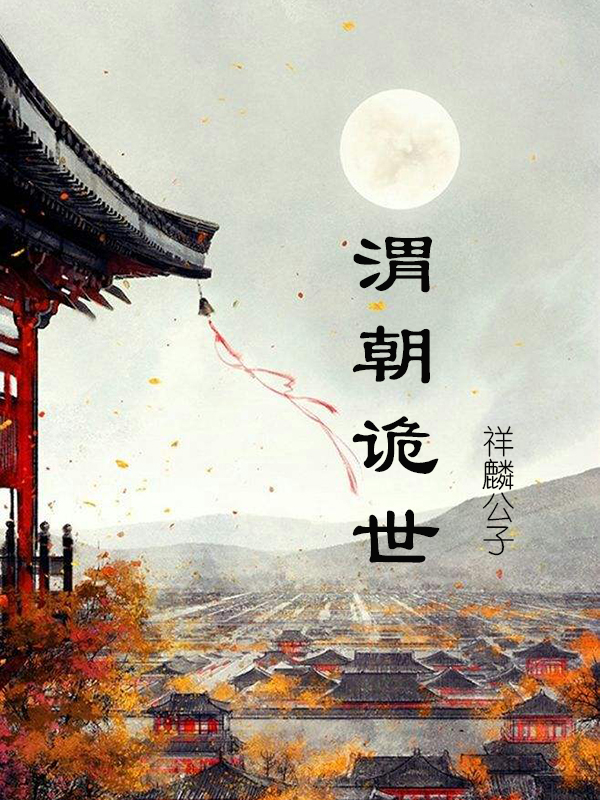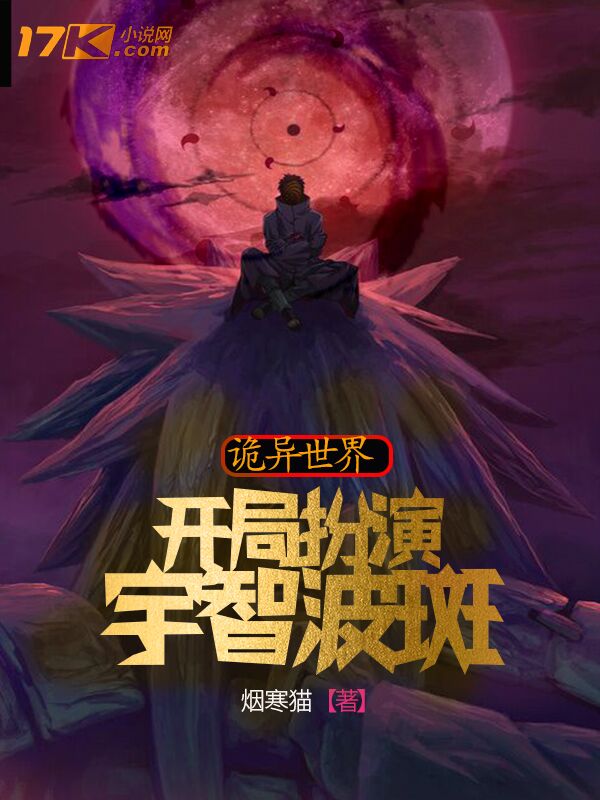“奴婢会将此心曲记成曲谱,烦劳公子命名。”声音虽沉稳、优美,质子听来却心上一惊,急忙说,“多谢你的好意,但还是别记下来了……怕是祸。”玄普依旧清浅一笑,“不怕。无论有何祸事,我等三人在此,自会一一化解掉。”质子犹豫着看向晋威,见其笑着点头,这才觉得心安,聚神一想,轻声道,“明湖念月……如何?”成崊点头,“此名颇有意思,居然有三个月亮,看来公子心仪之人必定与明月颇有渊源。”然后见晋威瞪了自己一眼,便抬手轻拍了一下红润的嘴唇。
“好,那么奴婢这就去记下‘明湖念月’。”玄普起身走至门口,质子紧忙又嘱咐了一句,“记归记,万不可让陛下知晓、听到此曲。”玄普转回头笑道,“只要此屋内四人不说,也便无碍,待那谢财迷之妹来了,晋威自会盯住她,想必也是无碍的。”晋威蹙眉道,“人家不似谢太医,并非多事之人,嘴很紧,你别乱判。”玄普与成崊默契地对视一眼,这一回笑得更为玄妙,果然令晋威心烦,刚欲发作,人已不见了,再一转头,成崊也不见了。“可恶。”晋威罕有地红了脸,动了气。
此后,几个人各自自在,互不干扰。到了日落渐黄昏之时,秦芗来了。“陛下命奴婢来问问,质子大婚在即,可还有需要调度之人,准备之物?”其实答案显而易见,不过是晋威后背无人盯视,陛下会时常派人过来问候问候,查探查探。别人做此事晋威必定生厌,秦芗若来,惜泓居上下只会欢喜,无人会有脾气。真是一步妙棋。质子暗想。
“一切都好,荀夫人之物陆续都已送来,现已安置妥当。”晋威按流程作答,然后忽而转了个弯,问道,“那柄南疆宝剑如何安置了?”秦芗倒也实说了,“陛下听闻舒将军家传宝剑被毁后,一直找不到趁手之剑,便将此剑赐予他了。”晋威这才释然道,“那么此剑也算不亏了。”
晋威独自送秦芗出门,临别之际,秦芗低声提醒道,“大门之外兵都撤了,看似无人看管,其实周遭日日有人盯防,且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因此,凡来此处之人、之事依然在陛下法眼之内。”其实晋威心中早有预料,不过还是很感激挚友的提醒。“你在陛下身边也要敛着锋芒,焉公公虽气派大度,然而人人都有嫉妒心,谁也无法免俗。”其实道理秦芗都懂,但也同样感激挚友的提醒。所谓过命之交,当是如此。
清晨如期而至,光色颇为艳丽。明日便是质子大喜之日,这也算作是吉兆。惜泓居内四人一兽早早醒来,各自忙碌。质子照例独自练剑,看客们个个都是顶端的剑客,因此手上的工作都不必停,偶尔看看便知质子何处精彩,何处犯了错。待质子将一套剑法操练完毕,三个人方才围聚过去,点拨一番。质子向来谦和、聪慧、勤奋,算作是师者最为欣赏与喜爱的那类学生,所以确实值得点拨。用过早膳,四人一兽又各自自在,互不干扰。众人暗想,此等生活若能运作一辈子,也是精彩无比的。只是,在皇帝法眼注视之下的惜泓居,不可能一直安享此等生活。
未时,临安公主策马而来,茂盛乌亮的发丝梳成朝云近香髻,身穿桃粉窄?上衣,下配胭脂大裙,甚为小巧、精致的绣鞋隐约可见。众人迎出来施礼,公主利落地下了马,请质子以外之人只管自在忙去,随行的潘略则接过缰绳,回身安置好骏马。
“没想到您会来。”质子脑子一木,便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本宫来此,已得父皇恩准,所以别傻站着,本宫口渴,要品茶,听潘略说敬亭绿雪甘甜美妙,那么你来奉茶吧。”质子只得遵命照办。书房一如从前,老气横秋,欢白见了天仙般的厉害人物,只顾缩在榻上,佯装睡着。公主喃喃道,“它倒是精明,知道此时若不装睡,本宫必然要折磨它,以替太子出气。”质子没有应声,只顾专注地做茶,因知晓公主极通茶道,不敢有半分闪失,以免让其失望、败兴。
某一刻,有些分量的五足银熏炉映入公主眼帘,炉香袅袅,颇有意境,公主略一蹙眉,知晓此物必然是二弟所赠,莫名上了脾气,抬起绣鞋猛地用力踢出一脚,熏炉自然就倒了,她便高声道,“熏炉倒了,果然不稳,需来个人,将此无用之物送去荀夫人的书房。”守在外头的几个人互相看了看,谁都不愿意进去,果然是厉害人物来了,惜泓居整个儿都怂了。
最终连同潘略在内的四个人齐齐进门,抬了熏炉,又都迅速退了出去。此时茶也成了,公主品了一口,然后挑眉看了看质子,罕有地,质子没有回避,目光对接良久,谁也没有败下阵来。“本以为有出色人物伺候着,做茶的功夫早就退步了,没想到一如既往,不,更胜从前了。”质子为公主续茶,然后轻声回复道,“心想着也许还有机会为您奉茶,也就不许自己退步。”
公主心上一暖,话也有了真实的情绪,“从此,除本宫外,不许你为任何人奉茶。”质子没有一丝犹豫,郑重答应道,“好。”公主进而又说,“本宫送你熏炉,你既然放置于书房,就不准再放别人送的任何熏炉,金的、银的,甚至御赐的也不行。别的任何东西也都是同理。”质子再度郑重地答应了。“这一回你错了,熏炉便也倒了,本宫很不爽,要罚你。”面色严峻,不似玩笑。“好。”质子依然看着公主的眼睛,轻声说,“任凭您处置。”面对这样的执着凝望自己的质子,公主感觉心跳极快。“罚你让出古筝,本宫要抚奏一曲。”质子稳住声音,又一次回复了一字,“好。”
公主进入琴室之前,对质子之外的四人道,“从此刻起,你们聋了,待本宫离开之前,惜泓居四下都必然是聋的……否则,要你们何用?!”四人心领神会,便出去分别镇守住惜泓居的四面八方。琴音起,质子立即就听懂了“清宵邕睦”,他奋力压制着情绪,不言不语,闭目倾听。
往时美好在头脑中不断浮现,只是,如梦一般的日子,眨眼之间就都过去了……“答应本宫,明日起,做个好郎君……明年春天,务必要做个好父亲。”质子知道应该说出“好”字,却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只好点了点头,凄然一笑,泪水的滋味儿灌满了咽喉,好生酸楚,却也终究没有自眼眶里涌出泪来。
公主走后,质子在琴室里独坐良久。无论如何,清宵邕睦算是成了,古筝也让公主尽兴抚奏了,虽然心之圣地依然没有立碑,但人要知足,对,他点了点头,这样便好,此生足矣。
夜里,院落之中已建好了一座青布幔的青庐,装扮起来十分喜庆。质子走进去,坐了坐,闭目联想明日成婚的情形,然后缓缓睁开眼,走出青庐,看着月光下的晋威,轻声道,“我想喝杯酒。”晋威本想说不可以,看着质子之眼,又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三杯,不可再多。”质子笑了笑,说不喝了,便回房睡下。晋威心上有些后悔,觉得此夜对于心有所属的质子来说,必定是非常难熬的。喝上一点儿酒,让嗓子和胃里都暖一暖,让心里说不出的话能借势倾吐一番,多好。但无论如何,他不能后悔,不能心软,质子前途远大,此刻正是紧要关头,绝不可再生枝节。
此时,叶明仙正在闺房中读一本书,其实心思也不在书上,毕竟明日要做质子之妻,未来的变数谁也说不准,一切全凭自己。若是不如意,也要咬着牙往前走,无论如何绝不再回头了,所以,此夜必然是今生在叶家度过的最后一夜,即使再漫长,她也愿意一点一点地慢慢度过。
忽而,门被敲响,她收好书,开了门。父亲站在眼前,用一双略微外凸、刻薄的眼睛看着自己。她愣了片刻,还是施礼,将父亲让进门来。“明日就出嫁了,你自己选的路,以后好歹都要自己扛着,别给叶家添麻烦。”明仙轻声答应着,面上没有任何情绪。
“别觉得这个家怠慢了你,没给过你什么,琴棋书画我都没拦着,你得到了跟你大哥一样的机会和条件,果然也比他强出百倍、千倍。”叶太尉以罕有的温和口吻道,“所以,拿出叶家赐你的本事,好好相夫教子……别只顾恨这个家。”尾音有些颤抖,叶太尉也不想掩饰,缓缓起身向外行走。“父亲多保重,若偶尔下朝得了空,还请来惜泓居看看女儿。”明仙说罢,跪地叩拜了父亲。父亲侧身看了看,轻声说,“好。”便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大婚之日,天气甚为晴好,叶明仙择良辰而至,与质子依礼完婚。直到夜里,明仙才借着灯光看清了郎君的脸庞,果然是世间难得一见的英俊人物,不由地柔声问,“以后,我唤您‘修郎’可好?”子修点了点头,“那么,我唤你‘仙娘’吧。”然后两个人陷入沉默。僵持了一会儿,明仙再度开口道,“修郎,早些休息吧。”子修轻声说,“好。”然后扭捏了一下,补充道,“放心,明年春天,我们会有可爱的孩子。”明仙心头一暖,道了谢。接下来两个人便成就了花好月圆的一夜。
清晨醒来,夫妻互相看着对方,都有些脸红心跳,然后彼此照应着起床洗漱,牵手出来与众人相见,大家顺势施礼道贺,夫妻俩也紧忙还礼,赏了每个人一些钱。接下来人们各忙各去,质子照例练剑,明仙见过兄长练剑,倒是凶猛激烈,却也毫无章法可循,公主曾戏言此乃泄愤之举。如今见过了郎君舞剑,只觉得如行云流水一般潇洒利落,变化无穷,少女之心怦然跳荡得慌乱无比。一套剑法操练下来,一个时辰眨眼间就过去了,明仙整个人仍然在境界里,如痴如醉,拔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