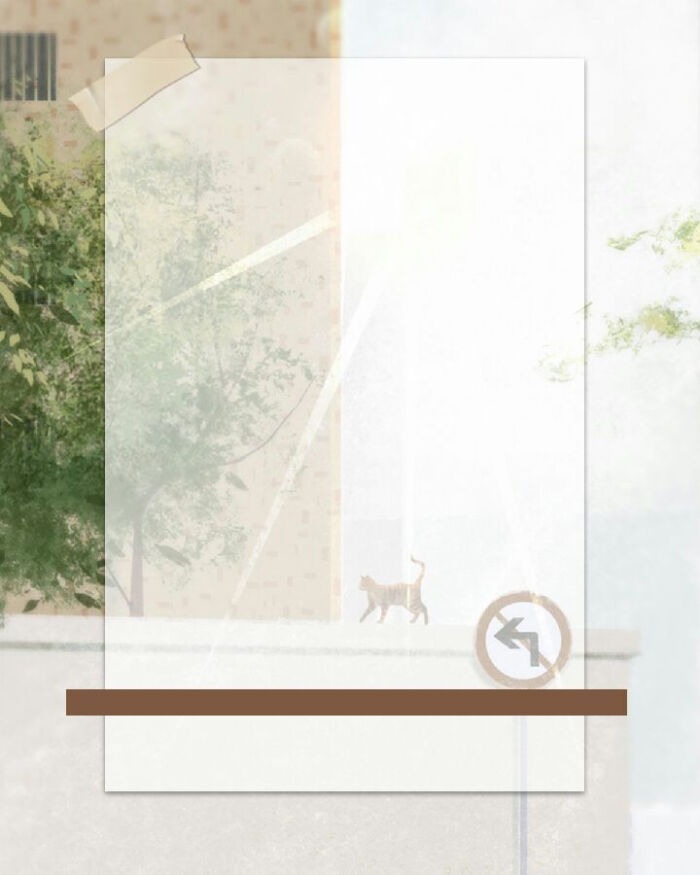第一章、午夜凶案
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上没有月亮,仅有的几颗星星,也像醉汉的眼睛一样无精打采、暗淡无光。小河边,一片黑黢黢的杉树林后面,隐藏着一座神秘的宅院。此刻,宅院里寂静无声、漆黑一团,所有的人都已梦游仙境……
这是一座宽阔的宅院,有前后两进院子。前院正面是厅堂,两厢是主人的房间。后院东边一排房屋,是下人的住处和厨房,西边一排是仓库和磨坊,最后面还有一座挺大的牲口棚。
这会儿,静谧的后院中,突然响起了“吱哑”一声,一扇木门被推开了,从屋里走出来一个瘦弱的男人。他披着一件破旧的布衫,一边系裤带一边嘴里嘟嘟嚷嚷,也不知说些什么。此人名叫狗娃,是这户人家的伙计。他睡眼矇眬、倦意未褪,系好裤带后,像个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地朝牲口棚走去。
倏地,黑暗中蹦出个活物,兀自从他面前窜过,把他吓了一大跳。接着,传来一阵“喵喵”声。狗娃骂了一句该死的猫,摸黑走进了牲口棚,来到马厩跟前,用火石点亮挂在廊柱上的风灯。昏暗的灯光下,只见几匹马静静地站在马槽旁,嘴里缓慢地嚼着草料。
狗娃穿好上衣,伸长胳膊,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然后走到草料棚那儿,抱起一把干草走了过来,放进了马槽。他忙乎了一阵,就“噗”地一口吹灭风灯,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路过茅房时,拐了进去。
茅房里更加黑暗,恶臭难闻。他走了几步,就停下来,不敢再往前走了,生怕一不小心掉进粪坑里。他解开裤带,掏出黑将军,对着暗处乱“嗞”一气。排泄完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动作迟缓地系着裤腰带。睡意像潮水一样漫上来,他的脑袋耷拉下来,似乎又要睡着了。接着,猛然一惊,嘟噜地骂了一句,迅速系好裤带。他转身刚要走出茅房,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嘭”的一声。声音虽然不大,但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却清晰可闻。
狗娃哆嗦了一下,摸黑走到窗前,朝外面张望。茅房这扇很小的窗口,正对着院子。院子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恍惚间,好象有一些黑影在晃动,影影绰绰的。正觉疑惑,忽然,从屋顶上跳下来几条黑影。不好,有贼!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在他的脑海中划过。他刚想大喊抓贼,可是,就像有一只有力的大手一把掐住了他的脖颈,叫喊声被窒息在喉咙里。因为,黑暗中突然燃起了一只火把,把整个院子都照亮了。火光之中,只见院子里黑压压地站满了人,他们都穿着紧身的缁衣,手里握着雪亮的钢刀。显然,他们不是一般的盗贼,而是一群打家劫舍、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看见这帮从天而降的强盗,狗娃吓坏了,身体就像狂风中的苇叶一样颤抖不止。他目光发直,眼前的一切好像对焦不准的镜头,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
手握火把的强盗大概是个头儿。他不知说了句什么,强盗们立即四散开来,杀气腾腾地奔向各间屋子,毫无顾忌地踹开门,径直闯了进去。接着,屋里传出人被刀砍的瘆人惨叫……
狗娃看见,从自己住的那间屋里冲出一个人来。不用细瞧,他就认出是与自己同住一屋的管家。管家跑出来后,看见站在院子中间手持火把的强盗,愣了一下,转身朝茅房这边跑过来。茅房旁边有一扇小门,通往外面的菜地。强盗追了几步,将手中的钢刀掷出去。钢刀像一只飞标一样,精准地扎进管家的后背。管家惨叫一声,像一截朽木一样,一头栽倒在地上……
强盗擎着火把跑过来,用火把照着,察看管家死了没有。这时候,狗娃看见,强盗的脸上有一道骇人的刀疤。这条刀疤又长又宽,斜亘在他的脸上,从鼻梁一直延伸到左边的嘴角。
强盗伸手去拨扎在管家背上的钢刀。刀插得很深,他不得不用一只脚踩住尸体,才将钢刀拨了出来。他转身欲走,却注意到了旁边的这间茅房。
强盗迟疑了一下,朝茅房走过来。狗娃颤抖得更厉害了,三十六只牙齿捉对儿厮打。正在这时,院子那头传来一个强盗的叫喊:“大哥,东西找到了!”强盗听见召唤,顾不上进茅房察看,连忙跑了过去。
这时侯,其他的强盗陆续回来了,许多人手中的钢刀都在滴血。众强盗在刀疤脸的指挥下,砸开一间屋子,闯了进去,将里面的箱子都搬了出来,又一箱箱地往前院抬去……
他们动作神速、配合默契,功夫不大,箱子就搬完了,人也没了踪影。院子重新陷入可怕的黑暗和寂静之中。狗娃僵立在那儿,像冻住了一样。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战战惊惊地从茅房里走出来。他奓着胆子朝管家趴的地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怕冷似的哆嗦着。他呆立了片刻,转过身,朝前院方向走去。
整个宅院都遭受了一场浩劫,所有的房间门户大开。他摸黑走进老爷太太的房间,在门口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他坐在地上,伸手一摸,摸到了一个柔软的身体,同时,还感到手上沾上了一些黏稠的液体。他记得屋角有个烛台,连忙爬起来,碰碰撞撞地走过去,摸到台子上的蜡烛和火石,点燃了蜡烛。烛光下,他发现自己的手上满是鲜血。他举起蜡烛照着,发现躺在门口的是丫环小翠。小翠穿着亵衣,侧身躺着,整个脸都被长发遮住了,身体下面有一大滩猩红的鲜血。
狗娃惊骇地瞪大了眼睛。停了一下,他缓慢地朝里间走去。里间是老爷太太的卧室。进去后,他看见老爷太太穿着内衣,都被杀死在床上。老爷临死之前,大概想爬下床去,结果半个身子在床上,半个身子在床下,就像一截树枝似地挂在那儿。
狗娃的手抖动得越来越厉害,手指一松,蜡烛掉在了地上,火苗被摔灭了,屋里又陷入到浓稠的黑暗之中。他的神经再也绷不住了,双手抱着脑袋,狼嚎般地大吼一声,转身冲出屋去。在门口,又被小翠的尸体绊了一跤。他爬起来,不顾一切地朝大门口跑去……
第二章、菀陵大户
烈日当空,树荫匝地,金风送爽,花香馥郁。官道上,偶见一两个农夫荷锄而行。路旁绿油油的麦苖已经开始抽穗,长势喜人。这时,两匹骐骥一前一后地奔驰而来,马上的两名骑士打扮精干、风尘仆仆。前头的那位,年纪约莫四十七八岁,身材健硕、气宇神威,两道粗黑的眉毛下面,一双虎目炯炯有神。他就是河南尹李膺。跟在后面的是他的贴身侍卫。
两人轻装快马,疾速而行。越往前走,官道上的行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只见前方出现了一座古朴陈旧的城廓。侍卫一夹马刺,催马上前,与李膺并齐马头,说:“大人,菀陵县城到了。”李膺一扯马缰,让马速放缓,仰起头看了看日头,道:“快晌午了,咱们进城打个尖吧。”
菀陵县城虽然不大,却繁华热闹。穿过城门,眼前便是一条宽阔的大街,街上行人熙攘,两旁店铺众多。他们挑了一家饭馆,将马缰拴在门前的石磴上,走了进去。
店小二热情地招呼他们,将他们引到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后,李膺点了几个热盘和一斤馒头。小二记下后,殷勤地问道:“两位客官,不来一壶烧刀子?”李膺摆摆手道:“不用了,我们还要赶路。”小二转身欲走,李膺叫住他,让他找人给门口的两匹马喂点草料。
功夫不大,饭菜上齐,两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时候,旁边一桌客人的谈话声飘了过来。一位客人说:“哎,你们听说没有?昨夜骆家庄发生了一桩凶杀案,骆员外全家被杀,财宝也被洗劫一空……”
“哦,有这样的事?”
“对,我也听说了。今天一大早,王县令就带人去了骆家庄,我娃他舅也跟着去了。听他说,十几口子,一个活口也没留下,太惨啦!……”
“谁这么大胆子,敢犯下如此凶案?”
“还能有谁?准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他们也许早就盯上了骆员外家的金银财宝。看来,太有钱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李膺将手中咬了一半的馒头放下,站起身,走到旁边那张桌旁,对一位身穿青布衫的老者拱手道:“这位老伯,敢问你们说的骆员外是什么人?”老者抬头瞅了他一眼,道:“你不是本地人吧?”李膺答道:“小可只是路过此地。”老者点点头,道:“那就难怪了。骆员外在咱们菀陵县可是大名鼎鼎,他住在县城十里外的骆家庄,是方圆百里之内首屈一指的大富商,家里金银珠宝堆成了山,没想到却引来贼人的觊觎,遭此灭门大祸……”
李膺回到桌旁,抓起馒头继续吃起来。侍卫压低嗓音说:“大人回乡祭祖,来回尚不足一月,没想到刚踏入河南尹境内,就赶上这么大的凶案。”李膺瞥了他一眼,催促道:“快吃,吃完咱们去县衙。”
两人风卷残云般地将饭菜扫光,结了帐,走出饭馆,解开马缰,踏蹬上马,掉转马头朝县衙方向驰去。
河南尹,原来叫河南郡。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建都洛阳,将河南郡改名为河南尹,辖京城洛阳和附近二十一个县,菀陵县便是其中之一。管理河南尹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叫河南尹。
李膺和侍卫来到菀陵县衙,衙役进去通报后,王县令亲自迎了出来,将他接到大堂上。分宾主坐下后,王县令有些不解地说:“本县昨夜刚发生凶案,尹府大人远在洛阳,如何这么快就知晓了?”
李膺笑了笑,说自己是回乡路过菀陵,在街肆上听说的。王县令恍然大悟,点了点头,道:“卑职一早就率领县衙一干人去现场勘察。凶案大约发生在昨夜子时至丑时之间。骆家九口全部被杀。大人也许已经知道了,骆家颇有资财,凶徒显然是冲着黄白之物去的。”
李膺问:“可找到了目击证人?”王县令摇了摇头,说:“未曾寻得。”李膺皱起了眉头,不解地:“凶徒杀人掳财,动静颇大,怎么就没有被乡邻发现呢?”王县令连忙解释道:“大人有所不知。骆家庄除了骆员外一家外,虽然还住着数十户村民,但他们的房舍离骆家宅院相距较远,最近的也有一里左右。加上凶案发生在午夜,村民们都已熟睡,所以并没有人目睹。只是有一位乡邻早起拾粪,路过骆家时,发现大门洞开,院内一片狼籍,觉得蹊跷,进去察看,发现尸首后才报了官……”
李膺听了,沉思不语。王县令试探地问:“大人要不要去现场踏勘一番?”李膺点了点,道:“也好。”于是,王县令带了几名衙役,与李膺一起骑马去了骆家庄。
骆家宅院的大门口,站着两名持械的皂隶看守现场。几个人进了院子,首先来到西厢房,这儿停放着骆家九口的尸体。李膺蹲下来,掀开死者的蒙面白布,一一查看。死者都是被刀砍死的,其状惨不忍睹。验看完尸体后,李膺又去每个房间逐一查看。
他们走进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的门锁被砸坏了,里面却空无一物。王县令说:“这间屋子大概是骆家的库房,歹徒们抢走的金银财宝肯定都放在这儿。”
李膺察看了一番,问王县令:“王大人,依你所见,这件凶案是何人所为?”王县令语气谨慎地说:“凶徒杀死骆员外全家,又抢走了全部财宝,看这阵式,好像不是一两个人。目下世道不靖,徐州青州等地盗贼蜂涌而起,他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卑职猜想,会不会是那些强盗听说了骆员外的名头,派出同伙潜入菀陵县来杀人劫财?”李膺思考片刻,点了点头道:“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真是那些强盗所为,他们远道而来,大白天带着那么多财宝在官道上行走,多有不便,一定会找地方隐藏起来。所以,卑职已经派出人手,前往各地的客栈、酒楼和马车店探察,看能否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李鹰又勘察了一阵,才跟王县令一起离开了骆家庄。这伙凶徒十分狡猾,现场并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一行人回到县城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菀陵县出了这么大的凶案,却没有一点线索,李膺放心不下,决定在这儿留宿一夜。他跟王县令道别后,离开了县衙,与侍卫一起去街上,找了一家客栈住下。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李修,在汉安帝时担任过太尉。父亲李益,曾任赵国相。李膺二十一岁时举孝廉,先后担任过青州刺史、渔阳太守,后转任乌桓校尉,负责在边境上抵挡鲜卑人。他身先士卒,不避箭矢,率领军队多次打退鲜卑人的进攻。后来,因遭权臣排挤,被免去官职。
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鲜卑人大举侵入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桓帝不得不重新启用李膺,让他担任度辽将军。李膺到达边塞后,鲜卑人慑于他的威名,主动把掳掠的男女汉人,全部送回了边塞。从此,李膺的声威远振边域。
李膺品格高尚,赋有清誉。他被免去乌桓校尉后,曾回家乡教书,门下弟子常达千人。凡被他接纳的士人,唤作“登龙门”。东汉硕儒荀爽曾去拜谒李膺,因为给他驾车,回来后高兴地对人说:“今天才得以给李君驾车。”他被人仰慕到如此程度……
次日一早,李膺又去了县衙,与王县令一起研究案情。快到中午时分,王县令派去搜查客栈和马车店的差役陆续回来汇报情况,其中一名捕头提供了这么个情况:他手下有一名捕快,在街上碰见了一个熟人,那人名叫狗娃,以前是骆员外家的伙计。王县令一听,连忙问道:“那名伙计现在何处?”捕头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我听那名手下说,狗娃只在他眼前晃了一下,就不见了。”坐在一旁的李膺敏锐地说:“这个人很重要,他很可能是这件凶案的唯一线索。”王县令一听,立即布置人马全城搜索,一定要找到狗娃。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时辰后,狗娃终于在集市上被找到了。
原来,狗娃因为害怕,逃离了骆家。他自小父母双亡,举目无亲,一直在骆家当伙计。如今没了栖处,便去了县城的集市,想重新寻个雇主,讨口饭吃,不想却被衙役找到,带到了县衙。
王县令立即升堂问案,李膺坐在一旁观审。狗娃被带上堂来,跪下叩头。王县令目光威严地瞅着他,问道:“你姓甚名谁,以何为业?”狗娃还没有完全从昨夜的打击中恢复过来,面色苍白,神情萎靡。他愣了一下,才哭丧着脸说:“回老爷,小人名叫狗娃,是骆家的伙计。”王县令问:“你既是骆家的伙计,骆员外全家被杀,你是如何逃过前夜一劫的?”狗娃便将自己半夜起来喂马,躲在茅厕之中的事说了一遍。
“你既藏在茅厕之中,可曾看清贼人的面目?”
“小人看见凶贼有十几个人,可是天太黑,没看清他们的模样。”
“那么,你既目睹凶案过程,为何事后不报官?”
“这……”狗娃一时语塞。
王县令冷笑一声,道:“莫非你与强盗勾结,里应外合,杀人谋财?快说,你分得了多少金银?现在藏于何处?”狗娃吓得连连叩头,喊道:“小人冤枉,小人确实不认识那些强盗……”
王县令一拍惊堂木,大声喝道:“大胆顽徒,不动用大刑,看来你是不会说实话的。来人!拶指伺候。”狗娃一听要动刑,吓得魂飞魄散,连忙道:“老爷,小人愿意说,小人什么都说。”
王县令一摆手,让衙役退下。狗娃道:“老爷,小人之所以不敢报官,是因为此事迁涉到本县的一个大人物,小人怕说出实情后,官府治不了他罪,反倒连累了小人。”王县令紧盯着他,问:“什么大人物?”狗娃咽了口唾沬,吞吞吐吐地说:“小人……小人认识那个领头的强人,他……他就是羊元群老爷府上的管家刀疤脸。”
王县令一听,倒抽了一口冷气,瞪大眼睛问:“你看清楚了?”狗娃点点头,语气肯定地说:“绝对错不了!最近,羊老爷跟我家老爷有所交往,刀疤脸曾随羊老爷去过我们府上,所以小人认识他。”
王县令让衙役将狗娃带下去。当堂上只剩下他和李膺时,李膺见他满腹心思的样子,不解地问:“凶案已露端倪,王大人为何反而愁眉不展?”
王县令犹豫了一下,才道:“凶徒的首领既是羊元群府上的管家,那羊元群与此案恐怕难脱干系。看来,这件案子甚为棘手……”
李膺皱起眉头问:“这羊元群到底是什么人?”
王县令说:“大人到任不久,自然不知此人。这羊元群是菀陵大户,不仅家财颇丰,而且还与皇上沾亲带故。他的外甥女就是宫中的田贵人。他以前与大人一样,也是二千石的高官,曾在北海郡当过太守。但是,他贪脏枉法,搜刮民财,弄得民怨沸腾,声名狼藉,遭到了上司的弹劾。可是,皇上宠爱田贵人,并没有治他的罪,只是罢了他的官。回乡之前,他将公家的财物掳掠一空,连郡署厕所里的精巧之物都被他拿走了。回乡的时候,他带回来的财物足足装了二百多辆马车,全部都是金银绸缎。我听说,他还与宫中的宦官交往甚密……”
李膺怒目圆睁,攥紧拳头在案几上猛击一拳,斩钉截铁地说:“无论他是什么来头,如果此案真是他指使人干的,我李膺绝不会放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