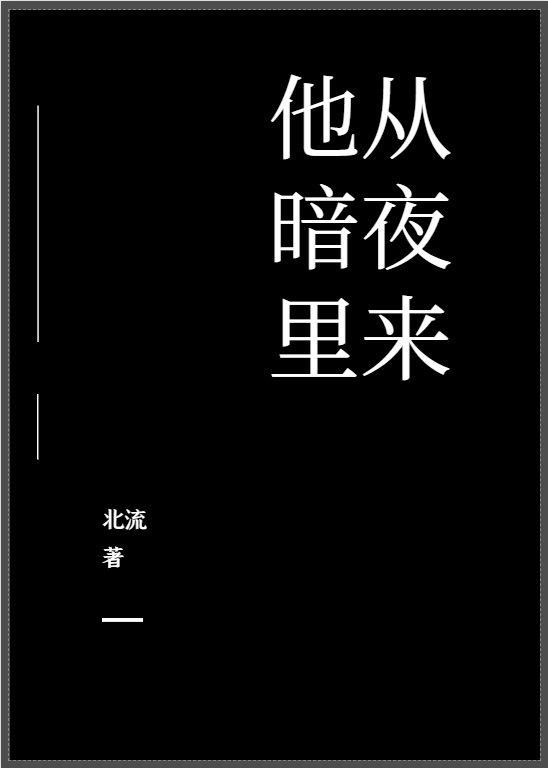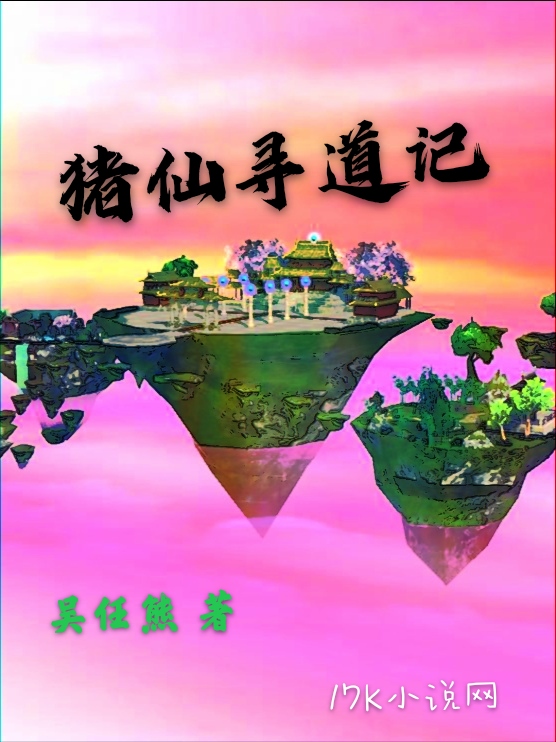自从纪宁出院以来,欧景逸每天都往安安家里跑。
“哟,小逸又来啦。”安安刚睡醒从房里出来,便看到欧景逸买的早餐已经放在餐桌上了。见纪宁的房门开着,便饶有兴致地看着屋里的两人。
欧景逸反倒没有一丝害羞的神色,理所当然道:“我们家小宁醒得早,需要我来照顾。”
纪宁恍然间看到安安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从前那样的羡慕与嫉妒,很安心的笑着。
安安说:“明明是你自己想小宁,还找借口。”
这回倒是纪宁害羞起来:“安安,你快去吃早餐啦!”
“打发我走?”虽然意犹未尽,安安还是妥协道,“好吧,好吧,我回避,有了异性就没朋友的。你们小两口继续。”
安安扣上房门之后,纪宁就忍不住娇傎起来:“你不去公司么?每天都在这儿呆上一整天。”
欧景逸宠溺地捏了捏她的鼻子:“陪你还不好?”
“好是好,可你也该工作啊。”鼻子被他一捏,顿时幸福感充释着纪宁的全身。
“那不就得了,下午安安他们办聚会,我怎么能不来呢?”欧景逸笑得很温馨,好像自己长久以来苦苦寻求的那种感觉在瞬间袭来,就像闪电骤然照亮整个的天空,忽然发现自己想要的幸福是那样的真实。
纪宁拿他没办法:“是啦是啦。”
欧景逸从包里拿出粉色的小绒盒,深情地对着纪宁说:“小宁,我知道我很笨,不会说情话,但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我买了戒指。”
纪宁脸上潮红潮红的,笑着眼前紧张到不行的男子:“买了戒指,然后呢?”
“然后,你可不可以戴上?”他将盒子打开,银色的镂花美得不可方物。
纪宁轻轻点头,低着头偷笑,任他拉过自己的手,缓缓戴上那代表承诺的戒指,她的眼里映出这个男子清澈的笑脸,心便像跌进了一大堆棉花糖里,又软又甜。
安安和左迁的婚礼办得很简单,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晚饭便算作结了婚。而左妈妈那边,说什么也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毕竟她一直坚信的儿媳是吉林。于是,安安他们打算领了证便回小镇。
火车站,离别在即。人们都在告别,有哭泣,有不舍,有豪迈的一声“珍重”……
安安挽着左迁的手,俨然一副小女人样。她戒了烟,再不会半夜醒来看老电影。她曾对纪宁说,结了婚之后的那些个夜晚,她睡得很安稳,这样的安稳在遗失了那么多年之后,终于又回来了。她说着的说着,竟然喜极而泣。
腾落走上前去轻轻拥抱了一下安安,算作告别。而多年后,慢慢回想,那竟定格成为最后的拥抱。
纪宁拉着安安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面对别离,祝福的字句最难表达,因为慎重和珍惜而失却了平日的流利。她笨拙地张了张嘴,便落了泪:“到了那边要好好的。”
安安轻笑:“傻瓜,又不是不会来了。”
“我们会想你们的。”周怡插话进来。
安安点头:“我们也会的。”
“好好照顾安安。”王小加依旧是他们当中的乐天派,他打破沉重的气氛,拍着左迁的肩膀。
左迁“恩”了一声说:“到时间了,我们该走了。”
欧景逸搂着越哭越激动的纪宁:“一路顺风。”
安安和左迁摆了摆手,说着“再见”的字句转身上了火车。待他们坐定,一脸不舍的纪宁通过车窗拉着安安的手不想放开,直到火车要开动了,她才恋恋不舍地缓缓放开拉着安安的手。
安安抿着嘴笑,,眉眼弯弯,睫毛在她的眼下投下隐隐的影子:“很快就回来。”
刚说完,火车便轰隆隆地开动了,剩下的人都愣愣地站在那儿朝渐渐远去的火车挥手。
腾落只觉得心猛地沉下去又浮上来,丝丝震颤,摇曳心旌。
宿命中所有的纠缠错结想必应该已经尽数散去,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忘记他,思念已经无处可归,不如永恒地忘却。
从火车站出来,沉默了良久的腾落忽然开口说道:“我也打算离开了,三五年之内不会回来了吧。”
王小加惊讶地看着他:“为什么?”刚问出口,他便自知问得不当。
“我已经对浪漫的爱情不再渴望,只是守着一份遥远的心情。”腾落微微叹气。
纪宁抽泣着鼻子问:“打算去哪儿?”
“到处走走吧,会时不时联系你们的。”腾落站在一颗大树下,那树有苍老的皮肤,干涸的皱纹,只有上面鲜绿的叶赫开出的花海追溯着它的年轻。那是一种细碎的白紫色小花,仰头看时像是洒满了树梢的阳光,静静地依偎着树叶不说话。
周怡也很难过:“不能不去么?”
腾落微笑着摇头:“我已经决定了,今晚的飞机。”
纪宁还想说些什么:“那……”
欧景逸打断她的话,拍着她的肩膀:“不要劝了,我已经劝过了,随他去吧。”
那是纪宁出院的第二天,灰蒙蒙的天空下,洁白而柔和的雪花漫天飞舞,像狂欢的精灵,覆住了大地,散发着冷而淡的清香。
无论欧景逸怎样劝阻,他心意已决。当看到腾落看着雪花一朵一朵柔软地掉下来的时候,欧景逸就明白了,生命中送死存在着这样的阴差阳错,注定让你与相爱的冷擦肩而过。或许,腾落所需要的是逃避,即使那是弱者的姿态。
那一天雪花无声地蔓延了城市寂寞的街角。
……
“那,那腾落,你要时常跟我们联络啊。”纪宁也不知道要再说什么好。
“恩。我会的。”腾落轻点着头,他已经学会躲避,不会再迎过去,让自己的心再次受伤,而是绕一个弯,转一个方向。
腾落就这样离开了,谁也不知道,他就这么一去不回了。经年之后,当纪宁再一次回想起彼时的某段心情,好像是坐在屋顶上看风景,有风吹过心灵,吹散了那些细细的尘埃。
他活着的时候,被埋葬在坟墓里,死了,仍被埋葬在坟墓里,只留下永远无法兑现的许诺,随着累累白骨,沉睡到天荒地老。
——腾落,你要时常跟我们联络啊。
——恩,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