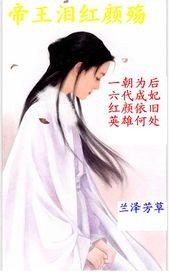这个夏天对陶渊明来说是悠哉乐哉!
晴天,走出去到南野看豆禾吐絮,到西畴看水稻抽穗。站在田埂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五脏六腑都感到爽快,连汗毛孔都透着清新。
不知什么时候身上的蓑衣重了,摘下斗笠仰脸试试,细雨落在脸上,像是有毛毛虫爬过,痒痒的。
回到家里,妻子和儿媳妇正在摘菜,菜叶上还带水珠,是刚从菜园里采回来的。坐着等待吃饭,厨房里风箱有节奏的响声和着锅碗瓢盆的交响。
最悦耳的是檐前雨滴,“滴滴嗒嗒”匀称而舒缓地敲打着芭蕉叶的声音,这声音让人心静,甚至有催眠曲的效果。
饭熟了,嫩绿的青菜看着就让人流口水。斟上一杯春酒,轻轻地呷一口,咂咂嘴甘醇如丝而下,很美的;深深地饮一杯,酣畅淋漓,很爽。
酒足饭饱后,打个嗝儿,伸伸懒腰,睡上一小觉,醒来后便是读闲书的时候。
陶渊明的五个儿子没有一个喜欢读书的;但是,雨天看到父亲读闲书,除阿舒外四个小儿子都围上来。阿通最起劲,嚷着要陶渊明读书给他们听。
儒家的“四书五经”枯燥乏味,《山海经》的神话故事有趣,《山海经图》是最有趣的,阿通读不懂文字,最喜欢看图画,听父亲对着图画讲山海经里的离奇故事应该是阿通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陶渊明同样享受着这种读书的快乐,没有功利的驱使,随心所欲给人的快乐。人的思想就像一个自由的精灵任意驰骋徜徉在另一个非现实的时空内。
读《穆天子传》陶渊明仿佛随从周穆王骑着八匹骏马,由造父赶车赴昆仑山与西王母赴会欢宴。在云霞之巅的玉台上,喝玉液琼浆,微醉之中陶渊明对王母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回到凡尘间后,只要酒喝,再让我的寿命长一些就足矣!”
阿通更好奇的是《山海经》的故事,他指着图画问:“精卫鸟是什么变的?”
“是炎帝的女儿——女娃变的。女娃在东海游泳被淹死了,死后化作精卫鸟,发誓要填平东海;所以就就飞到西山衔着木石来填东海。”
“能填吗?海那么大。”
“能,只要有恒心就能,无论办什么事只要坚持再坚持就行。”
“刑天没有头怎么能挥舞大斧、盾牌打仗呢?”阿通瞪着眼睛问。
“刑天跟天帝夺神权,天帝就砍了他的头;但是,刑天并不屈服,于是就把乳头变成眼睛,把肚脐变成口,仍然双手挥舞着大斧和盾牌。”
站着一直不说话的老二阿宣摇摇头:“怎么会呢?”
陶渊明想了想说:“女娲和刑天死后所变成的生命,既没有顾虑,也不后悔,只有壮志不变;所以就能这样。人是靠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这种力量就是‘志’!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陶渊明的这句感慨并非用来教育儿子的,他只是一吐胸中的块垒而后快。
西畴的早稻黄了,眼看再过三五天就好收割了。陶渊明一面谱料着收稻子的营生,一面安排着舂高粱米。
“爹,现在舂高粱做什么?”阿舒问。
“做什么,还用问能做什么?你爹脑子里有什么?”阿舒娘手里做着活,没好气地说。
阿舒媳妇见婆婆有点儿生气,剜了一丈夫一眼说:“爹,打算得还会有错吗?你只管照着做就是了。”
媳妇又走到婆婆身边说:“娘,您先歇会儿吧,俺爹是读书人,干这样的粗活,喝点酒暖暖身子,手脚也麻利。”
“我没有反对你爹喝酒,只是……”婆婆下面的话没有说出来。
媳妇说:“爹是明白人,咱顺着他就是了。”
“什么事都顺着他,可是他有哪一件事顺着我呢?”婆婆内心不平。
陶渊明说:“夫人,我知道辞官种田让你和孩子们跟着受委屈,我真是做不来官的呀!”
“谁怨你了?不是一样跟你下田插秧锄草吗?只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的。”
陶渊明笑着说:“不会的,不会的。”
阿舒舂高粱米回来了。
陶渊明说:“我和阿舒煮米酿酒去了。”
“去吧去吧。”翟氏没有抬头继续和阿舒媳妇收拾装粮食的袋子。
陶家的酒酿出来后,酒香飘出园田居,路人都能闻到酒香。
第一个来到陶家园田居的是陶成,还没有进柴门陶成就抽着鼻子闻香味。
“好香的酒啊!”陶成在院子喊。
“是三哥来了,馋猫鼻子尖啊,酒刚熟三哥就来了。”陶渊明的妻子笑着打招呼。
陶成已经进了院子,问:“先生呢?”
“三伯,我爹在里屋漉酒呢,您进吧!”阿舒媳妇说。
“三哥,来吧,这道酒酿得可真是好啊,进来尝尝。”陶渊明在屋里喊。
陶成进屋,陶渊明舀了一碗递给陶成。陶成捧着碗先看了看颜色,没有吭声,把酒碗凑到嘴唇上轻轻地呷了一口,咂咂嘴:“好,好。”然后一仰脖子,全喝干了。把碗递给陶渊明,说:“好酒,真是好酒。”
“再来一碗!”陶渊明说。
“来一碗!”陶成说。
又喝了一大碗。
“三哥,喝两碗行了。今晚上凑个酒局,把邻居们叫来一起好好喝顿。”
“好,那我就不走了。”陶成很干脆。
陶渊明的三个小儿子一溜烟地跑去邀请邻居,阿宣杀了一只鸡,阿舒媳妇去菜园采摘蔬菜,全家人动手一个酒局就准备好了。
一只鸡,新酿的酒,园田居里有了一个热热闹闹的酒局。
没有客套,也不分宾主,谁来谁入坐;没有祝酒词,也没有行酒令;不劝酒,也不斗酒,跟在自己家里一样;没有斯文,没有拍马溜须,心里有什么说什么。都是种田的庄稼汉,自然话题离不开春种秋收。
“陶先生,南野的豆今年怎么样?”
“陶先生,南野的豆被草赖住了。”
“是啊,先生新开垦的荒地,生荐子。”
“明年,我不种豆了,种高粱。生荐地种豆不行,今年在南野费了劲了,锄草就锄了三遍;明年坚决种高粱!”
“应该种高粱,先生你应该种高粱!高粱长起来把草就压住了,种几年高粱再种豆,那时杂草就少了。”
邻居们大声地说着话,大口地喝着酒。从南野说到西畴,从种豆说到插秧,从种麻说到植桑。说粮食,说蔬菜,说养蚕,说织布……
醉了的,歪歪扭扭地走了,没有人挽留,也没有人送;不走的,继续喝;不喝了,倒下就睡……
就这样从掌灯一直喝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