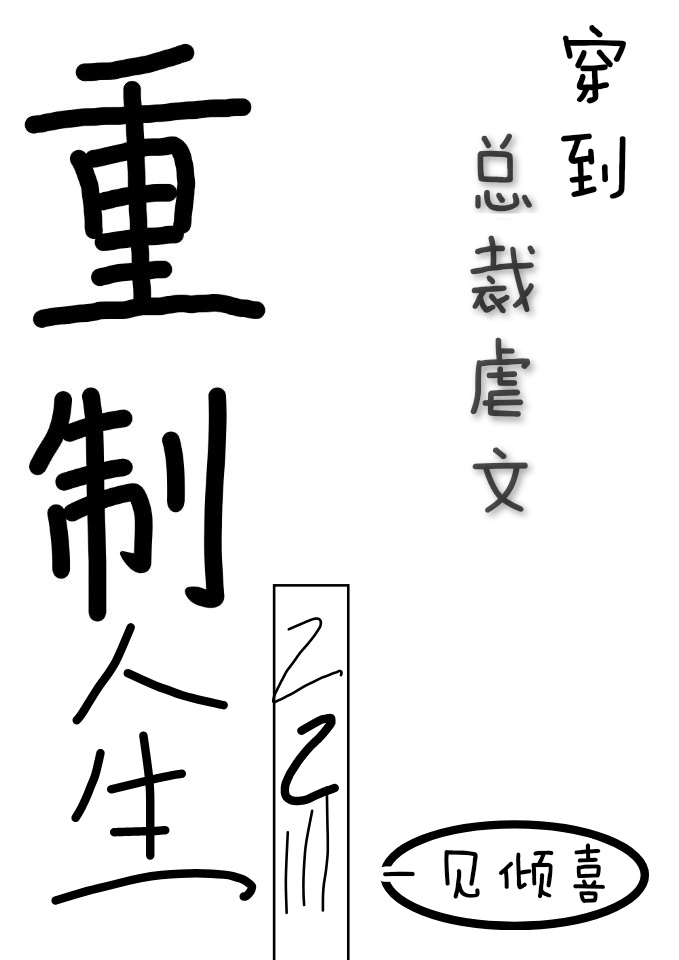少年生于东河郡太平县,此地位于国土最西南,父亲曾经为国吏,后因为不忍官场苟且之事辞官返乡,母亲未嫁前为商贾人家小姐,入嫁后专心持家。
父亲返乡为农后条件清苦无比,娘家不忍女儿受苦,接济了些银两,二人用其置了店面经营买卖,母亲从小耳濡目染生意场状况,父亲跑腿帮衬,使得店面经营得当,很有起色,并用盈余买了地盖了房,就在一切都向着美好、向往生活时意外发生了。
几个月前,太平县的驿丞神色慌张的入了家门,在父亲耳边密语着什么,父亲面色越来越沉重,传完消息驿丞就离去了,父亲独自坐在院落思索了一个晚上,还未等到天全亮便出了远门,他对谁也没言语,也无人知晓他去了哪里。
等他再次归家时身旁便多了一位老人和一个中年人,那中年人更像是老人侍从,从言行举止中可以看出父母很尊重这个老人,敬如上宾,少年很是好奇,多次询问父母老人身份,父母摇头不答,这让少年觉得老人越发神秘、诡异。
少年觉得老人神秘还有另一层原因,少年望向老人时,老人不需睁眼也不需少年言语便可猜透少年心思,少年以为老人也如杂书中所述会法术,所以很怕他,不敢太过放肆。
就这样平安度过几日后,这天终究是到来了。两辆马车从城中飞驰而过,左拐右拐来到了少年的家门口,头一架马车中走下了一个身着铠甲腰别长剑的中年人。
中年人下车后并没有叩门或推门,他只是手握剑柄静静待着,宛如战神一般,让人不寒而栗。
少年的父母此时正在屋内收拾行李,少年在院内玩耍,他望着父母房中传出的声响,明白父亲又要走了。
近两年,父亲经常出门的,刚在家待上几天就离去两天,少年起初还做询问,后来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不过这次好像不一样,这次母亲也要走,少年不解,母亲没做过多解释只是留下一封书信便匆匆随夫而去了。
有些话语当面不好说出口,书信便成为了最好的媒介,少年看着父母上了马车,然后伴着烟尘离远了少年的视线,少年眼眶红润了,他虽然不小但也不大啊,怎么忍心我独自在家呢?
“哭完了便过来吃饭吧。”院落里传出了老人的声音,少年这才想到家里现在又多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貌似会法术,能读人心里;另一个就像个木头人一样,面无表情,只呆在老人身旁听老人差遣,想到这哭的声音更大了,没一个正常人。
不管少年哭声音有多大老人都置之不理,最终还是少年的肚子咕噜乱叫声大过哭声才屈服。
互相了解一段时间后,少年淡然了些,这两个人虽都很奇但人还不错,但对少年很好。从信上看,父母归期未定,哭、闹也无法解决问题,自己也不小了,该自己经历经历世面了。
“一会儿不要害怕,别人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老人打断了少年的回忆,将他拽回现实。少年正了正神,转头看老人,不解,老人也在看着孩子,四目相对。
“过程太过于复杂,不过结果总会是好的。”老人先一步转离了视线,少年更加听不懂老人在说什么了。
重新戴好斗笠,杵着拐杖出了房门。现在夜已经很黑了,客栈的里的其他人都应睡了,客栈外老人正在与什么人商议着,待老人点头后,双双回入,那人蓄力一跃到了房梁上,老人则端坐在了客栈一角。
风吹着树叶,发出沙沙声,紧接着,另一种声音呼啸而来,渐渐盖住了沙沙声,愈来愈近,最后完全遮住。
“兄弟们都给我围好了、伺候好了。”这伙土匪的小头目狰狞着面目,拔出腰间别着的弯刀,指着客栈下死命令道。
小弟们纷纷响应号召,围住客栈。小头目一马当先,先一步进入了客栈。
然后用弯刀的刀柄叩着客栈的门板发出咚咚声。“醒醒,醒醒,都别睡了,都给大爷我起来。”小头目近乎疯狂的喊着,很快便传到了客栈房间所有人的耳里,尤其是少年。
屋里的少年着实是被吓到了,赶忙跑到到床上,躲进被子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说完后的小头目想搬个凳子歇坐下,这才注意到了那个角落里正襟危坐的老头,刚才说的话仿佛他没听见一般,还是闭着眼,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
小头目略觉有趣,喊了两声,老人还是不说话,他便多了更过兴趣,将弯刀平置于桌面,刀柄冲着自己,吩咐手下将老人带了过来。
小头目和其他人已经等不及发泄自己的欲望了,迫切用杀人麻痹自己,释放压力。
一番挣扎之后,其它人也都被带到了小头目身前,算上老人与少年一共七个人,分别是掌柜与店小二伙夫,还有之前两个喝酒阔论的外乡人。
少年是完全被吓傻了,看着老人又看到桌子上的弯刀,身体不自觉的发起抖来,眼泪也要涌出来。
掌柜三人也没见过这阵势啊,客栈开了小二十年了,见过打劫的,但没见过上来就要砍的,看众人的身着面色,钱怕是不管用了,这单纯就是来杀人取悦的啊。
那两个外乡人倒没什么怕意,虽然被押手还绑了起来,还是怒目瞪门口的小头目,咬着牙,等待时机,蓄势待发。
他们将几人围置于客栈中央,然后退入黑暗中,他们都想好了如何玩弄几人,不能让他们死的太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