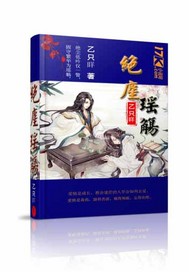淡淡斜晖透过窗棂,一位七旬老妇,坐在窗前似乎忘去了时光的流逝。这是一所老旧小区的六层小砖楼的单元房。她还记得这里原本就是她的家,是紫石外街,窄小的胡同,是一条由西到东的由高到低的胡同。幸亏她家住在胡同的西头,也就是最高处的一所小院子里。院子有颗老槐树,曾经有人劝她爸爸老宁头把树砍了,因为槐树是木中之鬼,很不吉利。可老宁头根本不信,每年晚春槐树开花,满院槐花香,串串槐花采摘下来,和棒子面搅合在一起蒸槐花饽饽,或者下锅炒槐花棒子面疙瘩,都好吃得很嘞。后来她在这小院长大,上学、参加工作。老爸老妈相继去世,就剩下她和哥哥姐姐。房子是父亲年轻时置下的,要兄妹四人平分,每人正房分不上一间,最终她用一套单位分的单居室和一万多存款,和哥哥姐姐换来了这套小院。
八十年代,她大学毕业,在单位找了个丈夫,一起在这个小院度过十年春秋。她拼命工作,还得照顾孩子。她至今搞不明白的一件事,就是他怎么就成了自己的丈夫,除了也有一张文凭外,其他的大概就什么都没有了。小院被拆迁了,拆迁办给她分配楼她坚决不要,她就要回迁,住回原来的紫石外街。房子给了,由于是点名要回老地方的回迁户,所以也没有太多的补偿金。当然房子也就一普通的三居室。后来补偿金加上她的积攒,她总算把闹着要出国的儿子送到美国去留学。儿子一走,至今又快二十年,没回来。顶多是给她寄过两次美金,一次一万“刀了”。
退休了,人也渐渐地真的老了。原来很多事都需要依仗她的老伴,突然提出要离婚。离就离吧,老男人拿着自己的工资卡和一个白净面皮的东北娘们走了,也不知走到哪去了。
老父亲老母亲从这里走了,哥哥姐姐拿着分到的小钱钱也走了,儿子拿着她最后血汗钱也走了,最后那个老男人也走了。
她坐在落日余晖的窗棂前,心中总是以前啊以前,那许许多多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