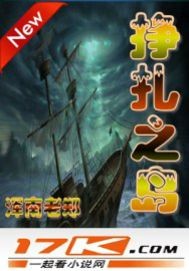这边蓉蓉上了车,心里兀自跳个不停,将衣服紧紧抱在胸前,怯怯的喊了声:“周委员,好歹不能连累我同学,下回见了她,你只当做不认识。”
前面的男人没搭话,车内的人影晃了两晃,想是他点了头。
蓉蓉安定了些,放松的将身体瘫在了座椅上,她当初来上海,一方面是为谋一份稳定工作,二来便是带着一项使命,她与他们不同,从大学起,便走着不一样的路,可山遥路远的摸索前行,一直都是她一个人举着火炬,身前身后皆是旷野,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好在有人在黑暗中呼唤了她一声。
“周委员,顾华奇的事已经牵扯出了很多人,万一我已经暴露,这个时候再去舞会,岂非羊入虎口?”她与周委员的接触极少,往往只有组织下派了任务,她才能见他一面。
“警备司令部那边得到的消息是没有,若行动过程中有变数,到时我们会及时通知你转移。”
听周委员的言下之意,似乎司令部那边有安插内线。
蓉蓉听他这样说,惴惴不安的情绪稍稍得到平复,眼中却涌起了些微怒意:“这样变节投敌,残害同志的叛徒,不可轻恕,否则还有效仿者,岂非片刻就能颠覆我们多年的努力!”
周委员还是没回话,只点了点头。
黑黢黢的夜,圆溜溜的小汽车在穿梭,像躲着月光,一个劲儿往阴影处藏。
新闸路陈家巷35号的一栋小洋楼,今晚出奇的怪,华灯初上的时间,门窗就被锁的紧紧,按理说,住小洋楼的人都爱夜生活,或是去上海大世界听听评弹,看看文明戏,或是西餐馆子来个烛光晚餐,毕竟人在上海,夜晚不应是俗世的蛰伏,跟着穿了黑色薄纱的白日女神巡游一番,把那些被神性调动的的兽性,贪欢的欲都释放出来,这才是夜上海的风韵情致。
在喧嚣的月色中,有个将衣帽裹得紧紧的中年男人,正立在楼下的小巷暗处,探出半个身子观察着动静。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除了行人,零星几只野猫野狗,再就是偶尔飞过夜空的美国飞机,轰隆隆的响。
那黑沉沉的小楼里都是死一般的静。
“35号~!”那男人心里默念着。
上头的命令是今晚八点转移,可除了早晨从门缝塞出来的一张字条——“勿要打草惊蛇!”,35号小楼里便再没递出过一次消息。
“等不及了!”男人压低帽檐,疾疾的走了过来。
那是栋带后花园的洋房,在巷子深处,走近就觉得草木深深,夜来刺拉拉的都是寒气。
往手上吐了两口唾沫,男人攀着一棵老桂树爬上了院墙。
隔着茂盛的枝叶,正看到院子廊檐下挂着灯笼,像是烧了些时辰,所以红的没那么艳,只暗暗的闪,像是聊斋里的鬼头灯。
“啪”男人已尽量轻声落地,可鹅暖石滑脚,他还是趔趄了一下,等他慌慌张张的起身,警戒的四处张望时,二楼房间里赫然站着个人,正直勾勾盯着自己。
男人背上的汗毛刺猬般炸开了,赶紧拔出了腰间手枪,对准了二楼,在那么一瞬,人影不见了,窗帘还在晃,证实刚才看到的绝非幻觉。
“TM的,见鬼了不成!”
男人额头上都是汗珠,密密渗出来洇湿了头发,他是奉军备司令部的密令来探查的,文件里明明说这里住着顾家的13口人,可眼见的都是死沉沉的静谧,人都到哪儿去了!?
“有人吗!!”他大声呼喊着,给自己壮胆,当然没人回答,连回音都没有,都被静谧的空气吞掉了,他小心翼翼的推开房门,空无一人,连桌椅都抹得干干净净,像是等待租赁的新房。
“中午我就守在门口了,没见人出入呀!”他想不通,还有那个人影,是不是顾家人。
“咚!咚!”楼上亭子间传来脚步声,窗户“啪!”一声被打开,接着是“踏踏”的奔跑声。
“砰!”
一时受惊,子弹就飞了出去,把天花板哗啦掀开好大个口子,玻璃吊灯绽飞了一地。
男人不顾一切的冲上了二楼,端着枪警惕的四处看,作为军人,他不信鬼神,毕竟跟着国军东征西战,什么怪事没见过。
“有种出来,别TM在你爷爷面前装神弄鬼的!”他胆子大了很多,一脚将亭子间的门踹开,地板上赫然一个大洞,是他刚才一枪打出来的,敞开的窗户正对着别人家的房顶。
他往外看去,远处一排排都是黑压压的屋脊,窗台,小院,空空的,有人有灯光也是冷清的。
“给他跑了!”
他恨恨的吐了口唾沫,一拳打在墙上。
“可顾家的13口人呢?”他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自从顾华奇投靠国军,很多革命人士就被供了出来,而后拘捕的拘捕,枪毙的枪毙,司令部要求追根溯源,于是,一干有牵连没牵连的,都被扯进了漩涡中,一时间人人自危,也都恨极了顾华奇,恨他是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为了以防万一,司令部只得派人转移顾家人,谁知,早上还好好的一家人,晚上便集体消失了。
“这回去该如何交代!”男人脑门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
正在这懈气的时刻,身后忽然叮铃铃传来电话声,男人被吓了一跳,电话像是在客厅,绕过狭长的走道,响着的是一台手摇电话机。
他接了起来。
“下午去不去百货公司看衣服呀?顾踏踏!”听声音是个中年太太。
“滚~!”他心情不好,直接骂了声。
电话那头,愣了愣,接着就是回骂:“对伐可以凶来兮额。”
他听不懂上海话,啪的一声挂了,那电话绳太长,一下子绕到他的袖口上,他心烦的解着电话线,就觉得手上腻腻的一片粘稠,等再细看,那电话线上红彤彤的都是血!
“哇!”他吓得后退几步,把那话筒丢的老远。
他这才发现,不光是电话绳,包括壁纸上,都隐隐有些血点子,不过因壁纸上的玫瑰也是红的,所以刚才没发现,现在这样细细看去,只觉得那玫瑰红的娇艳欲滴,像是一汪血水涸在了墙上,有两滴未干的将坠未坠,看的叫人心惊。
这里明显发生过什么!
可他是前线打仗的军人,说有勇无谋并不为过,此刻若是别人,早该一个电话挂到司令部求援,他却还在磨蹭着猜测经过。
房子里还是静悄悄,他端着枪又上了三楼书房,这是间两进深的敞阔房间,外间是会客室,里间是书房,四扇鸡翅木顶天书柜,海棠玻璃的柜门。
“《封神演义》,《杨家府演义》,《艳婚野史》,《续英烈传》,《绣榻野史》......”他沿着书柜数过来,边念着,边啐了口唾沫。
“看来这姓顾的还爱看明清小说呢!”他有些不屑,毕竟叛徒就像人堆里的麻风子,极具传染性,往往长出病痂的地方又是隐私处,所以人人避之不及。
终于,他停在了一本黑色的书面前,那本书没有书名,更像一本笔记,他将它抽了出来,分别翻到了7.23.68.90.112这几页,里面不过都是些曲谱,国际歌、流行歌曲之类,但这几页上都有被钢笔圈起来的音符,他小心翼翼的将音符数字抄了下来。
眼下的时局,两党的高层,都有了密码本,用来传递消息解读消息,特别是顾顺章,很多人和事经过了他的手,他要说的话,便道道深锁的变成了密码数字。
“这样至少能回去交差,否则一家人就这么凭空消失,熊司令定会给我个玩忽职守罪!”他这样想着,心里也是升腾起异样的疑问。
方才那个逃走的人,到底是哪方的势力?
若说是地下党,可能性很大,但没道理能这么快查到给顾家人安排的这处新住所,若说日本人,抓了顾家人来要挟国共两党,那倒是一箭双雕,国党只能服软,因怕日本人杀了顾家人,让顾华奇激恼之下跳反。地下党更不敢有动作,否则日本人威胁顾华奇吐露更多地下工作者,岂非会将地下党一锅端。
眼下顾华奇说了多少,在于国党给了他多少好处,若顾家人都死了,国党无论给他多少好处,怕他以后都会有所保留。
他有些挠头,也只能作罢,正待要走,就听楼下传来敲门声。
“顾踏踏~!顾踏踏~!
听这声音倒是格外熟悉。
去不去呢?他心想,万一是个知道顾家人下落的邻居,那可不能错过。
想到这,他理了理衣领,又把手指上的血渍擦了干净,便下来开门。
来的是个少妇,上海街巷里最常见的那种少妇,绸缎旗袍,烫了大卷的长发,口唇抹得红红的,像吃了满嘴印章子,手上还握着把瓜子,嗑的噼啪响。
“侬系?刚来的管家?”少妇半上海话,半苏州口音。
“嗯嗯!”他含糊的点了点头。
“顾踏踏~!”少妇没等他反应,径直走了进来,像是熟客。
“呃!慢着慢着!这家人都出去了,你不要喊了。”他阻拦着,怕她喊出什么不得了的变故来。
谁知那女人并不理他,只自顾自的来到厨房。
“每日顾太太都要约我来喝下午茶的,晓得啵,今天没叫我,我便想着是一家子看电影去了,我又馋着他们家厨子做的茉莉花燕窝,刚好,你新来的,我也不见外,先来舀一碗吃。”那女人熟练的揭开碗橱里的一个小盖盅,见里面乘着白盈盈,亮晶晶的燕窝,便有些得意的笑道:“看到了伐,顾踏踏特地给我留的!”
说完,端着小盅要去餐厅。
男人有些慌,餐厅天花板刚被自己一枪掀了个大洞,被发现了可不得了,于是陪着笑脸央求:“太太说餐厅的地板刚打上蜡,现在一时半刻不许人去,您看不如我给你搬个小蹬来,您就坐厨房吃吧!”
听到这话,那少妇眉眼间便有些不悦,但顾忌主人家的面子,也不能发作,便差遣男人去寻张舒服座椅来,她好在厨房吃。
男人心里只求少妇不乱跑坏了他的事,听说只是寻张椅子,便忙不迭的寻了来,又像模像样的铺上了坐褥,显得格外殷勤。
那少妇坐下刚吃了两口,便咂着嘴直呼疼:“该死的,不该磕了那么多瓜子,这下子嘴皮子都起了燎泡,吃口甜汤都疼!”
少妇信手将燕窝推了过来,冲男人道:“你给我把剩下的吃完,别浪费了,顾太太问起来,就说是我吃的,免得她怪罪,说好心好意留给我吃的东西,结果我倒不领情。”
男人忙推拒,见他有些窘,女人便捂嘴娇笑起来:“你这管家的,怎么憨憨傻傻,一碗燕窝而已,哪个做管家的没吃过主人家剩下的汤汤水水,偏你倒不好意思起来,你这人,真是与众不同!”
说完,便上下打量起男人,男人心虚,怕她看出端倪,便只能把碗揽过来,强吃了两口,就瞥见女人从碗柜的糖罐里抱出来一罐糖,舀了两勺在燕窝里。
“你可是有口福呀,新管家!”女人调皮的眨眨眼。
男人只能赔笑,好不容易把那甜丝丝的燕窝吃完,女人便磕着瓜子告了辞。
男人长舒了口气,拿出刚才记录的字条,想要继续破译其中的密码。
“68*3,8进2”男人嘟囔着,盯着纸条絮絮叨叨,忽然就见一颗红扑扑的水珠子滴在白纸上,啪的一声,触目惊心,
“这是哪里滴下来的水珠子?”男人正待要擦,啪的又是一颗,正好滴在他的袖口上,他这才发现,这哪里是水珠子,原来是他的鼻血。
这下,他慌了,忙起身,谁知脑海里嗡的一声的空白了,肺部抽抽的呼吸不了,他挣扎着想出声,却连动动嘴巴的力气都没有,很快,他呛出口鲜血,喷了老远,一下就载倒在地上。
客厅的电话此时又响了起来,叮铃铃的吵,格外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