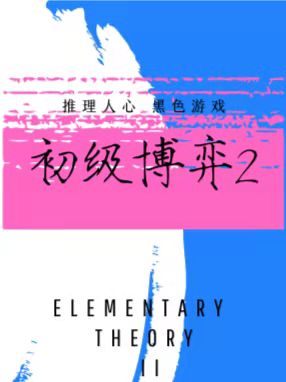这个翻过身摁停了闹钟,扯过被子蒙头打鼾的初中生,叫神坛。他本姓鲁,后来和他爹断了关系,干脆把姓一去,化名神坛。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神坛探出脑袋,伸手摸索着接了电话,那边吵着骂他:“喂,孤儿,还来不来了,都开了三局了。”电话这边的神坛倒也来了精神,举着电话朝那边吼:“哪个告诉你这话,再乱说我拧下你的头当下酒菜!”摔下早已挂断的电话,从一堆乱糟的袜子中,找两只还算干净的,放鼻钱闻了闻,满意地穿在脚上。
他一手扯着衣服从屋里走出来,穿上另一支袖管,不断用手在鼻前扇拂着,朝着台阶边吐了口痰,嚷道:“大清早的烧煤,整这么人,呸!”旁边邻居都看着他拖着尺码不同的鞋向村口大步走着,各自摇摇头,接着低头干手里的活。
两年以前,神坛刚刚升入初中,当时他还姓鲁。他从口袋翻出一沓纸钱,整理平整,共是三十四元,紧紧握在手里,站在路口等着红绿灯。那钱是他计算好买书包的,红绿灯前面就是商场。红灯还剩三秒,他感觉手里的钱软了许多,他摊开手开那钱是被手心的汗浸湿。他将那钱重新展开,数了一遍,还是三十四元,他又重新攥在手心,将手揣进兜里。绿灯一亮,他的脚却像绑着铅球般挪不动。他哆嗦着一步步往马路对面搓,像是个年老走不动路的老人,只是腰还没有那么弯。随着几声汽车鸣笛声,他抬起头来,看见直刺入眼的红光,才知道已经红灯。他还是低下头,将攥着钱的左手紧了又紧,双眼一闭,发了狂似的跑到马路对面。路过非机动车道时,一个扎着长辫,穿着和他一样校服的女生没能一把将电动车停住,险些撞上神坛。她将车推到一边,气冲冲得一把拽住神坛,像是在质问他:“你怎么过马路的,看不见红灯?一头莽过来,被我撞到你是不是还要收医疗费?”神坛抬起头来看她一眼五官倒是标致得很,皮肤似那刚剥开皮的鸡蛋般颜色,再被那红得掐出血的双唇映着,也是实实在在一个美女。他却没怎么在意,低下头蹭了蹭破了底子的鞋,扭过头继续向前蹭了。那女生见没回应,嘴里骂骂咧咧地跨上电动车一拧把走了。神坛眼睛直勾勾盯着地面,虽说没有停下,却也具备了与乌龟竞速的能力。
他盯着块稍有发红的地砖,头也不抬转身走上商场台阶,在门前怔了怔,才伸出右手推门进去。他又将头垂下,径直走上二楼,步过两家书包店,从一家牌子都没有的百货店门口停下来。把假肢一般的左臂从兜里掏出来,扳开手指,将钱翻开一遍又一遍地数一会,才终推开门走进去。随着木板门“吱——”地一声响,里面应声走出个将头发盘在头顶一摇一晃的男人,上下大量着神坛。随后转回柜台坐下,抽出沓钱沾沾口水数起来,抬起一只眉毛来问神坛:“要什么?”
从放学起就没再说过话的神坛,开口说着一套流利的普通话:“那个黑色的,左边第三排第二个,单层包。”哆嗦着将钱捋了捋,头还是耷在胸前。老板斜眼看了看,“啧”了一声,皱着眉头伸手拽下包,放到柜台上,意思神坛自己来取。
神坛双手拈着钱角,定在那里足足有三分钟。最后老板钱数完了,起身看见神坛还在那站着,向他喊了句:“干么呢!还买不买了,不买赶紧走!”神坛没说话。那老板两步化一步跨过来,看看他手里的钱,又问:“你这是多少钱?”神坛还是不说。老板一手夺过钱,嘟囔句“够个性”,胡乱翻了翻,留下一句“正好”,就将那书包甩给神坛,头也不回朝着里屋去了。神坛抱着那书包,说不上是快乐还是担忧更多些,只是往商场外走着。出了商场,天已黑得透亮。他绕着小路从院子后面翻墙回了家,又熟练地拉开窗子,双手扒住窗子,双脚一蹬,两手一撑,再将头一缩,便回到了屋子。
他换下衣服他换下衣服,躺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床上,床“吱呀——”响了一阵,神坛没再敢动,只是扯过一件衣服盖在身上,就当是被子了。他听着外面“叮叮当当”响起来,小心地翻过身,像是不很在意。那是他爹在外面,一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穿着个破洞衬衫,那洞是被烟头烧的。看遍浑身上下,只有手上最是干净,没有茧子,没有尘土。实际上他只有四十岁不到,名叫鲁由,是没怎么下过力。此刻正把家里翻成个底朝天,摸出几件还能换钱的玩意,揣进兜里,朝着门口啐了口痰,骂了局“没良心的”就出去了。
听见鲁由出门,神坛翻身下床,拖着从垃圾堆捡来的比他的脚大一码的凉鞋,走出客屋来,不作声地收拾些扔得遍地的东西。他听得见刚才鲁由那句话,也知道骂的就是他。鲁由回来,是找他要钱来的,其余时候是从哪都不能见到他的。这几天鲁由像是赌没了钱,所以回来得勤了,因此神坛常从后墙翻着进来。
将东西收拾完毕,神坛取出袋发霉的咸菜,从兜里翻出来块干馒头,就着吃了几口,走到河边捧起口水喝了,又回屋里去。坐在床边,两只手小心翼翼抬起张照片,捏起衣服上最干净一处将那照片擦了又擦,一直到反出来的光照得耀眼,才将那照片架在腿上,看了又看。
照片里是两个人,左边是个亭亭玉立的女子,长发散着披到肩上,两只手交叉贴在小腹上,只是头超出了照片边框,看不清长相。旁边石阶上,爬着的正是神坛,那时他两岁,咧着嘴嘻嘻笑着,将那双眼眯起了两道弯月。此刻神坛嘴角上扬着,不自觉对着相中的女子叫了声“妈”,那声音柔的不想是出于男生口中。虽然他没有关于母亲的任何记忆,却还是认定相中那个端庄优雅的女子就是他的亲生母亲。
他将照片缓慢地立在桌上,从床上躺下来,那床“吱呀”着晃了两下就再没有任何声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