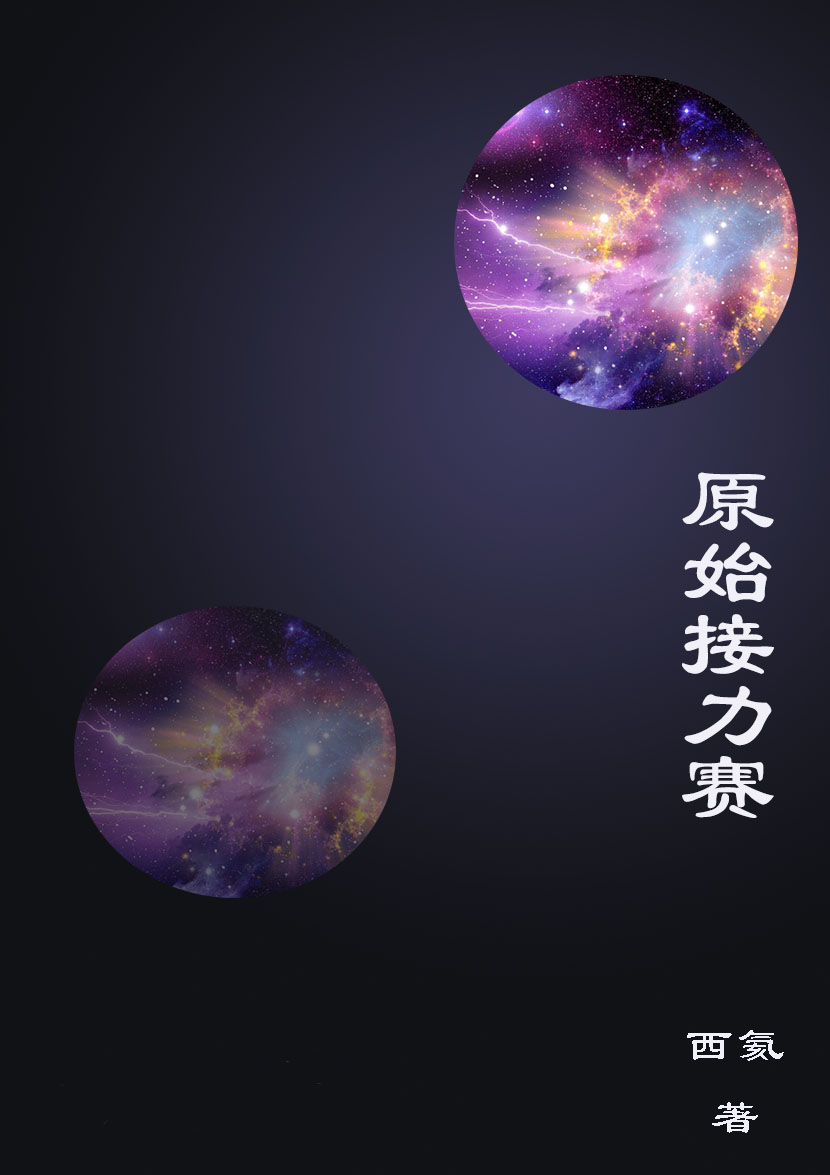熊途突然推开刑侦第三大队的办公室的门,将门口正在跟人说话的雷昊强吓了一跳,“哎呀,这不我弟吗?你怎么来这了?有啥事给哥打个电话……你是不是没我电话?来来来,存一个……”说着就去摸他的衣兜找手机。
熊途一把抓住他的手,气喘吁吁,“寄生植物,你知道寄生植物吗?它们没有根系没有叶绿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只能寄生在别的植物上,吸取它们的养分……”
“你跑过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个?就是想聊植物?”雷昊强虽然摸不着头脑,但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耐心,“那……那聊会也行,但是四点我还有个会,只能到四点……”
“不是。”熊途并不是伶牙俐齿的人,着急起来更是不知道该如何说,恨不得将脑子刨开,让他直接看。
此时此刻,他竟想起了应胜良,能够准备理解他话里意思的人,除了米小谷就是应胜良了。
但是自从那天的冲突之后,他与应胜良就没说过话,他躲着应胜良,应胜良也在躲着他,两人在走廊里遇见都会扭头避开。
也就是这个原因,他只能直接跑来找雷昊强,他怕应胜良看见他依旧不痛快。
他在心里小小地叹了口气,放慢了语速,“寄生植物寄生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吸取对方的养分,壮大自己,然后繁衍后代,因为它知道自己生命周期很短,一定要有后代才能延续它们物种的基因。但是好不容易结出的种子没用了,如果你是寄生植物,你会怎么办?”
雷昊强被问得一愣,“我?我……肯定不会只结一个种子……既然处于弱势,就只能多准备点……”
“对,廖汝一定也是这么想的。”熊途已经雷昊强终于听懂了,眼睛发亮,抓住他的手,“廖惠茹跑了,她并没有追回来,她一定准备了其他的种子……”
已经做好了陪他聊植物准备的雷昊强听到话题又转回案子上,一时没会意过来,愣了两秒钟,“你是说廖汝还是其他孩子?”
“不是,廖汝没有其他孩子,但她可能有个弟弟。她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人,她从一开始就准备了别的种子。”熊途非常兴奋,跟平时沉闷的样子判若两人,“寄生植物对宿主唯一的感情就是掠夺,越是凶狠越是缠绕得紧。肖长发不止一个情人,为什么只有廖汝生出了孩子,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后代,年近六十了却有了儿子?为什么他杀了廖汝之后,准备着出国时却突然中风了?我们查错方向了,寄生植物在感觉自己生命将尽时,会拼了命的保护种子,确保种子平安落地。”
“廖汝可能有个弟弟?廖惠茹说得吗?”雷昊强终于慢慢理解他话里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李心怡跟廖汝是一伙的?可是她之前要杀李心怡的孩子……”
“不知道,她一定有她的目的……”熊途说,“我们要查的是李心怡,真正的凶手虽然一直在帮廖汝,但是躲在表面跟廖汝对立的李心怡身后,我们被她生前布下的陷阱困住了。”
这个假设实在大胆而无厘头,也缺乏证据,但雷昊强依旧觉得眼前一亮,他立刻喊来了组员,“包路,把李心怡的资料全部给我调出来……”
因为李心怡没有作案嫌疑,完全被排除在调查之外,她的资料很少。但好在她的身世并不复杂。
李心怡老家在孟郊外的屠羊村,当初在剃头村外遇见的放羊老人似乎就住屠羊村,家中有一对务农的父母,父亲叫李文康,母亲叫辛英。李心怡在城里给他们买了套小房子,二老农忙时住村里,闲了就去城里养老。
雷昊强在查肖长发的时候,甚至还来过屠羊村,见过这对老人,可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目光都在李心怡和肖长发身上,根本没想过查他这对老实巴交的父母,跟没人敢把这个黑瘦的庄稼汉和廖汝联系到一起,只是简单问了几个问题便回去了。
再次来到这座老宅,所有人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终于在他家中的菜窖里找到了曾在视频中出现过的军绿色上衣、黑色裤子和三七牌帆布鞋。
但是李文康失踪了。
几乎是同一时刻,肖长发因为身体问题,办理了取保候审,被护工抬上车,两名律师跟在后面上车,随后,车子缓缓驶离看守所。
豪车行至景泰路段,突然被一辆农用三轮车拦住去路,随后车上跳下一个中年男人,用铁锨砸开车窗,打开车门,在车内人惊慌的呼救声中,从怀中掏出菜刀,朝着躺在后排的肖长发砍了过去。
开车的律师和随车的护工早跳车逃跑了,肖长发一声声哀嚎,引来了围观群众,有人报了警,在警察来之前,行凶的中年男人早已骑上三轮车消失在人流中。
根据律师和护工的口供,可以肯定行凶的人就是失踪的李文康。
搜索大队在高速路口找到了弃置的农用三轮车,监控拍到李文康弃车的画面,然而他本人则一头扎进了高速旁的深沟中,淹没在一人高的杂草丛中,再寻不到踪迹。
肖长发进了重症监护室,至今还没脱离生命危险。
李心怡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震惊,在警局中痛哭流涕,反反复复说,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对肖长发行凶。问得多了,便直接昏厥了过去,被救护车拉走。
还没半个小时,两名西装革履的律师带着媒体来到律所,质疑警局粗暴执法,将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强行传唤普通市民,将其逼到昏厥。廖队气得连吞了两粒速效救心丸,整个警局一片兵荒马乱。
熊途站在窗前,正看着楼下的闹剧,米小谷突然打来电话,焦急地说:“廖惠茹一个人出校门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帮我盯着她的学妹说,她出去的时候,脸色很难看。网上都说肖长发被重伤进了重症监护室,我本以为她是去见肖长发了,可医院那边说,并没有人去探望。”
熊途心里“咯噔”了一下,“你通知刑警那边了没?”
“我刚给孙组长打过电话了,我只有她的电话。”米小谷依旧很着急,“这大晚上的,她一个人能去哪儿?万一凶手要伤她怎么办?”
“不会。”熊途想到了一些事,突然觉得有些伤感,“凶手可能是想修复她与廖汝的关系。”
“为什么?”米小谷的声音因为着急而轻微拔高,“好,我知道你什么都不能说……你不要说了,专心想想她能去哪儿?”
熊途握着手机,手心微微出汗。
他听到了种子落地的声音。
***
夜色如漆,廖惠茹凭借着手机里发出的微弱光线,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山里,前方那个皮肤黝黑的瘦干老人仿佛融入了夜色里,不仔细辨别都看不清他的踪迹,只能听到树枝被踩断的“霹啪”声。
从小在城市里长大,走不惯山路的廖惠茹,在不知道多少次,险些被树藤绊倒后,终于发火了,冲着老人喊了一声:“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什么话在城里不能说?”
老人回头,看着已经被山路折磨得狼狈不堪的廖惠茹,折了回来,伸出手想拉她一把,但被触及到对方不信任的眼神,又将手缩了回去,十分耐心地哄劝着:“妞妞,再加把油,马上就到了。等到了地方,我就什么都告诉你。”
说着老人扭头继续往前走,廖惠茹咬了咬牙,心中隐约有些后悔,为什么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这样一个陌生人,并跟着他来了山里。
几个小时前,她正准备睡觉,手机突然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消息,接连几张照片,拍的都是她小时候,走进钢琴教室的场景。每张照片上都标注了日期和时间。
还有短信聊天截图,一张她进教室的照片下面,跟一串文字:妞妞,进去了。对方回复一个“好”字。
接连好几张,都是差不多的内容。
她起先看到别人偷拍她,只觉得毛骨悚然,但是仔细看那个回复“好”字的电话号码,竟然是她妈妈廖汝曾经用过的号码。
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谁一直在默默护送她去上钢琴课,一送就是近十年。
她鬼使神差地拨通了这个电话,对方的声音让她觉得非常熟悉,她小的时候似乎经常听到,但是在哪里听到的又想不起来,对方跟她说:“妞妞,我是舅舅。我时间不多了,临走前,想见你一面,跟你聊一聊,你的妈妈,我的大姐。”
就是这一句话,让她不管不顾冲出了校门,现在回想起来,她那一刻的冲动是从小到大无数次渴望与失望推动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跟妈妈赌气的孩子,终于等到了妈妈主动来敲她的房门。
终于爬上山坡,周围都是倒塌的石头房子,在黑夜里仿佛是恐怖片里的场景。
老人来到一处还算完好的石头房子边上,冲她招招手,“妞妞你看,这里……这里是我和大姐在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家,要没有它,我们两个可能都死在四十年前了……”
说着,他找来了藏在草丛里的梯子,手脚麻利爬上了阁楼。
廖惠茹犹豫了片刻,也跟着爬了上去。
阁楼并不高,人站立起来都能顶到屋顶,老人爬着进去,从怀里摸出了便携的小台灯,放在木架子上,微弱的灯光将阁楼里照亮了,老人坐在地上,看着不大的阁楼,惋惜地喃喃:“什么都没有了,都被警察没收了……”
廖惠茹也坐到了地上,着急地催促老人,“你要说什么?”
老人沟壑丛生的黝黑面孔上露出放松的笑容,仿佛经过了长久的逃亡,终于回到了家,“我是你的舅舅,我叫孔文康,后来跟了我养父姓,改名为李文康。你的妈妈原来叫孔惠,后来为了户口,就用了她的养母死去女儿的名字。”
“我从来没听她说起过这些……”这些信息来得太突然,廖惠茹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她为什么不跟我说,我还有个舅舅?”
“因为不说有不说的好处,不说就没人知道我和大姐的关系,我就能帮着大姐做些她不方便做的事。”李文康说着长长舒了一口气,“现在我所有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终于能跟你好好唠唠我和大姐的事。我们这一路走来,可真是不容易啊……”
廖惠茹屏住呼吸,听李文康慢慢说:
“四十年前,我五岁,大姐七岁,爹娘上山挖菌子卖钱,赶上了泥石流,两个人都被埋进了山里,尸首都没找回来。村里的人帮着联系了亲戚,那家亲戚本来是答应收留我们,可是等村里人带着大姐和我走了二十里路到了他家门口,他却变卦了,死活都不给我们开门。村里人家里也有孩子,不能陪着我们一直等,就嘱托大姐好好看着我,自己先走了。大姐带着我在他家门口站了一个晚上,也没人开门,我饿得一直哭一直哭,大姐就领着我去讨饭吃,走着走着迷路了,呵呵……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每个地方都有福利机构,你们怎么不去福利站,怎么不打电话报警?”李文康说的话,让廖惠茹觉得陌生,觉得匪夷所思。
“妞妞啊,四十年前,哪里有电话?我们村里连电都没通的。我和大姐都没上过学,不认得字,什么都不懂,哪里有现在的孩子聪明?”李文康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我们命也不好,第一次遇到肯帮我们的大人,还是骗子。”
“骗子?”廖惠茹心里一揪。
“大骗子,坏透了!”李文康提起这段往事,一脸阴郁地咬牙切齿,“他们说给我们饭吃,给我们漂亮衣服穿,还让我们住大房子,把我们骗上车,等到了地方,才知道是个窑子窝。窑子你知道吧?就是女人出卖皮肉的地方。他们是看中了我大姐长得周正。我们就被他们开车一路拉到了这个海市,说这边有客人看货。在进城前,大姐趁开车的不注意,拽着我打开车门,跳车跑了。我们两个一头扎进林子里没命地跑,也不敢回头,等听不到人声了,我才发现我的腿摔坏了,肿得像个馒头一样。大姐背着我,在山里乱窜,正不知去哪,就发现了这里。石头的房子,结实,不漏雨,打扫打扫还很干净,我们两个高兴坏了,流浪那么久,终于住上像样的房子了。”
廖惠茹环视了这个低矮的阁楼,她从小在城里长大,在她眼中,这里跟山洞差不多,怎么都称不上像样,可是看李文康脸上的欣喜又是真实的,她想着当时妈妈的处境,心中顿时一阵悲哀。
李文康继续说:“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年半,每天打山里的野兔子,摘野果子吃,天冷了,我们就捡些干净的树叶铺地上当褥子,好在这里也没太冷的天气,我们好赖算活下来了。后来,我们被放羊的老头发现了,他们把我们带回家,说要我当他儿子,把大姐送给了一个死了闺女的婆子当女儿。起初我不愿意跟大姐分开,但是那老头不要女娃,我就哭就闹,大姐给了我两巴掌,让我懂点事,给人当儿子总比在外面挨饿受冻强。从那以后,我俩就改了名,一个叫廖汝,一个叫李文康。虽然到了不同的人家,但是我俩经常在这里见面,大姐跟我说她的养母带她去城里卖包子,城里有多好,有多好,叫我好好念书,长大了去城里生活,让我们的孩子再不要吃我们吃过的苦。可是放羊的老头身体也不好,我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他就不让我上了,我接了他的班,开始放羊。大姐听说之后哭了好久,可她也没办法,她的养母一天学都没让她上过,她连名字都不会写。大姐十五那年,养母就死了,她一个人在城里打工,后来就在打工的饭店里遇见了肖长发。那年大姐来找我,给我买了好多礼物,她说,她都不知道原来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有钱人的小孩过的日子,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也就是那个时候起,大姐开始动了想要成为有钱人的心思,她说她需要我的帮忙,既然上天一开始什么都没给我们,那我们就只能靠自己去抢去夺……”
廖惠茹听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为什么非得当有钱人?普普通通的不行吗?”
“妞妞啊,你弹钢琴的时候多开心啊,大姐就喜欢看你弹钢琴。她没空陪你的时候,就让我去陪你,我就挑一篮子菜,跟你坐一班公交车,你下车,我也下车,你去弹钢琴,我就在琴行外面那条街上卖菜。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大姐是对的,我们村里的孩子都没人能学上钢琴,只有你,还有心怡。你们两个都是大姐拿钱供出来的。妞妞啊,大姐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让你的子子孙孙都能过上好日子,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是苦和穷。你要是还埋怨大姐,那大姐可就太冤了。”李文康说完,长长叹了口气,“我知道你怨恨大姐不能给你一个好的家庭,可是大姐她真得尽力了。好了,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你打电话报警吧,跟警察说我在这里,也算是跟我撇清关系,我做的事也牵扯不到你。”
廖惠茹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她觉得难受,又觉得失望,她一直想要一个原谅母亲的理由,可是李文康给她的理由只让她觉得悲哀,她依旧理解不了母亲的所作所为。
是啊,让她怎么理解呢?她读得书,走得路,每一步都告诉她人贵在自强,可母亲没读过书……可能母亲现在在另一个世界,也在埋怨她的无情吧?
她站了起来,拿出手机,“我肯定会报警。但是……”她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还是谢谢你,在我这辈子最孤独的时候陪过我。”
廖惠茹顺着梯子往下爬,刚落地,就见米小谷冲了过来,双手捏着她的肩膀,紧张地上下查看,“你果然在这。有没有受伤?”
于此同时,熊途已经顺着梯子爬上阁楼,就听阁楼上传来一声“咕咚”一声巨响,接着是金属落地的声音,随后,传来李文康犹如困兽般的怒吼声:“放开我!我要死在家里!求你让我死在家里……”
廖惠茹靠在米小谷肩头,泪如雨下。
很快,孙组长也赶到了,李文康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
上车之前,他站在车门前,长久注视着眼前连绵不绝的大山,仿佛在和好友道别。
暗金色的光芒从大山后面透出来,山中成千上万的树与花在光芒之中露出一点色彩,黑夜慢慢融化在这些色彩里,天就要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