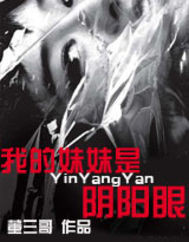今天忽然想起了一个故事,这件事还是我姥姥家的邻居讲的,过去这么多年还是记忆犹新。
为什么突然想起,这都是单位同事闹的,午休不说好好养养精神,都在那扯闲篇儿,扯来扯去就说到仙家看病的事上了,就是出马仙给人看病,当然都看的是虚病,虚病可能就是医院医生看不了的病,有点像癔症,超出自然的规律,医学或科学上又不能恰当的解释。
本来困意萦绕,听他们说的热火朝天口吐莲花。都给我整精神了,于是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当时小爷的嘴岔子一瞥道:“尔等先把布满吐沫星子的嘴丫子擦擦,听七爷给你们个真实的事(初七是我的生日,也是我的小名,家人和熟悉朋友都这么叫我)。听完了不敢走夜路或者做噩梦概不负责。”
于是各种不屑的声音不绝于耳......!必须先喝口水,润一下我这磁性的公鸭嗓子!就开始讲这个关于厕所里的吊死鬼......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到了寒暑假父母就把我送到姥姥家。是双职工家庭,大人都上班了没人看着我,到了寒暑假大人就把我送到姥姥家,姥姥家人多,有姨有舅的挺热闹。姥姥家在大方里住,八十年代的大方里都是平房,房挨着房户挨着户,几乎每一家都有棚子(就是很简易搭建的房子,不用保暖,不漏雨就行,用来放杂物)或院子,在几条胡同的尽头有垃圾站,公厕也都是旱厕,就是茅坑一整排,人多的时候大家都排列整齐的蹲着,也挺壮观!
单说这一年寒假的一晚,姥爷跟着车队去山里拉木材,舅舅没在家好像上夜班。家里只有小姨跟姥姥我们三个,我们正围着炕桌吃松子。因为姥爷常去山里拉木材,山货也带回来不少,木耳、各种蘑菇、榛子、松子,相比之下花生瓜子那就太一般了。八十年代物质还是挺匮乏的,买什么东西还凭票,就像粮票布票。而我们却总能吃到这样的紧俏商品,而且羡煞旁人,有时候东西多了还能给相好的邻居送点过去。我正在厨房玩火,就是把松子皮一个一个的放在炉篦子上,等着温度到了松子皮着火。到了晚上趁炉膛有火就压两撬煤,这样慢慢着到后半夜炉膛火才能熄灭,就听房门一响一股冷风灌了进来。
来的人我叫刘姨,是姥姥家的邻居,也是经常来。屋里她们三个就唠起了嗑,由于大人唠家常我是没兴趣听。又过了一会听见什么“烟魂”“招没脸的”“上吊”好奇心促使我把耳朵支楞仔细听。虽然在厨房但是她们说话我还是能听的清楚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这么注重对小孩子的教育,老人经常给我讲一些鬼怪成精的故事也是常事。
这时就听刘姨开始讲了起来,是说一个多月前的一天晚上,将近半夜了,刘姨去上厕所。因为平房区的厕所时旱厕,男厕女厕用墙隔开,一整排的蹲坑供人使用。刘姨进去就在第一个离门最近的蹲坑蹲下了,没多一会就听有“刷刷”的声音。当时她说不觉得像走路的声音,因为下的雪被人踩实了,人走上去不是那种“刷刷”的声音,随着声音的越来越近一个人影也进了女厕所。正在蹲着的刘姨也打开手电筒帮着照亮,(住平房的人都这样,都是邻居,晚上有人进厕所都会打开手电帮人照亮),随即她看见是个老太太穿着小花鞋,黑色趟绒上面有红花,鞋底是黄色的,鲜黄鲜黄的。当时刘姨在寻思着老太太的鞋还挺新鲜。随着那个人往里走手电筒的光束也跟照了过去,就见那个人越走越往里,最后在最里边的一个蹲坑踩上去。里面的蹲坑是最宽的,因为必须要顺下去水桶掏厕所,以前没有吸污车,单靠人用扁担挑着桶往出掏,一般没有人用那个最宽的蹲坑。看那个人小脚小腿儿的居然在那个最宽的位置,还蹲了下去。刘姨觉得纳闷,这老太太蹲在最宽的蹲坑,还不脱裤子。于是手里的手电就往上照了照,想看看是不是住在一左一右的人。当光束照到那个人头上的时候,根本看不见容貌,那个人的头是用破黄布着,破破烂烂的碎布。与此同时那个人的头也转向刘姨这一侧,就见那个人的胳膊重重的向刘姨这边掷两下,像是手里有东西砸人一样,紧接着那个人就一边摇着头一边开始摘包在头上的黄布。这时候刘姨感觉后背冒凉风,头发丝发炸,提上裤子就往家跑。好在不是很远,到了家就堆碎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这是刘姨听她们家里人说的,她一连几天高烧都不退,还说胡话。后来通过亲戚找个明白人来看,说是遇到吊死鬼了,要是看见吊死鬼不包着头那就是要找替身,看见的人基本也活不了。
再后来半夜在那个厕所和十字路口烧了些纸,毕竟人和没脸子的(没脸子的就是鬼魂土称)遇上是不吉利的事,过了好几天她才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