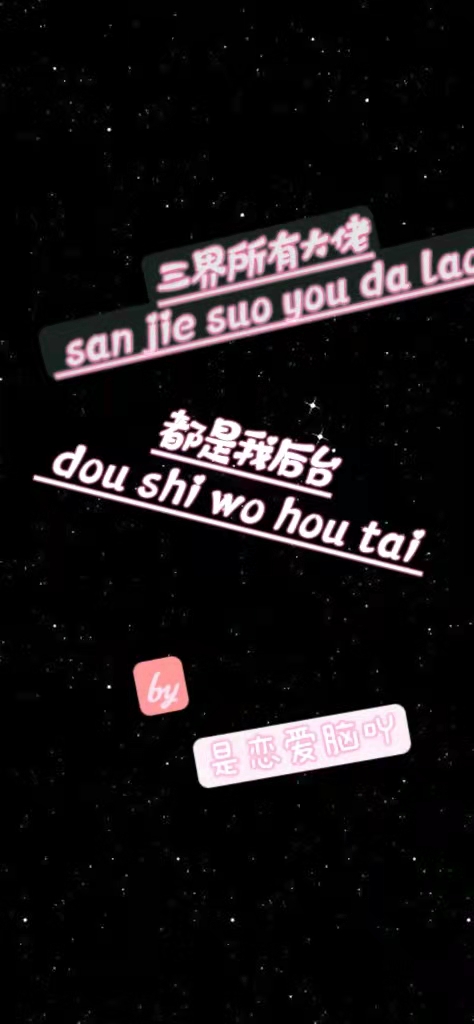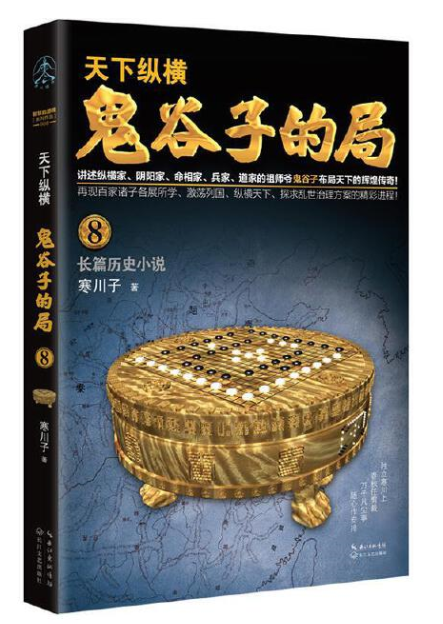引子:
“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问》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山海经?大荒西经》
檐下,灯火连成一线,幽幽照去轩廊的西头。
轩廊的西头,有一扇窅冥深重的门。
离开那扇门,她越走越远。
远到,门后透出的话语都已变得希微。
希微的,叫她再也听不清了。
如此,她方才停下脚步。
悬系的一颗心不再摆荡。
紧握的一只手不再颤抖。
指扣松开,玉笄崭露出来。
青白色的玉笄,被指间的汗水浸渍,光华愈发温润。
凝视玉笄,她又想起阿娘的话。
及笄那年,阿娘将这支玉笄放到她手中,对她说,这玉笄是世传之物,由家族中年成的儿女承得,往后,当她婚嫁,有了后嗣,也请她将这支玉笄交托后孙。
如今,她照例是要将这支玉笄传赠给她的孩儿。
然而,当她执起玉笄,站在兮月的卧房前,她却落慌,不敢叩门。
“时辰不早,娘子若无其他行事,青婢该回东院去了。”
“慢着,阿姊。阿姊能帮月儿看看么?月儿应该穿哪件衣裳去赴礼呢?”
“依我看,每一件都是得体的。”
“真是如此么?月儿怕闹得笑话。”
“怎么会?只不过是一场简单的仪礼。平素大方就好。何必太过在意他人的看法呢?娘子早些休息,明日也好早去早回。”
“慢些,阿姊。”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
“没有,青婢便回了。”
“阿姊,且慢。”
“又有何事吗?”
“那盏灯就让它点着吧。我听闻阿娘答应蘅寻元老会去槃凰庙观礼。想到如此,月儿睡不着。”
房内的交言声隐约从门缝里透出来,她驻定聆听。
聆听之间,身体竟是颤栗不停。
指尖未及触上门扉,胳臂已不再听从使唤。
一只手僵凝在半空里。
脚步声越传越近。有人正从门内朝着她走来。
手臂忽就痹软,匆匆垂落,没了力气。
转身,她仓促背过那扇门,逃离,回向东院去。
八年里,她从未踏足西院,从未经过这条轩廊。当她走在昔日的屋檐下,檐廊已显得古怪而生分,似乎比记忆里阴暗而悠长。
檐廊有多长呢?她不知道。她已经在长廊里走了很久很久。
走了有多久呢?她也不知道。她隐约觉得,或许已有一炷香的时间,或许有三两个时辰,又或许是更长的时间。
她什么都不知道,却唯独知道一点。那就是,即使再走同样久的时间,她也未必能够走到廊尽头。
因为,她与轩廊尽头的距离并未有丝毫的缩减。长廊尽头是连接别院的转角,那转角此刻就呈现在视线的不远处。她一眼就能瞧见那处转角。可当她每走过一步,迈近那处转角,那转角便似乎又远离她一步。如此,她永远也不可能走到廊尽头,走出这条轩廊,回到东院去。
凭扶廊柱,她歇作喘息。
看着手心里的玉笄,她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会逢其适,几名侍者言辞窃窃地,从转角处走来。
瞧见那些侍者,她忽然想到,不如就让侍者将这支玉笄带去卧房,交给兮月。
转念时,侍者已从她身旁走过,步影如轻烟。
她招唤几声,侍者们置若罔闻,如同从未瞧见她似的,转眼已行经老远。
站在灯火下回望向侍者们西去的背影,她握紧玉笄,陷入踯躅与迷思。
忽而,有风吹来。
阵阵清芬没入廊中。
嗅见芳馨,她从彷徨中醒来,循味望眼廊外。
廊外,簇朵盈枝,赤薇花正郁郁盛开着。嫣红的花瓣遇风散漫,如靡靡的一群飞蛾,向着灯火,向着她,窈窈落来。
碎红如雨逝,芳华似梦逾。此间的景致,令她望尔兴叹。正当她沉浸在一饷叹息间,灯外的碧宇流云里,悄然露出一轮圆月。
月当中天。
时间约莫已是子正。
夜已这样深了啊!
她感慨着,思绪纠葛,犹豫不定。
时移物异,且在害怕着什么呢?这样的夜晚,还要消磨多久呢?
她开始劝服自己,提起脚步,往兮月的卧房踅回。
她又一次站在了兮月的卧房前。
房内的灯火似乎已经熄灭。
幽暗的门前,她的手臂再次悄悄伸向门扉,伸向那对铺首和衔环。
可是,她的心仍是游移不定。
伸去的手垂落,抬起。垂落。抬起。
反反复复。
“阿娘。”
细弱的声音隔着门扇轻轻传来。
吱呀。
门,终是被她推开了。
视线过处,昏昏沉沉。
房中的陈设她看得不清,只见来满室人影,凌乱纷呈。蒙昧的灯光下,人影交织重叠,恍若一群鬼魅。
她朝芜杂的重影间看去,人罅里,一衫白衣倏倏显现出来。
衣白的郎君背向众人端立在床榻边。
是谁?她不禁疑惑,又定睛看去。
是他。心跳刹那间似漏停了一拍,屏住呼吸,她变得遑遽无措。
月照!她不经意地唤出郎君的名。
名字脱口而出,她的心似地坼山崩,訇然一声,坠落深渊。
战栗浑身。
她向着郎君的背影蹑踱而去。
众人恰时阻遏在她跟前。
月照的声音仿佛从时空的断崖边,涤荡旋来:“将夫人带出去。”
郎君的话语悠然飘落。转瞬间,室内的灯火似明亮些微。朦胧的光影褪去,众人的面孔逐渐清显,时光悄然回到八年前,记忆里的画面重新上演。
侍佣们将银盆和刀具搁置在床边。
床榻上,兮月安寐睡熟。
月照立在榻前,背影宛如一尊玉蜡,锵硬决绝。
挣扎,挣扎,用尽气力,拨开人墙,终于,她掖住郎君的衣袖。她匍到郎君膝下,歇斯底里,涕不成声,“报复,还不够么?”
月照扶她起身,看着榻上熟睡的孩儿,对她说:“亏欠的,如今方还了。”
她未甘心,转而冲向银盆,想要夺走盆中的刀。指尖未及,月照已推开她,先前一步拾起了利器。
烛火下,雪银的刃光冽冽闪过,凌厉森寒。霎时间,一声叮当,猩红滴落,灼灼夭夭,绽开在鎏金的盆沿上,醒目瘆人。
彩鹓睁开眼睛,天已敞亮。她扶撑在床头,额际的冷汗腻湿头发,昨夜的梦仍令她心悸难平。
“阿娘,月儿为您梳洗。”兮月端持面盆,走进卧房,将帕巾放入盆中,轻轻拧干,替彩鹓擦拭汗水,“阿娘可同月儿一道去?”
彩鹓看着兮月投在面盆中的倒影,良久未曾说话。“阿娘有些不适,便不去了。”
“可是,阿娘答应过元老。况且,今日亦是女儿……”兮月濡湿眼睛。
哐当。面盆被彩鹓扬翻,水洒泼了一地。
“说了不去,”彩鹓嗔怒,“出去。”
兮月转身跑出房门。
彩鹓望着银盆和满地的水渍,恍然失神。
番星正洒扫庭院,听闻夫人房中传出一阵剧烈的响动,便向夫人的卧房行去,欲打探究竟,却迎面撞见闪身而来的兮月。
兮月的一双眼睛,泪光涟涟。
他问兮月:“怎么了?”
兮月不语,掩泪,匆忙走开了。
番星行至夫人房前,想问夫人,方才发生过何事,但他只是一个卑微的佣人,没有夫人的准许,不敢擅自走进夫人的房间。夫人向来不喜欢别人涉足她的房间,甚至连兮月也需要征求夫人的同意方得入内。番星立在门前,犹豫不定。
想来,夫人已听闻他的脚步声,辨出他的话音。夫人的言语从里室传出:“番星,你进来。”
槃凰庙是祖庙圣堂。及笄礼惯例在槃凰庙中举行。主礼者是庙中的巫司,巫司年轻时在族谱上划去自己的俗世讳名,终生未行婚嫁,是以纯净之身侍奉着赤凰娘娘,族人感佩其德行贞节,皆尊唤其一声姥姥。
是日。少女穿上盛装,打扮得鲜妍靓丽,在爹娘和亲朋的陪伴下,乘坐玉车步辇,一路礼乐相随,繁花相送,异常气派地赶往了祖宗庙堂,路人的目光皆被其吸引,男女老少都追随至槃凰庙前,围观少女的典礼。
槃凰庙很早就开门逢迎。庙堂中,姥姥已经用云屏、幕帘隔出一角地,备下镜台妆奁,代以闺室。今日及笄的女儿有两位,元老蘅寻的女儿树玉和族主彩鹓的女儿兮月,树玉与兮月同岁,两人同日受礼。树玉当下已至,兮月却未到来。
番星受夫人嘱咐赶到槃凰庙,他没有看见兮月的踪影,只得怛怛地站在庙门前张望。众人亦跟随他等待着那迟迟未见的女子。
“重明寨的那位女儿不知何时赶来,这样等下去,贻误吉时,怕不吉利,不如让小女先行受礼。”蘅寻不耐烦道。
树玉的笄礼例时举行。女子走至彩屏后,背身坐到姥姥跟前。对着铜镜,姥姥轻抚少女的长发,拿起梳子,一遍一遍细细梳过,再将少女的长发绾起,束成盘髻,从描金的髹漆托盘里,拾起镶满珠翠的花钿和簪钗,将花钿和簪钗束入发髻,完成一道雍容又典雅的发式。走出屏风,欢情洋溢在的面容上,少女变得愈发明丽动人。
绾过头发,拜过赤凰神像,唱过祷词,笄礼就算完成。礼毕,盛满七色花糕的金罍被端来看客面前,是蘅寻吩咐婢侍给围观者们散播的点心,权当缀点排场,娱乐气氛的一种赏赐。堂下的孩童们兴起争抢,金罍很快见空。
姥姥将受礼的女儿和观客次第送走,扶着院子里的合欢树,看了看云头日影。日上梢头,家家户户该是炊烟绻绻,将要午食。兮月仍未到来。
兮月去了何处?番星坐在庙门槛上寻思。
敲开泥封,酒芬四溢,兮月抱坛站在断天崖边的祭台上。万丈高崖下,是汹涌的烈焰,澎湃的熔浆,是一片火泊炎湖。
传说,不周山曾是持维天幕的天柱。上古,九天之上的太虚境曾孕育出无数神明,神女赤凰也诞自那里。后来,神明间谑起争斗,共工与颛顼相搏,致使不周山崩塌,赤凰身死。赤凰的尸身落在这不周山上,化作这汪火湖。姥姥告诉她,鸾族的先祖乃是这火湖里的焰火灵精所生。
火湖是鸾族的诞成之地,也是鸾族的归栖之所。所有死去的族人,尸身都要被抛下火湖,在重明真火和熔浆里化作灰烬。这是鸾族的风俗和规矩,意寓让逝者回归本源,返璞归真。阿爹也在这火湖里。
她将酒水郑重地洒下崖去:“阿爹是否安好?今日,是女儿的生辰,亦是女儿的及笄之日,既来知会您听。”阿爹离世时,她尚是垂髫小儿,如今,已过去八年。八年的时间,往事都已模糊,但阿爹离去的背影仍历历于目。
那是一个夏初的深夜。
仆佣们点燃蜡烛。案上原本摆设的油盏不知何时已悄悄被换作烛台。蜡烛的火光比平日里的油盏明亮些。从黄昏到黑夜,通明的烛火燃烧了很长时间,兰膏玉泪,一捧一捧,滑落青釉绛彩的瓷台,长长的蜡炬慢慢煎熬成了半截。她卧在床榻上,盯着那案上的烛火,始终不能入眠。或许是因为白日里睡得太频,夜里她已睡不着了。
年初,她突然染上痼疾,隔几日就头晕发热,困顿乏力,昏昏欲睡。为此,阿爹延请过许多名医,医师们进出重明寨,几乎要踏破她卧房的门槛,然而金石无效,针砭无用,病情拖宕半载竟始终不见好转。
门吱溜打开,侍女们端持着厚胎玄彩的药罐走进房室。嬷嬷同平日那样扶她坐起身子,将她靠枕在床头。丫头小厮将陶罐里的汤水滗至白釉唇口的陶碗中。带着参白热气的黢黑液体,横到她的鼻息下,苦涩滞重的气味直窜她的灵台,令她晕沉作呕。那一夜的药汁似乎比平日里的更为难咽,她不愿喝。嬷嬷好言劝她吃药,她左右不听,人们无计可施时,阿爹突然绕过屏风走进来,劝离众人。
阿爹轻轻接过仆佣手里的瓷碗,坐来床沿,嘘嘘吹凉一勺药,送到她唇边:“来,月儿听话,把药喝了。喝完,阿爹有东西送给月儿。”
“是何物?”她好奇地问。
“喝完,阿爹方能交予你。”阿爹继续为她哺药。
她听话,捏紧鼻息,闭上眼睛,一鼓作气,喝下药汁。饮完汤药,她啧着舌头,长舒了一口气,等待阿爹的赏赐。
“阿爹要出门远行,到不归乡外去,明日起,便不能再陪月儿。”阿爹将腰间的结心翎解下。结心翎是阿爹的珍视之物,从前,她常常看到阿爹深夜独自坐在书房里,盯着结心翎反复把观,凝思入神,却不知阿爹是在思忆什么。
“月儿,要听阿娘的话。”阿爹笑着将结心翎放在她手心,完了,将她卧平,掖来薄衾盖在她腹上,“莫要贪凉。”
窗外的蛙蟾促织忽然歇鸣,闱室里也变得很谧静。烛火似乎暗淡起来,月光照在窗棂间韧薄的竹纸上,愈发清明。树木投下葳蕤的幽影,如同墨迹画在窗户上,都静滞不动了。阿爹起身离去,清癯的背影落在门前的皂纱屏风上,像一折轻缓的皮子戏,渐行渐远。她将结心翎放到枕簟下,忽觉困意来袭,又闭起眼睛入睡。
兮月解下结心翎,迎向夕阳。结心翎不过是一串朴素无华的饰品,一枚水色的珠玉,下缀两片赤色的羽翎。彼时,玉珠凝透金黄的暮光,宛如族人金色的瞳眸,闪闪发亮。崖风摧拂,玉珠下的两片翎羽轻盈摆动,像是一对相拥的恋人摇姿曼舞。阿爹的面容仿佛又浮现在珠玉上,她看得出神。
太阳欲将西沉,锦带去打扫祭台,却瞧见兮月的背影。兮月的背影与她孩儿的背影一般高,都是同样的年纪,她的孩儿仅比兮月岁长五天。
五天前,孩儿到不周山上来,与她共度生辰。
“我要到不归乡外去。”夜色里,孩儿站在断天崖边,眸中,升起一团烈火。
“阿娘却希望你做个寻常之人。”她劝道。
“我不甘心。”孩儿展开双臂,猎猎的崖风,扬起孩儿的衣袖,“世说,鸾族诞自火湖,人们原本皆是这火湖里的一团火。可是,为何,各人的命程如此不同?”
“崖下是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她攫住孩儿的衣袖。
孩儿却拉下她的手,跳下岩台。
她的心也跟随孩儿坠下岩台。
嗥鸣声起,孩儿化出真形。
孩儿的嗥鸣在火湖上一圈一圈旋动,她的心在悬崖上一跃一跃踮踵。时间点滴皆是煎熬,待汗水与夜色都被蒸得稀薄,孩儿终于从崖下飞上祭台。
口衔火精,孩儿双爪触及地面落回双足。
“取到了,我取到了。”孩儿捂着左眼,跛着足,向她走来,没走几步,却跪倒下去,咳出一口乌血。
她扶起孩儿,撕开孩儿那粘住血肉的衣裳。褴裳之下,孩儿全身的皮肉已被炙焦。她一点一点洗去孩儿眼中的烟灰,一刀一刀剜去孩儿身上的溃皮烂肉,一遍一遍拭去孩儿身上的焦渍血污。孩儿却是一声不吭。然而孩儿越是静默无声,她的心越是疼痛,尖刀都似扎在自己的胸口。“阿娘拦不住你。”她的眼泪忽已奔流。
孩儿握住她的手:“阿娘不能停下,时候不早,孩儿还要下山去。”
她为孩儿包裹扎布,扎布越叠越厚,孩儿却在说笑:“扎布缠了一身,倒似几件衣裳,也算是弱冠的仪服呢。”
她羞愧垂首,不敢去看孩儿的眼睛,悄悄从怀中掏出发带来:“阿娘不能为你缝冠,阿娘能做的,唯有这条发带。”
“请阿娘为我系上。”恰时,天空中,晨星点亮,孩儿的眼中映出一星耀光,
“贯笄可在今日?”锦娘朝兮月走来。
兮月回转心神,收起结心翎。
锦娘头上缚扎襆巾,身穿粗布麻衫,作流人打扮。断天崖是丧葬祭祀台所,需保持肃穆洁净,锦带被族人放逐到不周山上,负责打扫这断天崖上的祭台。
锦娘原名锦带,虽是一身贫素打扮,面容依然不减清丽,年轻时是个秀毓的美人儿,只道是命薄如纸。她本是元老鸣风妻室的表亲。因承袭血脉的缘故,锦带与鸣风的妻室在相貌上生得几分相似。鸣风的妻室对这位与自己相貌相似的表亲甚是喜爱。锦带家中贫寒,鸣风的妻室便接济锦带在其府上做了她的贴身婢侍。
鸣风素来嗜酒,一日酒醉,鸣风误将锦带当作妇妻,与之荒度一宿。醒来后,锦带羞悔不已,离开了鸣风府。不成想竟因此种下身孕。未婚的女子诞育身孕,在乡里确是人人耻闻的丑事,何况腹中的孩子还是姊夫的骨肉。锦带回到家中,父母亲邻俱不接受,锦带也就只能上山做守丧的女冠,在这断天崖上清扫祭台,思修度日。
生下孩儿后,锦带将孩儿送还鸣风府,因那孩儿的出生为人诟病,鸣风转而将那孩儿托付给了族主,让那孩儿寄养在重明寨,孩儿稍大了,便在重明寨里做事一份杂役的差事。兮月打小与那孩儿一同长大,那孩儿即是番星。
兮月从族人琐碎的言谈中晓闻锦带的轶事,对锦带感怀怜惜。因为这份怜惜,兮月对番星生有几丝同情。她与番星,长在一处,竹马青梅,嬉游玩闹间,倒也情似手足。因锦带是番星的娘亲,兮月称锦带一声锦娘。不成想,锦娘未曾下山,竟知晓今日是她的及笄之日。
“番星生辰时到不周山上来,我便猜着月儿将要行笄礼。”锦娘似看出她的惊奇,“转眼,月儿已出落如此,倒是个大人的模样了。”
轻轻的一句言语,听来,却有一些深沉,隐隐掺杂了几分怅惘。兮月看向锦娘,霞光染红锦娘的发冠,锦娘静静地伫立在夕阳下,面色如墨。兮月想,那就是所谓的韶华易逝,如同夜幕下的一片余晖,鬓边的一缕白发,煞是凄凉。
天色已晚,太阳业将沉沦,是该下山去了。
兮月来到槃凰庙。番星正坐在庙门前,蹙目焦神,四下张望。
“兮月,你去了何处?”见兮月现身,番星欣愉地站起来,伸手,露出手心里的一支玉笄,“这是夫人为你准备的。”
兮月接过番星递来的玉笄,走进庙中。
庙中,人群早已散尽,姥姥只身站在院子内的合欢树下,长长的身影埋没在合欢树的影子里,静悄悄的,便是和番星一样,是在等她。
妆台前,天光已冥,姥姥点亮一盏灯。兮月坐在灯光里,姥姥解开她的发带,用梳子轻轻梳开她的发丝。如瀑的长发散落,又被慢慢盘起,绾成发束,再被结作发髻,姥姥的动作温静娴熟,让她惊奇,姥姥尚未没籍于这座庙宇前,也是一个巧思打扮自己的寻常女子吧?兮月瞧着铜镜里的那双手,忽然埋首啜泣起来。
“阿娘从未像姥姥这般替月儿梳过头发。”
姥姥坐下,将兮月拢靠在臂弯里,轻轻抚拍着兮月的肩臂,道:“勿怪你阿娘,你的阿娘是族主,不是一个寻常的母亲。”
兮月抬起头,将番星带给她的玉笄,递予姥姥。姥姥从她的手里接过玉笄,为她簪上。兮月记得,阿爹曾同她说过,一个人长大了,就不能再像孩童一样任性哭闹,否则会令人耻笑。玉笄落进发髻的那一刻,她就是个成人了,兮月抹去眼泪。
“时辰不早,便要速归,不然被阿娘问晓,阿娘又要生气。”兮月同姥姥话别。
元老们起身作别。彩鹓立在堂中,让执事为元老们送行。侍婢见状拿着茶盘走入堂中,欲要收拾客人们饮剩的茶水,收拾未毕,却被彩鹓屏退,心下有所会意,夫人乃是要得片刻清净,遂行退出堂去。
兮月回到重明寨时,天已昏黑。省心堂里,燃着煌煌灯火,一片通明。
省心堂是阿娘待客议事的会堂,也是连接内院与外院的中堂,坐北的正壁前摆设有一张明晃晃的金漆案,案上祭有一方玉砌的宝匣,匣子内贡纳的是几本经折装的族簿。族中所有人的名字都被记刻在厚硕而庞杂的谱簿上。过去,兮月每有犯错,阿娘便要命她跪在金漆案前,领受笞罚。想到阿娘那指粗的戒鞭,不由胆寒,兮月打从省心堂前经过,向来是垂首低眉,疾步而行,此时更加不敢看往堂内,生怕撞见阿娘的一双眼睛。
“兮月。你过来。”阿娘的声音自堂内传来。
过门到底被阿娘瞧见,兮月只得入堂。
阿娘独身站在省心堂里。堂中,客案上零散摆放有几只空茶盏和一个茶盘。看来,一场客会刚刚结束。兮月蹑蹑绕开彩鹓的目光,忙作收拾案上的茶具。阿娘忽然问道:“兮月。阿娘决定重开女儿节,给乡里成年的女儿们举办贺典。你觉得如何?”
自阿爹辞世,女儿节已多年未曾召开。兮月不知阿娘是出于何意,又为何征询她的意见,阿娘稀少以这种平和的语气同她说话,兮月错愕不及。“阿娘的决定,月儿不敢议论。重开女儿节,自是喜事,然需准备的事项却是繁琐,阿娘需月儿做些什么?”
“庆典事宜,我已托付执事去办。近日,执事去货集买办节物,你且随他到布店,挑一匹心喜的料子,让裁缝为你做件新服。”阿娘说完,背过身去,似瞅着族簿玉匣,黯黯游神。
见阿娘不再问话,兮月端起茶盘悄悄退出省心堂,出得堂门,不禁稀奇,迟归之事阿娘竟似忘了问及。
天色未明,番星已备好犊车。今日,执事要去货集买办彩绸,用来在女儿节上为楼台挂彩。执事看着犊车,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年岁渐高。倒把这事疏忽。该让你换辆马车。”番星扯住牛儿脖子上的缰绳,却是好奇,“几日里,去集都是此车,缘何要换马车?”
执事道:“今日,娘子与我们同行。”话音未落,兮月已提着衣裙跑过来,匆匆坐上行车。番星看到兮月,忽然明白过来,落轻鞭子,对兮月说道:“行车颠簸,你且坐稳。”
到货集时,晨曦微露,货集里已是一派繁华景象。连日来,重开女儿节的布告传遍乡野,女儿们走出门闱,盛行至热闹处,左右顾盼,郎子们也似热浪风行。人们都忙于为节庆博购物品,货集里,卖灯烛和饰品的摊铺悄悄多起来。举目而望,满眼都是陈列物品的货架和济济的行客,尤其是那天灯架子,周围圈挤着许多郎君。
执事看着天灯周围那些年轻的男子,心生趣意,戏言道:“番星,你也去买一个来。”
兮月听到执事的话,笑不掩嘴,随言附和道:“当买一个来,在女儿节上送给心喜之人。”
“谁要买灯?才没有什么心喜之人。别再取笑于我。”番星却似害羞。
执事取过缰绳,从怀里掏出两枚银钱交予番星,笑道:“你且去买一个来,不是送人,算是与天祈福也好,将来,亦得良缘。顺便,去买几张馕饼,我与娘子都已饥迫,便在前面的布店等你。”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女儿节已至。女儿节持续三天。三天里,人们将到处张灯结彩,敲锣击鼓,载歌载舞,乐此不疲。
平日,阿娘令她呆在寨子里打理事务,少许她出寨。但这几日是女儿节,阿娘允她出门。兮月随意走动,在这难得清闲的日子里,她本该自在享受,可她却高兴不起来。她独自游荡在巷道上,嬉笑逐闹的孩童从她身旁奔跑踅过,三五成群的乡民在她面前来去往复,她站在碌碌的人流里,耳闻嘈杂与喧嚣,心中却安静得如同一堵山壁,任凭这繁华猛烈撞击,也掩不去回声似的寂寥。恍惚中,她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错觉,为什么来到这里,又该往哪里去呢?
逛得无聊时,兮月看见不远处的一间香烛店,里面挤满了乡民。人们拿着捧香从店中出来,尽是往槃凰庙的方向赶去。兮月看着那些善男信女,想起姥姥来。在这不归乡里,与她亲近的,怕只有番星与姥姥了。不如去看看姥姥正在做些什么,她想。
当下,姥姥的槃凰庙,尤其热闹。人们结伴进出,其间多是风华正盛的男女,他们虔诚地祭拜赤凰神像,沉心祷告,跪地起签,又将写满祈语的红丝绦系到庙中合欢树的树枝上,欲福得一线好姻缘。
今日,姥姥的职责是替香客解签。姥姥坐在堂前,人们从她身旁走过,无论解签与否,姥姥都会送上一串她亲手制作的羽饰,姥姥将这种羽饰叫做羽符。姥姥说,羽符是她对人们供奉香火的回赠。羽符由乐洵川的河石和彩雀的一对羽毛制成,小巧别致,佩在腰间甚是好看,女儿家尤是喜爱。兮月坐到姥姥身旁,帮姥姥整理符签。她看往来的人们言笑晏晏地摇晃着一串串的羽符,恍思出神。乍看羽符,兮月觉得那些羽符同自己的结心翎倒是十分相似。
不知不觉间,太阳挪到西天边。暮色阴红,白昼即将过去,来槃凰庙祭拜的人越来越少。“陪姥姥坐事一天。为何不曾见过赤凰娘娘。去,求支缘签来,让姥姥瞧瞧。”姥姥站起身来松懈腰肢,对兮月笑道。
“月儿既无美貌,又无甚才识。不敢奢望姻缘。”兮月羞赧道。
“傻孩儿。姻缘重在缘字。世间儿女,皆有自己的一份际会因缘,莫要看轻自己。”姥姥说道。
听姥姥如此说,兮月走进庙堂中。
对着赤凰神像,兮月跪下,双手合握了签筒,贴在胸前,闭目祷告:“神明在上。姥姥说,莫要看轻自己,月儿也能希求一份姻缘么?月儿亲缘凉薄,自幼,唯独阿爹疼惜月儿。如今,阿爹去日已久,月儿年岁长成,这世间会有一位像阿爹那般,将月儿放在心上的郎君么?如果世上真有这样的郎君,他在何处呢?若有一日,得此缘分,月儿遇见那位郎君,纵是山高水阔,天涯海角,月儿也甘愿随他而去,相偕到老。”
签筒摇转,祷毕,缘签咚咚落下。兮月拾起签木,向堂案上排签的红书,临照看去。
半炷香后,兮月走出庙堂。
姥姥正拾掇长案,将剩下的羽符收拾起来,装进箧筐里。
“求得何签?”姥姥问及签序。
“第五签。”兮月伏到姥姥跟前,将那签号缓缓道来。
扑啦。
手中的羽符突然从指间滑脱,散落一地,姥姥耳闻兮月所述的签序,恍惚一怔。
“姥姥,怎么了?”兮月见姥姥举止有异,问道。
姥姥委身取拾地上的羽饰,脑海中开始浮现出解词来。
“胭脂语琼阑,簪花诉婵娟。明镜照影怜,鬓丝倚夜寒。”
这是兮月所求签序下题注的两句签文。
想不到,重遇这副签文,竟已过去大半人生。身伴青灯,长侍神明,她以为自己早已忘却俗世尘缘,然而此刻,当签文从她的灵台中闪过,却有一丝自悯覆上心头。
“胭脂语琼阑,簪花诉婵娟。明镜照影怜,鬓丝倚夜寒。”
她默念着签文,忽觉有些疲累,扶靠桌沿坐下,望向檐角迟暮的夕阳,不能言语。呼吸沉郁在胸腹间,她似乎有些喘不过气来。夕阳的辉光斜照着庭院里的合欢树,傍晚的风徐徐吹拂,那些明艳的红丝绦如花火蝴蝶盎然舞动,记忆随着那浓艳的色彩扑簌散开了。
那时,她与不归乡里的其他儿女一样,憧憬着一份遥不可及的感情,向往着一片广阔繁华的天地。那时,她尚未削去自己的半匹长发,也没有从族谱上划去自已的世俗讳名。那时,她且是个纯真烂漫的怀春少女。
“云衣,容阿娘唠叨劝诫,这桃园的郎君有何不好?相貌堂堂,家境又颇为殷实。嫁予他,是旁人羡慕不及的缘分。”
“他是个哑巴。”
“哑巴又如何?总比巧言郎子来得实在。那些所谓的浓情蜜意,有多少是天长地久呢?有言道,于喈鸠兮,无食桑葚,于喈女兮,无与士耽!莫要心气太高,沉湎于风月幻梦,蹉跎了年华与良机。夫妻间相待如宾,平和日久,譬如阿娘与阿爹这般,即是足矣。”
“阿娘让孩儿再想想。”
“想通方好,爹娘这就将求亲的帖子答复去。”
阿娘拿起庚帖去往东家桃园。
她望见爹娘的影子走远,开始鼓捣起行李。
打包一笼白面饽饽,挑出几件平日里爱穿的衣裳,又从阿娘的脂粉盒里偷得几枚银钱,然后,她走到窗前,端起食床上的执壶,给自己斟满一碗茶水,匆匆饮尽。末了,她将一封辞别的书信压在那青秞茶碗下,走出家门。
“我偏不嫁。”她一路念叨,走出几里地。
又过几里地,她来到不归乡的边界处。
界石之外,是神秘而自在的万千世界。她站在临界的陌道上,向身后的故土回望了一眼。这一眼,她意外瞅见槃凰庙。
槃凰庙修筑在道口旁的一座青丘土坡上。它既似在盘望天地间巍峨亘立的不周山,也似在俯瞰谷地里错落连绵的宅邸与田园,又似在目送像她这样即将出走乡野的离人。她停下脚步,饶有兴味地看着槃凰庙,心中忽生留恋。该去同先祖和神明作一次道别。于是,她故道折回,爬上青坡,推开了槃凰庙的门。
偌大的宗祠祖庙,那一刻却是静悄悄的。
她走进神堂,只见巫司正立在蘸坛前,为神坛上的供灯剪拨灯芯。
见有人走进庙堂,巫司转身看去。
“今日,庙中怎如此寂寥呢?”她凝视着巫司的一双眼睛,疑惑道。
“今日,是我的寿辰。世人怯见我,我亦怯见世人。”巫司应声道。
“此话何意?”她接着问。
“每年此时,我都会布帖,招纳生徒。然而,无人将孩儿送入庙中来。”巫司沉叹道。
“既做巫徒,就不能婚配从俗,要在神堂里孤掷终生。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儿来做巫徒呢?”她低声感喟一句。
“所以,世人怯见我。”巫司吹醒火折子,为供灯重新点燃灯芯。
“可是,作为巫司,连族主也需敬拜您三分。您若择定谁家的孩儿来做巫徒,他人怎敢违逆?”她又疑惑道。
“莫敢违逆。然而,我素来不使强权。”巫司拿起旃檀香,撩过供灯的灯火,点燃香头。
“为何?”她却是不解。
“因为,我不愿有人步继我的后尘,在这庙墙内孤身终老。”巫司将檀香插进铜炉里,“所以,我也怕见到世人。”
“可是,无人步继您的后尘,祖庙就会断继无主。总要有人来侍奉先祖和神明。”她卸下行囊,心中暗暗咕哝,巫司真是个古怪之人。
“因此,我唯有等待,等待有缘之人的出现,等她甘愿来做我的徒生。娘子可是这有缘之人?”巫司似听见她的腹语,陌然含笑地看向她,接语道。
“巫司言笑。我只是来与神明道别的。云衣要离开不归乡。此去经年,不知何日方回。”她拾起蘸坛上的签筒,跪到赤凰神像跟前。
“世间事,莫强求。娘子且自珍重。”巫司退让到一旁,摇起法铃,诵起巫经,为她祈福。
诵经声中,她摇转签筒,默诉一言:“神明在上。云衣不愿嫁与桃园的郎君,云衣想去寻求自己的姻缘。临别的时候,云衣想再问一问神明娘娘,我的姻缘将来如何?”
卜签摇落,她拾起签木,依照堂案上贴着的写满签序和签文的红书索骥而去。第五签,中平,题名妆待,有文言:“胭脂语琼阑,簪花诉婵娟。明镜照影怜,鬓丝倚夜寒。”
姥姥的双眼茫然看向合欢梢头的一片云,然而又好像并非是在看着那片云,却是透过那片云,看去遥远天穹里未知的深空。姥姥的眼神迷离叵定。她究竟在看什么?兮月不知。
“这签,是否征兆不详?”兮月打断姥姥的神思,嘀咕道。
“中平之签,无谓详祸。签文所言,是位思妇。得签者如彼妇人,粉黛罗敷,候遇良人。意寓个中机缘,尚需等待。”姥姥却是回应。
兮月想,这签文听得模棱,不过,世间的签文,大多模棱,求签者当是寻一乐趣罢了。如此,她并行追问,接着帮姥姥捡拾羽符。
姥姥变得缄默寡言。自方才兮月将卜签说与姥姥听,姥姥的心思暗自游移,常是恍惚,庙堂悄然耽于沉寂。“我的羽符呢?”兮月打破寂静,伸手向姥姥讨要,旁人拜祭完神明,从庙堂出来,都能得到姥姥送予他们的一串羽符作为礼赠,为何她竟未得到这份赠礼。
姥姥撇过头来,目光垂落在兮月的束腰上。兮月纳闷,沿姥姥的目光打量而去,姥姥的目光凝驻在她腰间所佩的两片翎羽间,半天不动。
骄阳下,大片大片熟黄的禾稼,沿着乐洵川,一路铺呈到青山下。在那禾稼尽头的,是她系念的家门。
穿过阡陌,循过水畔,转过山脚,当年离家的人儿,重新回到她的家门。一廿的光阴,弹指挥去,曾经的单纯少女俨然变成一个深沉妇人。她与家门俱不复当年模样了。屋前的蒿草长作池水一样深,屋里的蛛网垂成苇箔一样长。她走进自己的卧房,食床仍摆放在窗牗前,上面的尘灰已结作毡毯一样厚了。她推开窗扉,屋外的风涌入房中来,食床上的尘灰霎时被吹开,尘灰下,当年的那只青秞茶碗重现眼前。
她走出家门,刈禾的农人背负草秸,正从她的家门前走过,农人依稀认出她的面容来,告诉她,自从她离开不归乡,爹娘思其忡忡,俱在翘盼中怏怏病殁了。
她离开旧屋,赴往不周山,拜见亡亲。她本不愿到不周山去。想到自己的离家久别,想到自己未尽的孝行,想起自己的天真和自私,她羞愧难当,哪还有脸面直视爹娘埋身的火湖。然而,她已无处可去,不得不将自己逼上崖台。
崖上的太阳朝升暮落,她在崖前孤坐三天。第三天,她走上祭台。
悬岩下的风,猛烈呼啸,炙热的氛浪和刺鼻的烟气扑面袭来,她伸首从岩台的边缘往下看。赤红的熔浆沸滚翻腾,似一条条发光的游鱼,在崖下的潜渊里窜行翕动。
熔浆的光亮染红山岩和绝壁,染红她的衣裙和面庞,也染红了星光和月色,她和这个世界仿佛都在燃烧。
右脚缓缓向前挪去,脚尖慢慢探出悬岩,她的心一寸一寸化作死灰。
突然,一道风旋猎猎卷过,一双手疾疾伸来,她的身体被扯回了岩台。
然而,鞋底捎带的碎石和腰上所系的结心翎都已随风落下崖去。
她跪在岩台边,看着那飘落的羽翎。结心翎翻来覆去,如同两片痴缠的落叶,在崖风中辗转下沉,毫无声息地,坠入渊薮,消失在了视线里。“于喈女兮,无与士耽!”她记起阿娘的教诲,可是,她已是追悔莫及。她注视着火湖,灵魂仿佛与不周山一样崩陷了一块,过去填满她生命的那些妄念,想象,绮梦,都破碎、断裂,坠落到深渊里,随烈焰融化了。她惊起一身冷汗,不由怯缩,转身躲入背后迎来的胸怀。
过去,她从未察觉自己的懦弱,她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无畏的人,她想要的人生当是与众人不同的模样。直到她尝试踏出悬岩,她才发现,她从未真正地看清楚自己。原来,她只是这世上无数平凡女子中的一个。当她面对火湖,面对死亡,意识到自己的庸常与脆弱时,她开始懊悔,开始愤恨。这些悔恨都凝结成了眼泪,汹涌地流奔出来。
巫司搂着她,像爹娘怀抱孩儿般搂紧她。崖风逐渐吹干她的咽嗓和眼泪,直到她再也哭不出来,她抬头看向巫司。巫司满头白发,面容上爬满皱纹,巫司已是老迈。
“过去的生命已然死去,如今是为新生。”巫司的那双眼睛却还像当年一样澄明,“娘子可愿做我的徒生?”
从此,她拜入槃凰庙,做了巫徒,三年后,承祧,继为新任巫司。在此后的第十七年,一个寻常的清晨,她重遇旧物。
那日,堂前的合欢初绽,香盈满院。她像往常一样例行祷告。正值默祷之时,有人叩响庙门。她启门去看。敲门的是一双壁人。郎君名为月照,娘子名为彩鹓。
娘子掖着郎君的衣袖,入门来,起先是谒神礼拜,继而是求签问卜,然后又往合欢树上系绦祈愿。结束时,娘子突然起念,摘下郎君腰间的锦囊,跑来她跟前,赧赧道:“半月前,郎君在火湖里拾得一串羽符。这羽符不似姥姥平日里所赠的羽符,浸在熔浆和重明真火中竟丝毫未损,当是一件宝物。今日忽然想起来,若这宝物是先人用作陪葬的冥器,冒然拾得,便不吉利,希望姥姥能为这羽符赐福加持,也好慰告先灵,避晦趋吉。郎君不久就要离开不归乡,临行前,也能落个彩头。”
娘子将器物从锦囊里取出,放到她手心。她端看女子所谓的宝器,赫然怔立,那宝物正是二十年前她失落在火湖里的结心翎。
片刻之后,她释然一笑,将结心翎带到神像跟前,颂词唱经,为其赐福。赐福完毕,她将结心翎交还娘子。
娘子接过羽翎,道:“这宝物,却还少个名字。”
她低吟一句:“此物名叫结心翎。”
“结心翎?”两人听闻话语,霎时羞红脸面,喃喃自语,却是不敢看向彼此,“永结同心?”
“谢姥姥赐名。”娘子与郎君笑语盈盈,走出庙门,晨光下,悠长的一对背影,落在门槛上,悄然紧挨在一处,好似连理双枝。
“这羽符,你已有了。”姥姥看着兮月腰上悬坠的羽饰,告诉兮月:“此物先是一位故人赠与我的,却为我遗失在不周山上。后来,机缘之下,你阿爹拾得此物。如今,你阿爹将它交与你,是希望你平安顺遂,将来能觅得一位如意郎君。”
咻的一声,西天边升起几团明硕的烟火,色丽斑斓,华美至极。烟火瞬间照亮了整片天空。与那高耀的烟火相比,槃凰庙的院墙显得低矮了许多。姥姥安静地站在合欢树下,她的面孔被烟火之光照得忽明忽暗,神色间似带有几丝落寞,大概到了姥姥这般年纪,总会感怀过往,念起一抹伤情,兮月想。
“回去吧。”姥姥道,“你阿娘尚在等你。”
兮月向姥姥辞别,走出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