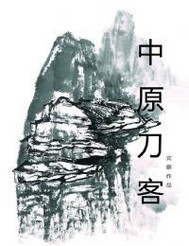大奎带着侍卫随便寻了一家农户,只说自己是过路的,山民朴实倒也不见疑。本来大奎长得一副憨厚模样,不做农夫真真有屈这幅长相,如今换了百姓的衣服若说自己不是寻常百姓,估计没人会信。
庄户人家没什么招待远方的客人,只是一盘青菜几个地瓜饼子,外加每人一碗糊糊粥。大奎走一路吃喝一路自然不饿,却把侍卫小六子饿坏了,狼吞虎咽般的吃了自己的份子。大奎把自己的那一份也给了小六子,小六子满口答谢:“还是五哥疼兄弟,那就多谢五哥了。”说罢埋头大吃再不理会其他。
大奎也不介意,顺口与这家人闲聊起来,这才得知这家农户共两口人,当家的这个庄户汉子及自己的婆娘都在家务农,只有一个女儿已嫁到了外村。听这农家汉子说了自己的家境,大奎心中不仅犯疑。看样子这两口人不过三十许人,就算有儿女也应该年纪不大,怎么这么早便出嫁了?大奎的侍卫小六子是个精细人,自然也觉出了其中的异样。大奎不好开口问,小六子倒是放下碗筷打着哈哈问起了原有。
汉子有些扭捏答道:“乡下人成家早,我十七就娶了孩儿她娘,十八就当爹了。孩子大了留不住,上年冬就嫁出去了。”
大奎听后点点头言道:“是啊,要不是年景不好,我也早就成家立室了。”
汉子闻言不仅有些惊诧,小心问道:“大哥怕是快四十了吧?还没成家?”
大奎佯装落泊的样子叹口气道:“谁不说是啊,只顾着东北西跑忙生计,也没抽空回家说个媳妇。”
若按风俗讲,家中有人来做客,女人孩子是不能上桌一起吃饭的,但在乡村僻壤倒也不讲究这许多规矩。这汉子的老婆在锅灶前忙活完了,又添了一道菜,竟然还是荤菜。大奎看了个仔细,端上来的却是一盘榨的焦黄的蚂蚱。大奎心中明白,连年兵祸再遇到蝗灾,老百姓没什么东西糊口便将蚂蚱用菜油榨了下饭。这东西倒也好吃的紧,记得小时候大奎的母亲就曾给大奎做过榨蚂蚱。睹物思人,大奎不仅黯然神伤。
吃过晚饭,大奎就与小六子在这家农户的偏房睡下了。一夜无话,第二日一早鸡刚叫,汉子的媳妇便起了床,先是熬了猪食再去喂猪。谁想刚到偏房门前却发现,那个叫小六子的竟然抱着扁担窝在偏房门前睡着。
到底是农家女,见了奇怪事连忙放下猪食桶回了屋,片刻后便将自家汉子拉出来看热闹。
汉子倒也是直爽人,几步走到小六子身前刚要去唤醒他,还不等汉子走近,小六子已睁了眼站起了身。
“哎呦我说大兄弟,你就在门外蹲了一夜啊?”汉子开口问道。
小六子放下扁担伸了个懒腰,这才笑道:“不妨事,习惯了。”说着向汉子笑了笑,这才续道:“劳烦兄弟借我木盆一用,我去打些水来,过会我家哥哥起身后该洗漱了。”谁知话音没落,身后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
大奎边向外走边嚷道:“出门在外哪里有那么多规矩,不洗了。”说着走到院中美美的伸了个懒腰,再去看了看呆站在院中的农家两口子,不仅笑道:“叨扰一夜,这就走了。多谢两位款待。”说着大奎由怀中取出钱袋来,摸了一锭最小的银子出来。
那农家汉子倒没什么,倒是他媳妇看到银子两眼放光。这也难怪,穷怕了。见到银子哪有不动声色的?
大奎见状不禁笑道:“这是一两银子,权作宿资吧。”说着将那一小块银子递了过来,那汉子没动,倒是他媳妇忙不迭的上前接了银子。大奎也不介意,吩咐小六子道:“打点行装,我们该上路了。”
小六子应了一声便去里间挑了担子与大奎一道出了门,汉子与媳妇自然送到大门前。
大奎在门前的木桩上解了缰绳牵过自己的骡子,这才回身问道:“兄弟,向西再走多远能到枕头乡啊?”
汉子还是没说话,他媳妇得了银子嘴快的很,忙上前应道:“再走七八里有个打谷场,附近几十户人家,那就是枕头……。”话还没说完,身旁的汉子忙伸手去扯媳妇的衣袖,他媳妇觉出不对也晚了,只得把话说完:“就到了!”
大奎见怪不怪,笑着翻身上了骡子,这才拱手道:“多谢,告辞!”说罢带着小六子取道向西一路行去。
等到大奎二人刚刚走远,这汉子不仅埋怨他媳妇道:“你怎么啥都说啊?这两人就不像是好人!”
他媳妇当时便傻了,忙问:“你咋知道?”
汉子气道:“过路的哪有一出手就给一两银子的?你看他们那身板,比我都结实,一看就是练过武功的人。他们去枕头乡干啥?”
媳妇还是不明就里,傻乎乎问道:“去干啥啊?”
汉子急得团团转,口中急道:“最近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听说东边还闹匪。这两个人定是来踩点的,若真是匪岂不祸害了乡亲们。”听汉子这么一说,他媳妇也急了,忙问对策。
汉子思虑半晌这才道:“昨晚我就看着不对,那个骑骡子的看着好像老百姓,说起话来文邹邹的,那个挑担子的对他毕恭毕敬。再加上今早上,那挑担子的睡在旁屋门口。我寻思着这个骑骡子的至少是个寨主一样的人物。”
“啊?那咋办啊?”媳妇此刻已是六神无主。
汉子一跺脚咬牙道:“我超近路先去乡里,跟乡里送个信。你挨家走一趟,告诉乡亲们都躲到山里去,这里要遭匪了!”说着转身进了院子,几步赶到篱笆根抄起一柄劈柴的斧子便要走。
他媳妇在门口千叮咛万嘱咐:“他爹,你可要小心着啊。”
“知道了。”说这话的功夫,汉子已奔出老远,片刻便拐进了一条小路。
大奎骑着骡子头里走着,小六子挑着担紧随其后。二人向西又走七八里此刻天已大亮,骑在骡上远远看去远处果有一处打谷场,四周零零散散数十户人家。此处该算做一座小村,依山旁水倒也是个好去处。
“可算到了,大人请人去做官却废这许多周章。”小六子说话间伸了衣袖擦了擦汗。
大奎叹道:“如今天下初定,大明正需德高贤才出来做官,若是随意委派不问德行,岂不是苦了一方百姓?”
小六子不仅笑道:“大人心怀天下百姓,我这当兵的可比不了。”
大奎扭头去看小六子,身材健硕样貌堂堂,若是太平年当是妻儿满堂了。其人先是跟从徐达元帅东征西讨,后来因为身手了得方才做了徐元帅的侍卫。如今奉元帅之命护送自己回山东赴任,一路上兢兢业业倒也吃了不少苦头。
“小六子,你家是哪里的?”大奎没话找着话。
小六子边走边答:“说来也巧,我与大人算是半个同乡,我是兖州府人士。”
“哦,看来你我甚是有缘啊。回头我跟徐元帅去封书信,你就留在我身边吧。”大奎边走边留意小六子的神色。看得出,小六子不愿意。
“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这个人就是心大,若没几个帮手还真有些手忙脚乱。你看看眼下,我这人手就不够用了。”大奎的意思是,这一路上遇到的看到的,百姓刚刚安定下来,很多事都需要官府来做。冯师爷、区大锤、孟哥三人就留在了张家庄。如今平阳府的府尹被斩了,又要出来请人做官,人手上捉襟见肘是不争的事实。
小六子没说话,只顾低着头跟着骡子走。他心中所想自然是回到军中跟从徐大元帅麾下,纵使百战沙场马革裹尸也要报答徐达元帅的知遇之恩。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大奎也不强求。眼看着进村了,却是一个人影都不见。
大奎就在打谷场上下了骡子,回手将缰绳递给了小六子,自己信步向村子里走去。明明村中路上有牛羊的粪便,看样子时候不长,怎么就是不见人呢?
随意走到一家门前,却发现院门紧闭。大奎伸手推了推,竟是由内上了门栓。
大奎不仅好奇心起,爬到门上借门缝向里张望。只见院里有几只鸡在吃食,地上的谷米还在,应该是有人的。初来乍到也不好太多唐突,大奎直起身又去了别家。小六子一手挑着担一手牵着骡子,就跟在大奎身后向下一家走去。
此时进村时的路边草丛里探出两个头来,看到大奎二人的一举一动不仅交头接耳一番。
“看到没有,这两个人鬼鬼祟祟东张西望,看样子真的不是好人。”
另一个点点头道:“嗯,叫乡亲们抄家伙,先把这两个人放翻了再交给赵保正细细审问便是。”……。
大奎二人接连走了三家都是如此,家家院门由内上着门栓,却始终不见人影。大奎心中不免急切,走到一家门前再看还是拴着门,不仅伸手去将大门拍的‘啪啪’作响,口中喝道:“有人在家吗?”
岂料话音刚落,倒是身后有了动静。回头去看,只见左右胡同呼啦啦冲出一大群乡民来,个个手持棍棒扁担,更甚者还有锄稿镰刀。这群乡民就似见了生死仇人般呐喊着向大奎二人冲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