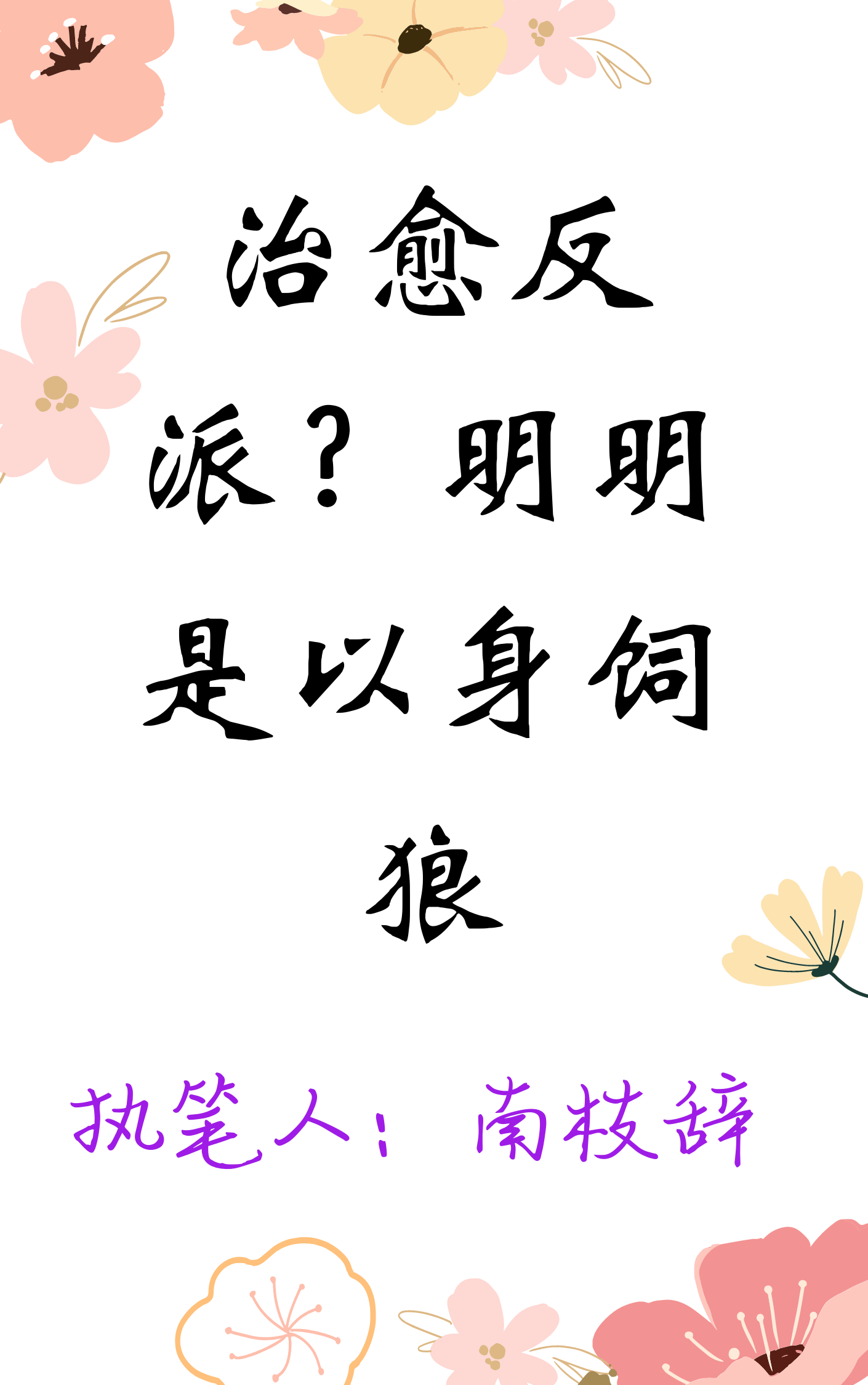花魁一下子就跑不见了。
“二哥,你看到了吗?”我问着和我一样震惊的老二。
“这花魁确实好看。”
“不是,他的脸,好像快要掉下来了。”
老二又震惊了一次。
前脚回到家,后脚蒲草和老大便回来了,看样子已经把胭脂给送过去了。
“你们刚从青楼回来?”
“没有,”老大注意到了我身上的衣服,看了蒲草一眼:“在城门口遇到了齐姑娘,送到齐姑娘家里去了。”
好啪,都去家里了,下一步是不是该见家长了,讨论那婚姻大事。
“你怎么穿我的衣服?”
“我……”他语气生硬的很,我知道我一定是做错了事,嘴怎么也张不开。
连忙换下衣服,是不是我太脏了,弄坏了他的衣服,从他厌恶的表情里,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件很重要的衣服。
“我,我,我去给你洗干净,对,对不起……”他的眼神就像是在打我的脸一般,我的眼泪不自觉得就往下滴,我胡乱抹了把眼,有些抽泣,低着头,不敢看他。
“不必了。”
他抢过我怀里的衣服,又一次离开了。
这时大哥过来安慰我,还训斥了二哥一句:“那老三这么宝贵的东西,你怎么随便就拿出来!”
又蹲下强壮的身体,用他那粗壮的手指擦着我的眼泪:“那老三就那一件像样的衣服,是他逃难时一直带在身上的,他是前朝遗孤,记性不好,才如此。”
我抬头看看那有些落魄的身影,竟然还有些心疼,我很久没有学过历史了,可背负着亡国之恨,还回忆不起什么,确实是迷茫。
不就是衣服,我可以。
我来到了布坊,里面全都是品色极好的绸缎,可是我的眼神一下子被那墨蓝色吸引住了。
“这个,这个多少钱?”
“小姐好眼光,就这一个上好的青金深的缎子了,只要八十两。”
算了,卖半个肾也换不来八十两啊。那缎子一下子看起来没那么好看了。
我还是有些不舍,垂头丧气出了门,刚一抬头,是那彩彩。
他没有穿那艳丽的红色,脸上裹着厚重的面纱,可是我只看了一眼魅惑的眼睛,就打定他就是彩彩。
“青金深。”
那嗓音甚是动听,就好像是清晨山涧中的鸟鸣般,果然是个优秀的人。(嘴脸)
等等,最后一匹青金深,他要是买走了,我怎么办。
“不行!”
那彩彩盯了我一眼,我一下子又想起了他脸皮裂开将要掉落的样子,心脏不自觉跳得厉害,不敢再言语。
见我示了弱,那人头也不回,付了钱,带着青金深就离开了。
我没有那么多钱,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还没等到走回去。就发现青楼边上全都是人。
这古代的身体都是相当的好啊,这青楼怎么还能排上队呢?我不是个凑热闹的人,本想着快步离开。
可不知谁喊了一句:花魁彩彩!
我心想,对啊,彩彩确实是花魁,花魁确实是很漂亮,可是那是一个抢别人东西的人,我听得有些烦了。
“花魁,好像死了。”
死了?!
我明明刚才才见到他啊,虽然裹着面纱,可那双桃花眼我第一次见到就过目不忘了,怎么,怎么就说死就死了呢?这还不到半个小时啊?
我更加困惑,挤进人群中,果然,人群中躺着一个红衣男子,他双眸挣得巨大,不知是那里出的血,染红了身下的一大片,已经没有了之前让人见色起意的美感,竟然有一些骇人。
但那人也确实是彩彩。
还真是奇了怪了。
很快,左道明带着县衙的人来了,还带走了一批人,这看起来好像就是彩彩从二楼摔下来死的,可是,可是才二楼,彩彩明明不是头着地,为什么会死了呢?
各种疑惑,我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就走回到了家,震惊了我现代人一辈子。
哈,果不其然,又是那齐姑娘。
她自己是没有家吗,天天往镖局跑,知道的以为活多,不知道的以为安家了呢。
我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却撞了一头的怨气。
“彩彩去世了。”
“彩彩去世了。”
我和蒲草几乎同时说出了这个消息。
那齐姑娘好像是知道内情一般,啜泣了两声。
“不对,我今天还看见彩彩了啊。”
“怎么可能?彩彩自演出出了问题就一直待在青楼里边,你怎么可能见过他?”那齐姑娘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要剧烈些。
我有些见不得她那样得便宜还卖乖的绿茶行为:“怎么?你是一直盯着他来着?还是,你把他推下去的?”
“我,我……”
“好了苏小歌!”蒲草。
虽然心里气愤,但我还是尽量心平气和地继续说道:“那你不应该给你的发小收尸吗,来我们镖局干什么?”
“我……我,我想借一匹快马。”她又开始啜泣起来,那嗓音甜腻得让人想吐,阵阵闹人心。
“好。”蒲草竟然答应了下来。
“好个屁!”我骂道,气得转身就走:“好啊,那为什么不准备两匹马呢,你们带上些家当找地方过活去不就好了!”
出了门,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淌,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我跑到了河边,蹲在地上抱住膝盖,要是没有穿越就好了,说不定现在还谈上恋爱了,和男朋友拉着手逛街,喝着奶茶说着情话。
越想越委屈,我把头深深埋在腿里。
“喂,小歌儿,”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道我的眼睛红肿成了什么样子,一支大手噗乱了我的短发。
听声音像是左道明,他意思到我哭了便不再说话,静静握住我颤抖的手,等在我身旁,等我平静下来。
我不知道我的样子是不是很狼狈可笑,从他的眼神里竟然看出了一丝丝的心疼,他跑到我的面前,用他的衣服给我擦擦眼泪。
“怎么了啊,小霸王。”
“彩彩。”我几乎是哑着嗓子,啜泣地蹦出那两个字,现在想想还真是丢人。
“彩彩案确实是有些奇怪,没关系,慢慢来,好吗?”我第一次感觉到左道明的温柔,看着他的眼神竟然有些像哄小孩子般。
“好。”
左道明轻轻抱住我的肩膀,他的怀里竟然如此的温暖:“我带你去看看,别再哭了。”他力气很大,可是又很温柔,像老大一样,把我拔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