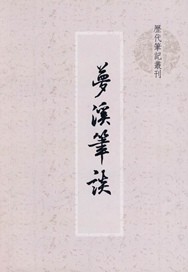“我们哥俩就是喝了点酒,就凭你一面之词,怎么就说我们就是凶手呢?”
我拿过左道明手里的拓纸,里面是一片破瓷。
“这个罐子是所有盐罐里最好的,外边还渡了层胶,应该是装钱的。”
那二人还是没有要承认的模样。
我接着说到,轻轻对着罐子片哈了一口气,瓦片上立马起了白霜,隐隐约约浮现出了一枚指纹:“这不是?”
“呵,”那跪着的反倒笑了起来:“小姑娘,这指纹谁都有,就这一个指纹,你能说明什么?”
我心里不禁暗喜:“大爷,这指纹还真都不一样。”
左道明拿来了揉好的面团,果不其然,他们哑口无言,认了罪。
那二人是林家的帮工,以前和盐贩有过交集,一起合伙干了比小买卖,挣了些钱,可那盐贩起了私心,把钱都藏在了盐堆里。那兄弟二人来要钱,三人起了争执,其中一个人抄起了装银子的罐子,砸了盐贩的后脑勺,盐贩随即晕了过去。
二人要离开之时,盐贩又醒了过来,二人便合力将盐贩扔进了巨大的盐罐里,盐贩越挣扎陷得越深,渐渐没了气息。
二人有些害怕,便将那盐贩扔到了尽东边的草地里。
心里想着请来了齐格隆冬强镖局的老大,活能干的快一些,早些拿钱跑路,可不知,我发现了盐贩。
恶人自有天收,我也说不了什么。
完事了,饿死了。我便离开了衙门。
“可以啊,小歌,”那左道明一下子从我身后给我来了个锁喉,搂的我喘不上气来:“你这几年长出脑子来了。”
是的,又一拳。
左道明和我并排走着,肿着两只眼。
“我就是想请你吃顿饭去。”左道明在一旁抱着胳膊,自己嘟囔着。
“你早说啊,”看着他红肿的两只眼我就是忍不住笑:“那我们去吃什么,给你补补。”
我看到他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我们去吃烧烤吧。”
“烧烤是什么?”
唉,古代人的生活也太没有情调了吧。
烧了些木炭,左道明买来了羊肉,穿在了红柳枝上,小王便开始了她的表演,翻面,撒孜然,盐。那羊肉的油一点点滴进火堆里发出滋滋的响声。
我忽然意识到有不对劲的地方。
“这是哪来的羊肉啊?”
“你的羊啊。”左道明说得轻描淡写。
我心里又暗骂一句,拳头一下子又准备好了。
他连忙摇手:“怎么可能,我从集市上买的。”
肉已经飘出了香味,也变了颜色。我咽了口口水,把手里的羊肉串递给了左道明。左道明捂着脸,又将信将疑地接过我手里的羊肉串尝了尝。
“你还怪会弄这些奇怪的东西。”左道明吃着手里的羊肉串,满口热气。
“我和你们不一样。”我饿得要命,也没空跟他斗嘴皮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灭了火,不知怎的,左道明反倒早走了。
我回再到镖局,天还亮着,大哥和二哥在家里,蒲草又不在。
好像还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我的小鸟。
“大哥,我的小鸟呢?”
我记得把它放到了屋里的桌子上,怎么不见了,是飞走了?
大哥停下了手里的活:“奥,那小鸟啊,你道明哥来过,讨要去了。”
好家伙,打他那两拳都是轻的,还说什么请我吃饭,男人啊,满嘴里跑火车。
大哥见我生气了,便安慰我道:“你道明哥啊,从小就想当锦衣卫,这不肯定又是去练功了,他从小帮了你不少,小鸟给他就给他吧,不行改日大哥再给你捉一只回来。”
我倒不是生气那小鸟被他抢去,我就是气不过,他万一把那小鸟玩弄死了。
“锦衣卫?”我倒是不生气了。
“是啊,那孩子打小就很精神。”
额,就是皮呗,这倒是看出来了。
这时,我看见了老二在打水,那井口小,大一点的桶肯定是进不去的,可老是用那很小的桶打水就是很费力气。
抽水泵。
又一个灯泡从我脑门上亮起。
“怎么了,别生气了,我现在去跟他要回来。”老大转身就要出门。
我连忙拉住他,冲他笑笑:“我没有生气,不用麻烦了。”
我一心都在那老二的手里,回到了房间里,万年理科生的智慧一下子就用上了,我抄起地上的滑石,在墙上画起了图:要是可以利用压强差不就可以把水引上来了吗,况且那井也不是很大。
找来挂在树上的一根草绳,一丈量。
好,要一张又厚又韧硬牛皮,支点,还有引水渠,我把那草绳系在手腕上,引水渠倒是好开,这铁和牛皮可怎么办呢?
“左道明,出来!”
抢走了我的小鸟,我要你一个刃甲不过分吧。(好像是有点过分。)
不管了。
大概过了两天,我趴在井边了两天,终于从铁匠那里打出了一根大概两米长的铁棍,大功告成。
“你说这小幺儿,是不是让啥给迷住了?”那开了闸的老二又在说我,我都听见了,真的是。
“小幺儿没有,这不,弄好了。”我拧紧了那最后一个连接点,串上了一根细铁,拍拍身上的土。
我抬高了下巴:“来吧,试试看,这样出水会省力些。”
老二半信半疑地凑过来,学着我教他的样子,压起了水。我蹲在那井跟前,紧盯着那引水渠。
果真,那水喷了我一身。
水不是从引水渠出来的,是从封口的地方喷涌而出的,这又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的顶封得太厉害了。”
我们都望向了门外,是蒲草,他提着一袋子什么进来了,可是我的目光全都被他那俊朗的面庞和背上背着的我送的刀吸引住了。
哈!可是我又一下子冷静下来,可能他只是喜欢苏小歌,不是小王吧。是小王,小王。
“给你的桃花酥。”
那一定也是齐姑娘给他的吧。
一股心酸,我咬咬嘴,伸手接过了那桃花酥。他眼神不对。
“你怎么把我的腰带缠在手上?”
我也吓了一跳,这是我从他嘴里听到的最多字的一次。
我连忙拆下来,可那腰带很长,我缠了很多圈,所以怎么薅都薅不下来,我俩尴尬一视,看出来他也脸红了。
我憋出一个更尴尬的笑。
蒲草转身就走了,留下了一句话:“从顶上开个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