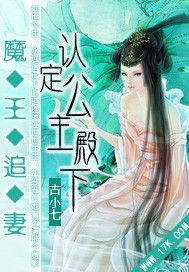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了,空气中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抽噎声和宠溺的安慰,时不时有花瓣掉落,蹑手蹑脚,就是风也知趣的静了声,只是暖洋洋的清清飘荡,漂荡着带起少年雪白的发丝,那没有小揪揪的白发,配上如玉的面颊更显纤尘绝艳。
“好了,乖,不哭了,你看你,哭的跟个小花猫似的,我都心疼死了。”少年轻柔的说着,骨节分明的手落在狸奴的脸上,轻轻地擦拭她的眼泪。
狸奴缓缓的抬起小脑袋瓜,怔了怔,一只小巧消瘦的手缓缓的触上少年的脸颊。
少年则微笑着把那只手往脸上压了压,“这一次不是梦了,说好了,我保护你一辈子”,声音柔软,眼里也不禁染上了心疼。——不管经历了什么,还是那个小姑娘,一钻进他的怀里就是乖巧可爱,豪无暴力倾向。
啪啪啪,少年脑袋嗡的响了一声,还沉浸在刚才的“毫无暴力倾向向中”,脸上又是啪啪的两巴掌。
“哥~哥~哥!,你怎么不回答我,不疼吗?说好了,明明,明明这次不是做梦的啊。”狸奴满眼伤心惧意,弱弱的抽泣着,然后再次举起能把他哥抽懵的弱弱的小手。
“我草你祖宗,还来,我特么……”少年温柔的说着话,温柔的把头死死的转向一边,脸上却迟迟没再落下巴掌,他愣愣的转过头,转眼便对上一双水灵灵的眼睛。
“哥,你刚刚……说啥?”
“我说,你轻点,很疼,不是做梦”
“哥,你刚刚说脏话了”狸·单纯无害·奴,软软懦懦的(无情)说出实话。
“你听错了”
“你刚才明明……”
“你听错了”
“你说……”
“你听错了”
“我听错了”
呼,少年长长的舒出一口气,张张嘴,准备转换话题,话还没说出口,耳边就传来了一声甜甜的叫声。
“哥哥~”
耳边一阵酥麻,少年的声音也跟着变的更加柔软“怎么了?小猫,是想问我为什么都死了,却会出现在这里吗?”
狸奴张了张嘴,闭上,然后又张了张,露出一副欲言又止,止言又欲的模样,一双手把她往怀里搂了又搂,好似一副心疼极了。
“没事,想说什么就说吧,哥不怪你,永远都不会怪你,你不要再因为哥的死有心里负担了,你看,哥都会来了,以后哥陪你朝花向晚,细数繁星。”
甜甜的花香配上柔软的话,直戳心低最灰暗的地方,狸奴只觉一阵感动,口水就跟不要钱似的,哗哗往外喷。
“哥,既然我祖宗就是你祖宗,那是不是就是你要艹自己祖宗啊?”
“哥,是不是鬼也都能那啥啊?”
“哥,当了鬼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大逆不道啊?”
“哥,咱祖宗长啥样啊,男的女的啊?”
……
又是不短的一段时间后。
朵朵杏花,春色满天,一红衣消瘦的小女孩在花丛间肆意浏览,踩踏的木质的地面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她的旁边是自闭的蹲在一旁抹着一脸口水的少年。
还是那个木屋,却已然是另一片天地,除了满屋的杏花外,冒着嫩芽的地板,长着绿油油爬山虎的墙面都洋溢着温暖的气息,原本放着红色蜡烛的供台上用瓷盘摆放着鲜艳的水果,几支香飘着袅袅婷婷的轻烟,最前面挂着一幅画像,画面以淡绿和粉红为主调,其间静卧一女子,身姿窈窕,双目微瞌,一袭烟水桃花裙称的身姿越发的修长淡雅,然而就是这么一幅温婉的画风,配的却是一张窈窕邪魅的脸,如同河流飞向瀑布,音乐升至高潮,偏那顺滑的水袖下又伸出一节森森白骨,白色带粉的叶子攀附其间,一朵白花从指骨尖开出,轻按在勾起的朱唇之上,做噤声的手势,将一切强行拉扯回平静——山雨欲来风满楼。狸奴忍不住多扫了那张脸几眼,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忽然 左面有暖风轻轻吹来,一时间带起漫天花雨,让人情不自禁的转过头去,只见原本放置的挂钟已然消失不见,取而带之的,相墙内凹陷的24个“匣子”,金丝镶嵌,里面的环境各异,但每一个匣子里都放着一个玉盘,里面装满了墨汁,墨汁上立着或雕花,或雕树木或雕动物的白蜡,此刻蜡烛上都点上了株血白的火苗。
“哥,你好了吗?,可以回答一下我刚才的问题了吗?”
“好……咳咳咳咳咳咳咳,emmmmm……让我缓一会儿,变成鬼以后灵体不稳定”少年猛的拍着胸口,眼里闪过一抹庆幸,浑然不知一颗血淋淋的头颅此刻正缓缓从头上的杏花树上冒出。
是一个小女孩的头,被压扁的头,血乎啦嚓的头,也是那个挂钟时针的头。
狸奴捏了捏手,再次提醒自己面前的这个哥哥只是个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