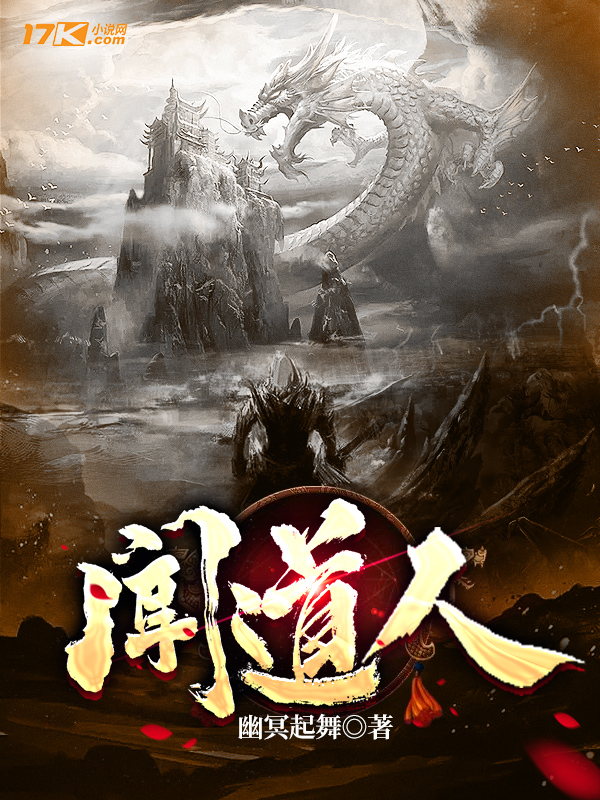第二天,江廉是被饿醒的,他惊讶地发现,昨夜另一床榻上的毛团灰物不见了,而二楼同层的别间厢房门窗皆是摇摆对开,烈风如猛虎,吹走了江廉的冠帽,小商人心中不由低估,这也太过奇怪,怎会有风同时自四面八方刮来呢?
一身凌乱地狼狈下楼,却不见桃妹,正堂之内也不见疯沚漠和任何的医者病客,江廉踌躇撩帘,整衣正冠后,踱进了后院。
浪草茵茵,物乱尘积,杂物堆垒的院中一袭黑裙优婉,正是疯沚漠。
只见她肩头借力,正轻叹着气扶起横翻在地的竹架,踮起脚,吃劲地搭上了两株无花弯叶还滴哒着水珠的藤草。
江廉原想问问桃妹在哪,然望着女子疲乏吃力的单薄身影,江廉心中不忍,有意相帮,可无奈瞥了眼自己白胖的伤手,便即侍立静待,不敢上前惊扰。
风落秋阳,直见女子忙完,江廉才不解地问道:“娘子,这医肆中的其他医士还未回来吗,怎得就娘子一人啊?”
歇坐的疯沚漠转过头来,似乎才发现院中多了一人,她复又拾起了脚侧一敞躺在地的木匣,瓶瓶入手,小心而专注、按寻某种顺律地收走了歪斜滚倒了一整个石案的玉瓷小罐, 方邀了江廉坐于石案旁的厚凳上,笑道:“此处暂且就我一人。”
“啊?”江廉皱眉道:“娘子一人尚如何经管啊?”一个比他家台州门铺大了许多的医肆,奇怪得既没有领掌的管事,也没有飞手抓药的伙计,江廉不敢想,若这单薄唯一的医士有日离门而去,那这硕大的店院不就空置了吗?
忽然地,和风悠缓下,一名碧裙女子旋风般自外面卷了来,她将两个食盒放于石案上,眼巴巴地望向疯沚漠,好奇地道:“大人……便是新主嘛?”
“是啊,在下一任临世前,我暂代此位。”
碧衣少女瞄了眼江廉,又小心翼翼地急切道:“那疯公子去了何处,可还会回来嘛?”
“不知啊……对了……”疯沚漠揭开食盒,端出热腾喷香的酱果米粥,诡测地笑了笑,“段黎,你家蓝娘子可是准备将你卖于我为药引了,呵,见你这般兴切,可是准备妥当了吗?若已万事皆了,便留下吧。”
“啊!大人莫要胡乱非议,娘子……怎会将奴卖给他人!”碧色衣裙的少女惊愕不信,紧张地反驳了句,一阵风般又卷回了幻琂酒斋。
“疯……娘子……”江廉惊地舌卷,不敢置信地颤着胖手指着疯沚漠,“你,竟要将这女子入药!怎可这般……这可是人命啊!”
“江公子莫要被红尘蒙眼,拘泥于表象啊……”疯沚漠认真专注地看着对面惊恐万端的小商人,笑得奇异。
江廉不懂, “疯娘子……此话何意啊?”
“她是只獾,可为难遇的好药啊!饭要凉了,江公子快吃吧。”
午膳间,江廉心惊胆裂吃得筷乱饭溢,只这口中弥散的菜汁香味,江廉莫名觉得有些熟悉。
临墙挺立的大银杏树下,堆着口盛满鳞纹黑水的泥瓷大缸,疯沚漠歇了膳走近,粗糙无光的水之面印出了此刻女子苍白病弱的脸。纤长的玉指划过,浑浊黏腻的黑水皲裂,分斩了水中人无神的笑颜。
一阵咕噜的水声轻响,黑水之面,浮浮沉沉浸出了张灿笑如风、优艳美丽的女性娇颜,正是蓝银芳。她一如既往地笑,樱唇开合,水中面竟无奈放言,传出了人语,“疯娘子,本娥何时将段黎卖于尔为引?”
轻点水中女子翘鼻,疯沚漠悠然自若,淡淡地道:“那半生镜的一次望川观道,乃已不知何往的疯公子于二纪前同生罗面官所换,且此物精贵,每百年只可照一回,昨日黄霞覆日、昼夜相隔,阴阳平和时正值此镜回光的契机,蓝娘子那一眼,可是用去了本该属于我的天机啊……”
“一次望川观道所需的代价,蓝娘子当知晓,疯公子留此天机于我,我自是苦熬煎盼,才好不容易等到了和尚用完几近百年……唉,事已到此,段黎,正巧乃我所需药引,呵,有了这幼獾,我便当作蓝娘子还了这因果,如何?”
水中的蓝银芳一愣,颤声道:“什么……”
姿容妖幻, 娇颜浮面,江廉瞧得稀奇,不由张大嘴。
“江公子手可好些了?”未等到蓝娘子的回答,疯沚漠轻轻划散了水中像,转身淡笑着问江廉。
“啊……好多了,昂,敢问疯娘子,桃小姐去了何处啊?”
也不知为何,江廉忽然有些不敢看疯沚漠,莫地记起了正事,江廉垂眸礼貌地询问。
疯沚漠昵了眼江廉,语气微长,“桃小姐……去禅寺听佛了。”
“啊……”江廉愕然,“那疯娘子可知她去了哪家寺庙吗?”
“知道啊,就在这永安道中,不过江公子还是莫要去了,这桃妖听佛不喜歇断,不会搭理公子你的。”
江廉有些懊恼,昨夜他怎的就睡着了呢,许是近些时日他太过精疲力倦,乃至桃妹所言,他竟毫无印象。
江廉心中担忧,前天夜里他出事,并未被招去那山中,那么,今夜呢,明早睁眼目之所见,难道又会是林木巍峨的远山桃树吗?畏思及此,江廉越加地后悔,恨不得扇自己几个耳光。
疯沚漠忽然扯开话芯,幽幽道:“江公子可是忘记,公子璘兄今日苏醒,江公子可欢喜啊!”
对啊,江廉一拍脑额,满眼欣喜地作揖告辞,临出门前却又止步,回身郑重诚恳地道谢,“这两日多谢疯娘子照顾,待在下章府归来取回了盘缠,必双手奉上诊金谢礼,拜谢娘子大恩。”
疯沚漠支着额,眉间似伴着愁虑交叠,见此,只淡淡的道:“诊金谢礼皆不用,公子在半年后,若还来永安道,便将公子那幅山雨飞鲤图赠于我吧。”
“啊……好。”江廉一怔,忆起自己房间的墙上画,嘴角抽搐,他不明白,为何会有人喜欢此物,而更加诡异的是,疯沚漠又是如何知晓这幅画的,且……都成那样了……
江廉走后,破布医舍后院再次陷入了诡异的死寂。
疯沚漠掩唇轻咳,一缕墨色自唇角悄声无息地滴落,垂了目,疯沚漠隐下眸底的疲惫空洞,不在意地抹去面上痕迹。
捏了捏不知何时歪在食盒边蔫角耷膀的灰蛾,疯沚漠望向澄澈刺目的天际,沉闷地也不知是在低喃自语,还是同这灰蛾说话,只听她茫然地道:“你说,我到底是谁……”
“扔下破布医舍让我善管,可这道店未开,眼下居然连下一任新主也来了,却又是个奇奇怪怪、不懂医理的商人……”
“真是,究竟要做什么……”疯沚漠合上眼,抱怨似地叹口气,夹起呼呼大睡的灰蛾起身,出门去了。
而此刻的外街水乡,滔忙有秩的船港捞出了具男尸的事,很快的,成了这临泽镇里繁碌茶后难得的谈资。
小莲巷,章府。
富甲豪商章元束哀丧欲绝,一夜痛失爱子的愤闷悲凄压垮了这位父亲的圆滑笑面,气势冲天带人去衙门闹了一场,然却了了无果,气晕在了回府的软轿上。
江廉今日一身灰扑扑的麻衣粗裳,昨日破布医舍醒来时,江廉便发现自己的脏衣被换下了,一念及自己的衣裳会是疯沚漠所换,江廉素脸腾地红了,他忙吐气,默了句禅语,扯平心悸。
怀揣着一腔压抑喷薄欲出问情一切的激切,江廉紧赶带跑,终于周转至了章府,却崩溃地发现昨日他走过的脚门竟落了锁,门仆也不见了
黄昏褪山,夜之华宴拉开了序幕。
熙熙攘攘的零散人影晃动,白日里十分冷寂的永安道,此刻却很是热闹。
“嘿呀,永安道何日才能正常开门迎客啊,奴家都等不及了呢。”
“呵呵,谁说不是呢,晚生这些狐皮囊衣都半年没人买了呢!诶?说起来,前些时日,晚生从洛阳赶往长安的路上,遇上了玄宗的仪仗啊,像……又是遁去骊山温泉的呢……”
“哟,那看见咱们就跑的商人又来啦,不怕了嘛?”
江廉颤着手捂住淤肿的脸,无心理会身周的笑语,浑浑噩噩地冲进了破布医舍。
正堂内,柜案旁,一名灰发盖着鸡皮壑纹的老者正慢吞吞地落笔行墨,而其身侧的黑衣女子则温言细语地说着些江廉不曾听过的奇怪药名。二人闻声望来,一个捋着须呆愕,一个讶然问道:“江公子这是?”
“没……没什么……”江廉颓萎地任由疯沚漠教着老者如何上药包缠,一人则独自缩坐在一旁,他懊丧无神地瞧向二人盯着他的脸激昂地讨论是否应该服药去肿、用药温敷,一种难言的失落与悲凉掀翻了那压抑心底已久或是恐惧亦或是愤怒的复杂情绪,江廉突然痛声地呜咽,落下了眼泪。
“这位公子哭什么?可是杨下弄疼你了吗?”老者吓得松了手中瓷瓶,歉疚道。
江廉摇头,他十分羞愧地向老者解释,自己只是一时悲从心起,才会失礼,且打碎的药瓶日后他定会按价赔偿。
老者松口气,不在意地打扫了地面,热水净手后,又寻觅排排紧闭的药柜拿来了崭新的玉瓷小瓶,他一边粗手粗脚地于江廉脸颊上涂抹,一边侃然正色地安慰道:“既已被打,那公子便莫要徒生忧恼,养好伤才是。”
疯沚漠亦是弯唇, “呵呵,江公子脸肿如斗,莫不是撬了哪家姑娘的香闺啊?”
“公子年轻力壮,怕没个轻重伤了姑娘的心,以后可得好生哄诱……”老者也木着脸笑了。
“褪肿后,江公子俊容依旧,再好生爱抚娇宠番,想来那姑娘会原谅公子的,没几日便是中秋了,永安道那天会很热闹,公子可携了佳人一同前来赏月,正所谓红袖添香,糜色酒香,江南之地碧水河畔的浪漫,果然还是于此地最有感念啊……”
“天上银月霜,碧池美人娇,船笑咉夕酿,眉落暗思藏……且道这秋夕月圆,真的会有镜中月卖吗?介时,肆中若无病患,杨下也去消个财。”
江廉一阵地愕寒,眼泪都霎时憋退,他羞愤道:“二……二位切莫拿在下寻乐,在下怎会如那登徒子般闯女子闺房呢……”
疯沚漠与这老者皆是笑起,只听疯沚漠道:“呵呵,好,公子的手也该换药了。”
然而语罢,却是老者取来了药,笨拙地解开江廉手上略脏的布条,专心致志地查看起江廉的十指。
掌灯时分,老者满意地打了个他自认十分可观的结扣,背着手去扒席案上两堆小山高的药材。
江廉怪异地抖了两下被包得歪七扭八的绷带,不料下一瞬白森森的布条竟荡着圈松散开,江廉沉默了。
纤手挑了挑灯芯,烛焰撩着火星噼啪乱响,明灭不定地恍现了疯沚漠此刻定定出神下那诡测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清侧颜。
江廉咽下口水,他既恐惧,却又实在好奇,眼前的女子是念及什么才会露出如此即欲摧毁自己了结一切的病态神色呢。
然事急从权,江廉硬着头皮上前,讷讷地道:“疯娘子,可否劳您帮在下重新包扎一回吗?”
疯沚漠怔怔转过了头,一双迷惘空洞的黑眸死气沉沉地静视着江廉,直至小商人被盯得局促不安地流下汗来,疯沚漠飘游天外的神思方才回归,她拍了拍脸颊歉然道,“好,公子且坐下。”
双手再次被束缚包裹,江廉寻着机会小心翼翼地问道:“疯娘子,桃小姐回来了吗?”
“桃妹未来,兴许……已经回括苍山了。”说着,疯沚漠突然严肃认真地看向闻言便蒙头丧气的小商人,“江公子,你真的从未学过医吗?”
江廉怔愕,不明白眼前的女子为何会再次这般问,只道:“是,在下从未学过……”
疯沚漠皱眉,严肃地道:“既你与此地有因果,那我便带你去见见那小丫鬟吧,”
江廉腾地跳起,先是欣喜,后又不安道:“疯娘子,那要去颠连巷找那丫鬟吗,那是什么地方?在下真得可以去吗?”
疯沚漠道:“可以,不过公子去了不可言语,不可乱跑。”
“啊……为何……”江廉心中疑惑,他总觉得这个看似温柔寡淡的疯沚漠在见到他的第一眼起就有些不对劲。那眸色潋沉,白皙的人畜无害的清雅笑容下却偶有一瞬疲乏、焦迫、乃至微不可察锋利的复杂神色隐泄。
江廉正茫然无措,旦见女子温柔一笑,“因为你是人呐。”
“啊……”
另 一边,埋头苦干的老者将头从两堆药草中拔了出来,有些无力挫败地道:“杨下药材尚未分完,若同大人一道前去,回来再继续分药,恐是截了明日也分不完……“”
“你不用去,不是还头晕着吗,分药不急,乏了就去歇息。”
疯沚漠拍了拍额头,淡淡叮嘱了句,便引着江廉走出了破布医舍,婷婷袅袅地迈进了永安道弥朦的白雾中。
夜凉如水,江廉抱着手,眼睁睁看着四周紧闭无名的各色小楼渐渐隐没,那些摇曳晃动的模糊人影也同样消失不见了,一阵不安的凉意窜入了心底,江廉这才后知后觉、毛骨悚然地发现自己竟如此轻易地相信并跟随一个才见了三回的怪人闯入了此方缥缈天地。
许久后,周遭一汪的白雾依旧缭绕,搅卷如云朵,轻飘飘挨蹭着江廉的衣衫,江廉颤抖着手拥紧自己,又快走几步,四下张望。
云雾衔着黑夜暮色笼罩天地,除了自己,唯有前方那抹清瘦的倩影惹眼地醒目,而其他的便真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江廉不由汗颜,他脚下还是永安道吗?这里,究竟是哪……江廉惧骇地想,会不会下一瞬就有妖怪立现,然后一口将自己吞入腹中呢……
他心中苦闷,前有险路,后又不知退路,事已至此,他只泣自己倒霉,才会怪事诛身,又思及自己一个软弱的人类如何在妖怪的地盘间挣扎呢,江廉苦涩地吞下悔意,还是早些弄清了那丫鬟的事后,赶紧离开为好……
“公子去章府出了什么事吗?”前方不知何时提了盏白纸鱼灯的疯沚漠忽然背着身问道。
江廉警惕地打量眼四周浓晕不散的白雾,在确信并无异动后,才无奈愤闷地说起了下午的事。
角门落锁,章府门客若市,江廉终是因惧怕被家仆认出而不敢进府,却又放不下能偶遇章璘或者明武的念想不停在章府周围徘徊。
街巷上,人来车往间,江廉暴晒着日头苦苦挨到了日暮西沉。
浑浑噩噩地江廉没有取回足以归家的盘缠,然黄昏在即,左右逡巡下,江廉凄楚悲凉地发现自己于此地举目无亲,竟再没个安心的落榻之处,难道,他只得借着月色走回台州吗?
然而令江廉险些喜极而泣的是,途径一家布庄时,江廉惊愕地撞见章璘正友同两个少年挑三拣四地比划讨买着时下十分受年轻公子小姐们推捧的青荷布样。
“贺言!璘兄!原来你在这啊,身体好些了吗?”
“诶?你……萌生啊,你怎得来明州了?家中的铺子不用看管了嘛?”
江廉懵了,“不是……贺言留信让我初秋送桃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