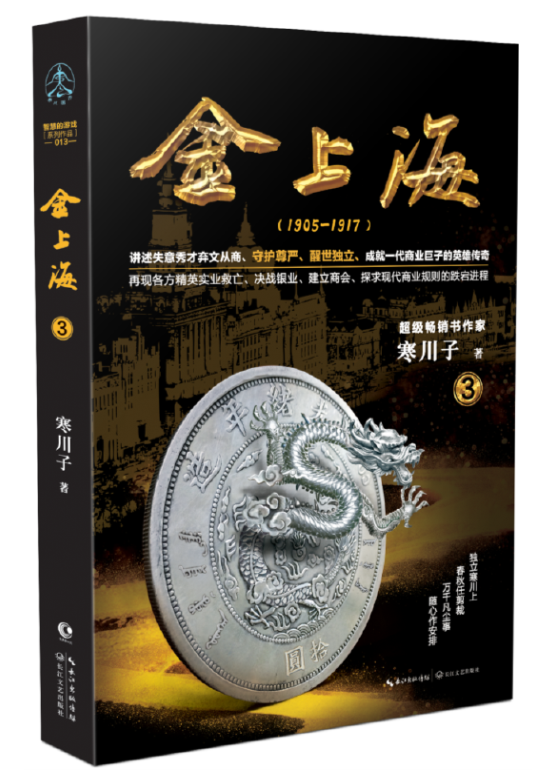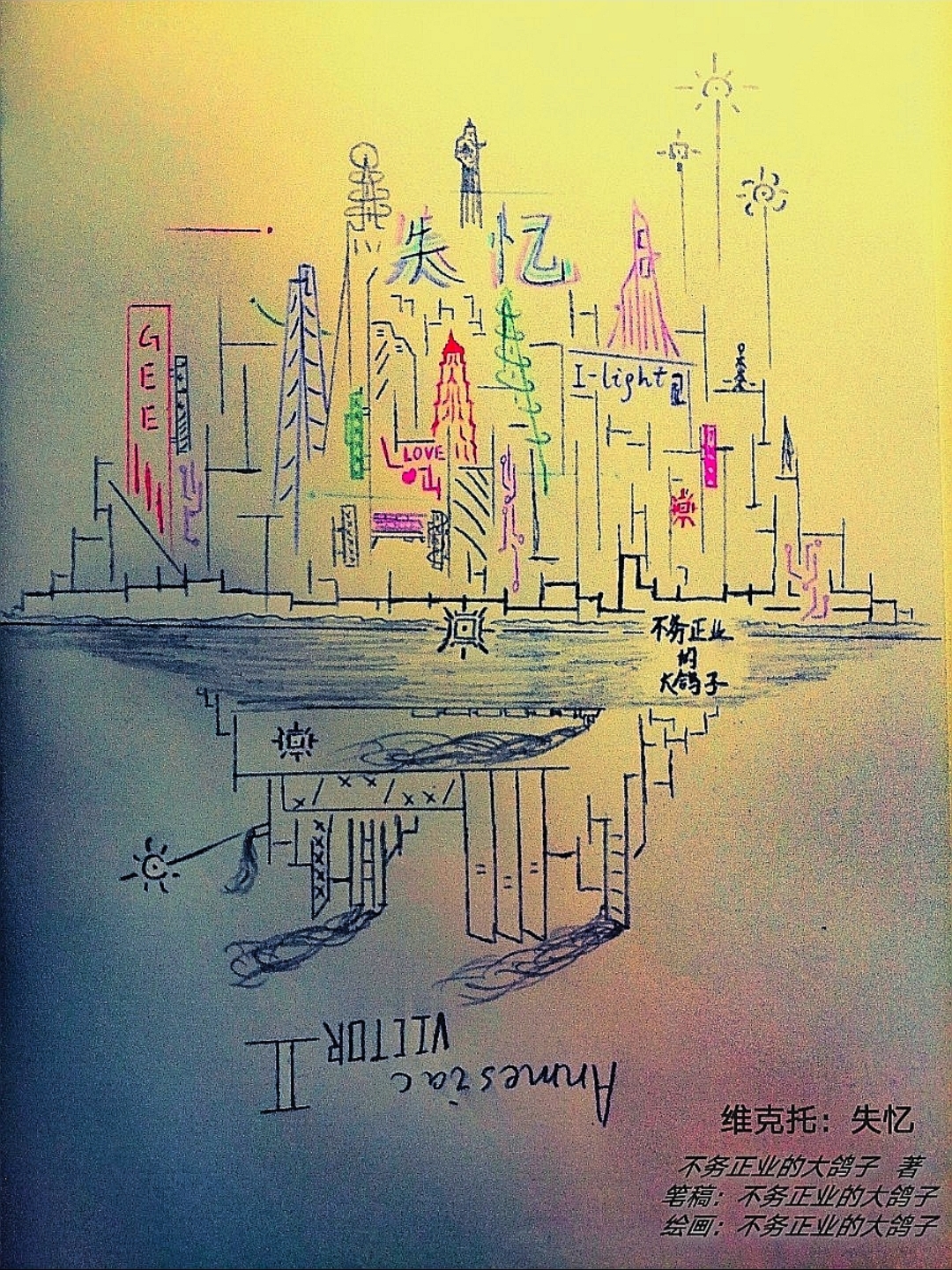伽崀山下的月息河一直横穿着墨城而过,举国闻名的云雾茶就是出自伽崀山。
位于天暄最南端的墨城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以月息河为界,左岸繁华、右岸颓败;左岸的夜晚灯火阑珊,靡靡之音悠扬婉转、右岸的夜晚只有死一般的寂静。左岸聚集着所有的贵胄子弟,右岸是社会最低等的贫民们。
时值正午,热辣的太阳晒得人有些昏昏沉沉,连素来叫声震天的知了都奄奄一息的,所有人都巴不得躲在阴凉的地方偷闲。
而右岸的月息河边却蹲着身材一个娇弱的女子,卖力得洗着手中的衣物,河水已经打湿了她洗的泛白的绣花鞋。不断的有汗水从她的额间滴落下来,她却顾不上擦。原本苍白的小脸已经被太阳晒得通红,连嘴唇都晒得有些干裂,起了白色的薄皮。
过了一会儿,手中的衣物洗的差不多了,她才仰起头看向对岸。河面很宽,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河对面那间素雅清丽却不失富贵的楼阁是浮云楼。
烈日晒的她有些恍惚,她擦了擦额头上的喊,她好像已经不知道跟着哥哥从左岸搬到右岸有几年了,是七年?是十年?还是已经更久了?
她是李嫣,李家当年是墨城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四世同堂,祖孙齐乐,在墨城当地颇有声望,口碑也很好。李家的当家主早年是先帝身边的近臣,连县城老爷都要礼让三分。
十年前,李家的当家主李航因为文字案被牵连,落了个满门抄斩,祸连九族。她与李航是旁戚,才保全了她与李家最后一条血脉李即的性命。李即带着她躲到右岸,从此隐姓埋名,不问世事。
李嫣已经不记得最后一次去浮云楼是什么时候了,李家抄家的那一天,她站在浮云楼前,楼里的浮云姑娘走到她面前,对她说,如有什么麻烦可以去找她,浮云楼的大门永远为她敞开。
李家出事后,原先门庭若市的府里便冷清了下来,她跟着李航的长子李愿,也是她堂哥去求那些个平日里与李家私交颇好的官员,得知他们是李家来的,不是闭门不见,就是冷言冷语相待。
客气一点的,还能跟你寒暄几句,说一些抱歉的话;不客气的直接用扫帚赶人,更有用冷水泼的。
那个时候,浮云姑娘能对她说出那番话,她已是万分感激,虽然还是没能将摇摇欲坠的李家救于水火,她也没有必要去麻烦浮云姑娘。
她拖着沉重的浣衣桶一步一步往自己居住的小木屋走去,安静的林间小路上果然没有遇到一个人,她暗自松了口气。
她为了躲避外界那些污秽的流言,才选择正午没人的时候去洗衣。哥哥虽然叫她不要介意,但她毕竟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姑娘。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难免会有些流言蜚语传出来。屋旁的住的也大多是无所事事的长舌妇女,最爱的人后嚼舌根。
“嫣儿,你回来了,我正想出门找你,怎么大中午的去河边?看你,满头都是汗。”李即刚刚从校场操练回来,身上厚重的铠甲还没来得急换下。看着李嫣吃力的抱着木桶,他连忙上前欲接过。
李嫣未松手,摇了摇头:“不重。”
李即站在院子里,看着晒着衣服的李嫣,他的兵甲很重,衬着她的小手瘦弱而苍白。他记得他带着嫣儿从李家逃出来的时候,嫣儿才五六岁的光景,跟着他颠沛流离,到处吃苦。别家的姑娘到这会儿都许了好人家了,却因为他耽搁了,连个上门说媒的人都没有。
“嫣儿,我们晚上去浮云楼吃饭,我想带你见见媚笙。”
李嫣刚刚晒完衣服,抱起空木桶,手上一顿,沉沉的木桶顿时跌落在地,砸在了她的脚背上,她却恍然未觉得痛。
李即立刻将她抱起,放在石凳上,脱下她的鞋袜,盈盈如玉的脚背已经红肿了:“你坐着别动,我去找膏药。”李即刚刚转身,李嫣的泪就掉下来了。
等到李即拿着膏药出来,看着李嫣哭的梨花带雨,不禁莞尔:“很痛么?怎么还跟孩子一样哭鼻子了,羞不羞?”
晚上,李嫣穿了一件紫罗兰色的彩绘芙蓉对襟收腰振袖的长裙,是她去年生辰的时候李即特意找人给她做的,她一直舍不得穿,今日才拿出来。
发上只是用一支普通的银簪挽住,盘成精致的柳叶型,发间别着一支鲜艳的山茶花做点缀。画龙点睛般的让原本瘦弱的李嫣显出勃勃的生机来。
还未到晚间,左岸就已经莺莺燕燕的开唱了,她亦步亦趋,有些彷徨的跟在李即的身后。十年的困苦、贫瘠和忧愁已经让她羞于站在别人面前。
浮云楼还是跟十年前一样,年代越久,浓厚的檀木散发出来的香味越是清醇、甘甜。相较于左岸浮华的一切,浮云楼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却偏偏让人沉醉其中,并甘之如饴。
在雅间里,她看到了常常被哥哥挂在嘴边的媚笙。
“虚己,你来了。”虚己,是哥哥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