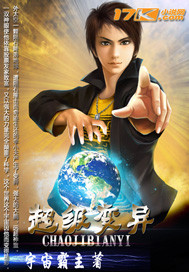刘儒山赶忙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走近谢婉亭,踮起脚跟,凑过耳朵,脸上猥琐的笑着,身子尽量往谢婉亭身上靠去。
要是平时,谢婉亭肯定会给他伸过来的那张臭脸一个耳光,然而她要说的事事关重大,她也不管那么多了,轻声将白狐持《九重经》来这儿的事和盘托出。
刘儒山听了,脸上惊讶的表情一闪而过,随即深沉下来,迈着小步子,在厅堂里踱来踱去,他毕竟是一门之主,这件事必须慎之又慎,稍稍处理不当,就会酿成大祸。
白狐瞧他走来走去的,眼珠也跟着转来转去,时间久了,晃得他眼睛都有些花了,厌烦道:“你怎么老走来走去的,定下来不行吗?”
刘儒山虽然知道白狐在说话,但对他说的内容却是置若罔闻,闻而不听,他停住脚跟,怔怔地盯着白狐,这人在这个时候拿《九重经》出现,到底有什么目的?他为什么堂而皇之的就在这里叫嚣找天镜派掌派之人。刘儒山反复思揣这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刘儒山人是停住了,可是好似在神游物外,并没有把自己的话听到耳里,白狐撇撇嘴,“喂,掌门人……喂,掌门人……”连叫数声,对方依旧不语,愣愣的看着自己。
谢婉亭见丈夫想得太过入神,上去拎了拎他的衣领,刘儒山这才幡然惊醒,转头“哦,哦……”,谢婉亭给了他个暴栗,“蠢材,想什么呢?快拿主意。”虽然许多事情上谢婉亭都做得了主,但对于关乎门派存亡的大事,她也不敢马虎,多要征求刘儒山的主意,再行定夺。
小眼珠在眼眶里转一圈,刘儒山又开始盘算起来,自己的仙术刚练至第三重,若能得《九重经》上的秘诀相助,势必事半功倍;药香门的弟子们若能习得《九重经》,那重振药香门也指日可待;但倘若让别人知道《九重经》在我门之中,很有可能引来不少觊觎宝书的正派邪门,抑或仙人魔将,我药香门势单力薄,势必惨遭灭门。
刘儒山左思右想,权衡再三,既怕灭门之祸,又不想把唾手可得的宝物拱手让人,但他本性贪婪,瞧了几眼《九重经》就放不下了,用商量的口吻问谢婉亭,“还是先给少侠找件衣服,留他小住几日,你看如何?”说完,眼巴巴的等着她决定。
谢婉亭知道刘儒山这么说,是想留住白狐,夺取《九重经》,她心下也极是赞同,能朝夕见到白狐这样个俊男;又能练到《九重经》,功力大增,当然愿意,但她又不愿在刘儒山面前急于表露心扉,失了威望。于是,她白了眼刘儒山,用慵懒的语气,慢条斯理道:“那就这么定了吧。”
药香掌门见妻子答应了,立马便开始张罗起来,“魏道,速去取件衣服来,给少侠蔽体遮寒,我们得留少侠在这小住。”他可不片刻不想看到白狐那迷人的身段,深怕谢婉亭不小心把持不住自己,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给自己扣个绿帽子,便宜了这小白脸。
谢婉亭对刘儒山这点小心眼,自是心知肚明,她当然不想白狐穿了衣服,恨不得时时刻刻都看着他的身子,但这些她是万万说不出口的,若自己连这个都说出来,那非被人当作话柄不可,她只有怪刘儒山多事,剜了他一眼,没好气的道:“瞧你那猴急的模样,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掌门人?”
刘儒山不敢回嘴,装作没听见,面露和蔼地对着白狐温言道:“少侠手中可是《九重经》,若是,可否借在下一观。
终于说到正题了,这侏儒谈到《九重经》,态度都来个180个大转弯,看来这书至关重要,我得好好利用,敲他一大笔。白狐干咳数声,清清嗓子,扬起手中的宝书,得意洋洋道:“算你小子识货,这便是你们那什么……饿……垂涎三尺的《九重经》,借你看嘛……暂时还不可以的。”他怕刘儒山一拿到宝书,就占为己有,不还给自己,那自己岂不是白跑一趟。
刘儒山本来也没有抱希望白狐会把书借给他,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要是他有《九重经》他也不会把宝书毫无防备的随便借给别人,他表面上对白狐的话表示理解,好像漫不经心顺口道:“少侠,你可知道这《九重经》有何意义?”
刘儒山这么一提,倒是勾起白狐心中许多疑问,这《九重经》究竟是何物?缘何狐狸理事会,天镜派众人都渴望得到?白狐随手接过魏道递过来的白绸衣,胡乱披在自己身上,不管怎么样不能在这些人面前显得自己无知,他佯装对《九重经》了如指掌的样子,摇头晃脑,“我自然知道,此书名曰《九重经》,谁要是学会了那可当真了不得,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呼风唤雨,号令天下……”他知道此书如此重要,想必功效不小,索性胡吹海侃起来。
下面众人听了都微微颔首,毫不夸张的讲,《九重经》却有此等神效。刘儒山则眯起眼睛,扭着上翘的小胡子,语重心长道:“那么少侠可知道这《九重经》可是本不祥之物。”
白狐正胡夸得起劲,突然被打断,一句话噎在喉咙里,好半天才道:“你说什么?这书是那什么……不祥之物?”
“不错,此书是天镜派至宝,同时也是武林各派,仙界的空翼城,魔界的无底窟,人间的游妖们梦寐以求的宝书。”刘儒山见对方吃惊的样子,就断定对方对《九重经》并不完全知晓,看来自己是说到点子上了。
“仙界?魔界?空翼城?无底窟?游妖……”白狐完全被弄糊涂了,这些究竟是什么啊?怎么从没听说过?